大英图书馆的声音档案馆为未来的人类保存了数百万份音频资料,我们可以从其中听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大英图书馆的声音档案馆里保存着超过7百万份录音资料,这些资料中包括人类运用录音技术留下的最早的录音片段 图片来源:Clare Mallison
1930年,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索尔(Patrick Saul)的17岁男孩走进伦敦的一家唱片店,想找一张匈牙利作曲家多南伊的小提琴奏鸣曲唱片,可是这张唱片已经售罄,索尔马上赶去大英博物馆,希望至少在那里可以找到这张唱片来听一下。可是当他去到博物馆,却被告知大英博物馆里不保存任何留声机录制的唱片。多年后,索尔着手建立起了国家声音档案馆,他描述当自己意识到已经无法找到那张唱片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第一次听到了死亡这个词”。
后来索尔进入银行工作,对保存声音材料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又用了好几年时间游说富人捐款,最终于1955年创办了录音研究所(Institute of Recorded Sound),这是声音档案馆最初的名称。在之后的数十年里,经过多次拨款和后续建设,该研究所成为了现在的大英图书馆声音档案馆。档案馆内收藏了超过700万份各种录音资料,这些录音资料都保存在位于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保存的格式多种多样,从蜡质圆筒(wax cylinder)到WAV文件。这些录音材料有的年代悠久,包括人类运用录音技术留下的最早的录音片段,内容从英国爵士乐的口述历史到玻利维亚爬地雀的鸣叫声,应有尽有。

成立后,声音档案馆不断扩充馆藏内容,收藏的录音材料包括全球音乐、广播节目、著名文化人物的采访录音等等,甚至还有声音地图,人们可以录下自己的地方口音,然后上传到声音档案馆的网站上。
为未来的人类保存过去和现在的声音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而且与照片或信件不同,录音资料并不被人们视为一种历史文物。那么,通过声音保存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该选择哪些值得记录的声音并将之保存下来呢?
2005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得主艾米莉·汤普森曾在2002年出版了《现代性的声音景观》(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一书(该书被广泛认为开启了对声音研究的全新领域),她强调以声音作为观察历史的一种媒介,能够赋予人们独特的深刻见解。2013年,汤普森创建了一个名为“喧闹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网站,这是一张互动地图,记录了1926年至1932年期间纽约市被投诉的噪音情况。在网站的介绍中,汤普森解释说,她的目的不仅仅是向新的观众群体呈现城市的声音,“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声音的意义,采取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倾听模式,让现代人的耳朵聆听到过去的音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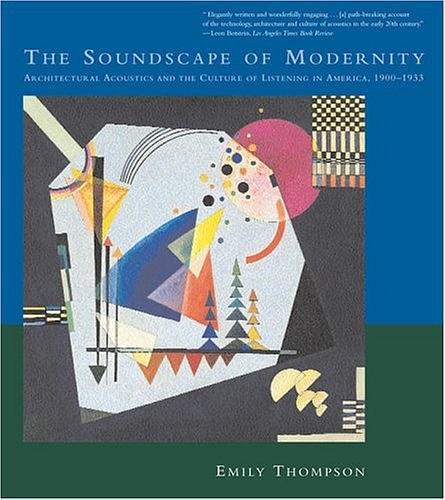
和汤普森的数据库一样,声音档案馆为馆藏的每一份声音资料都保存了背景环境和技术细节,这样任何人听了这些录音后都能了解它存在的历史环境和位置。“我们有回到过去的能力,”档案馆的声音技术主管威尔·普伦蒂斯说,“我们的文化通常以视觉为主导,因此人们不一定意识到声音具有的价值,但是录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记录了时间。”听一首1950年代的民歌,或是听一段1960年代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谈话,都会对人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因为这些录音将过去与我们当下的体验并置在了一起。我们也发现其中存在着相似之处与显著区别:例如,20世纪初,伦敦街头最常听见的声音就是奔跑的马蹄发出的刺耳的哒哒声。但是当年伯威克露天市场里摊贩们的叫卖声,与今天人们在类似的环境里听到的吆喝声却几乎不会有什么区别。
试图理解过去将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过去距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一些我们现在认为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声音,例如,调制解调器的拨号音,或是传统火车的机车头发出的突突声等,其实都是在不久之前才变成文物的。而且现代生活中许多恼人的声音,例如iPhone的铃声或摩托车的轰鸣声等,很快也会依循这个规律,成为代表着过去的标志。

声音档案馆馆藏的录音资料有些来自捐赠,有些则是因为接受了特别委托而保存的。例如,一些负责人为了填补藏品的空白,希望确保英国中部地区的一种语调轻快的独特方言得到记录和保存。“如果我们留存的拷贝丢失了,那么这些声音将永远被人类遗忘,”普伦蒂斯说,“我希望所有声音都能被妥善保存,因为它们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目前,档案馆收藏了18.5万卷录音带,在未来的五年里,他们希望将其中的16万卷进行数字化处理,这样就可以保存大约50万份录音(而且他们将获得约20%这些录音的版权,后续可以将这些录音放到网上)。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份的录音资料可能面临永远丢失的命运。
档案馆声音工程师的工作是将一箱箱的光盘和磁带进行筛选,并试着将其归类入档,他们通常是最先听这些录音材料的人。这些工程师或档案管理员在一天之中听到的录音总是五花八门——可能是一段1970年代对一位驱魔师的采访录音,也可能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种特别的青蛙的叫声。有些录音材料送来时附有注释,或是附有对录音所包含的内容的猜测性描述(例如,“1918年,电台广播录音,来自英国德文郡?”)。另外还有很多录音材料需要工程师去分辨其中人们可能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或者用于演奏的是何种乐器。
1857年,法国发明家爱德华-利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É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为他的声波记振仪申请了专利。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录音设备,由一个非常大的漏斗和一根指针组成,能够在煤灰覆盖的玻璃上记录声音产生的振动(这是最早的声波运动的视觉呈现)。20年后,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他的留声机中有两根指针,一根用来录音,另一根用于录音回放。他的留声机保留了那个大大的漏斗装置,用于捕捉一定范围的音频。目前声音档案馆里的很多录音都是以乙烯基塑料唱片、磁带和蜡质圆筒等方式保存着。

载有这些录音的材料质地已经十分脆弱,而且还一直经受着岁月的侵蚀。即使这些录音本身的音质能够达到完美状态,用来听它们的必要设备却有可能已是被时代淘汰的过时产品。十年前,在eBay上花100英镑就可以买到一台专业级别的卷盘式磁带录制设备,现在一台这类机器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800英镑。而且,要找到具备相关知识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这种机器,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鉴于上述情况,声音档案馆开始加大力度对馆藏的所有声音材料进行数字化处理,这一举措也是一项名为“保存我们的声音”(Save our Sounds)的倡议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将持续至2023年。根据活动计划,声音档案馆与英国各地的区域中心开展了合作,培训工程师和档案保管员,使他们具备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继续进行保存当地历史的工作,并且确保重点不仅仅聚焦于已经在伦敦开展的工作上。
这项活动包括带着磁带、乙烯基塑料唱片和MP3等音乐文件走访养老院和学校,在教室或社区会议厅里为听众播放他们所在地区的口述历史,或是一段1960年代的当地电台新闻节目录音。“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听到有关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在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一些甚至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播放过一个钢铁厂内部的录音,对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们,这段录音唤起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回忆,”普伦蒂斯说。
对于各类录音材料,无论是记录日常事件(两位来自曼切斯特的好朋友之间关于学校生活的对话),还是重大事件(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1964年的瑞弗尼亚审判时发表的著名演讲的录音,这份录音来自曼德拉的辩护律师乔尔·约弗),又或者是文化活动的片段(1991年,约翰·伯格在当代艺术学院朗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该录音长达一个小时),声音档案馆全都给予同等的重视程度。这些各种各样的录音材料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处理,而且被妥善地保存着,很多还被仔细附上标签放到了网站上,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它们。其中包括不少来自英国各地的普通人的录音,这些人大多并非名人,但是聆听他们对自己平凡生活的描述非常令人感动。这些普通人讲述他们遇到的人、他们听的音乐、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的各种感受,对我们了解过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声音档案馆里,历史已经不仅局限于新闻标题和事件的整合体,历史还是一系列可以体验丰富情感的游览历程。
声音档案馆在保存声音资料的工作上所显示出来的仔细和审慎,与新兴的现代音频素材的保存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诸如YouTube等一些互联网网站,在对音频资料进行保存和归档的工作上则显得疏忽大意和处理失当。2019年3月,MySpace网站宣布,数千万份于2003年至2015年期间上传到该网站的音乐文件已经丢失。
互联网上的一切都是永恒的,这句格言的背后似乎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成为历史记录的声音材料保存在互联网上,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不需要专业设备或专业知识。但另一方面,这些声音的实际材料,包括音乐、实地录音、环境噪音的剪辑片段等,都是保存在各种网站和社交网络上的,这些网站和社交网络有可能在一年内就会关闭,而且这些网站可能要求大众必须使用一些很快就会失效的软件才能获得这些声音材料。
尽管数字化处理对保存许多年代久远的录音材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的录音材料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但是录音中的一些不易捕捉的无形部分可能会因为数字化处理而完全消失。音乐家兼作家达蒙·克鲁科斯基在他的播客和同名书籍《聆听的方式》(Ways of Hearing)中探讨了音质改变的问题,以及这种改变对人们的聆听体验造成的影响。达鲁科斯基指出,声音从模拟信号录音的形式转换成数字格式后,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因为大多数数字格式固有的压缩和处理手段消除了声音材料中原有的环境或背景噪音。

毫无疑问,环境和背景噪音也是声音档案努力加以保存的重要部分。1987年录制的伦敦7号线双层巴士在波多贝罗路上行驶的录音资料之所以能够使听录音的人感觉身临其境,正是因为当时安放在巴士顶层上的录音设备录下了远处呼呼的引擎声、巴士靠站停车时清亮的叮一声铃响,以及雨点慢慢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的啪嗒声。模拟信号录音具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缺陷,因为恰恰是那些细碎的杂音、静电噪音和背景噪音,令听者感觉身处一个无比真实的氛围之中。
声音档案馆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合作伙伴的加入,才能保证妥善保存所有的馆藏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全部数字化。同时,这种需求也导致一些人认为,并非所有的声音资料都是有价值的。普伦蒂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将来我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这是声音档案馆的核心宗旨,而且这一宗旨自开馆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1955年,索尔和录音研究所新任命的董事一起呼吁公众提供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录音,并且声明任何录音都不会“因为审美标准的理由”而受到拒绝。这一原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也许现在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但是正如档案馆的其中一位董事所说,“我们无法判断我们的后代会对什么内容感兴趣……因此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让我们的馆藏无所不包。”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嘈杂,耳机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只听自己愿意听的声音,而把其他声音全都拒之门外。当你听到半个世纪前曼彻斯特一条喧闹的街道上的声音,便会意识到,在过去,无论是在音乐厅里还是在繁忙的街道上,或是大家围坐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声音曾经是人们的共同体验。2020年代的录音与一个世纪前的录音听起来肯定截然不同——有可能更加碎片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混乱。但是,如果像声音档案馆这样的机构能够做到认真聆听,相信未来的人类将有可能听见过去以及现在的声音。
本文作者Sanjana Varghese曾是英国维康基金会学者,主要为《新政治家》杂志撰写科学和技术类文章。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