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斗士”已经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记者 |
编辑 | 黄月
2020年的伊始并不太平。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外,中东局势开始了新一轮动荡。1月底特朗普公布了引发巴勒斯坦强烈反对的“世纪协议”,协议除了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之外,还提到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之一是“对恐怖主义的坚决抵制”。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依然起伏不定,伊朗总统鲁哈尼2月23日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恐怖主义”。3月5日,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刘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上强调,“恐怖主义不分好坏,反恐不应执行双重标准。”
那么,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谁有权力定义“恐怖主义”?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我们在面对查理周刊事件、伦敦和马德里地铁的爆炸案时,似乎很难质疑 “恐怖主义”一词的确定含义:它是一种绝对的恶行,是少数能将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打击的敌人。然而,“恐怖主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如此清晰。

2015年7月,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名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闯入当地一座非裔社区教堂,开枪杀死9人。后续媒体报道无一将此事件定性为 “恐怖主义袭击” ,这引发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假如这名枪手是穆斯林,那么这起枪击案毫无疑问会被定性为一场 “恐怖袭击” 。
在恐怖主义研究领域内, “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斗士” 已经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而当我们意识到 “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界限模糊、所指不定,或许是时候对其进行一次溯源了。在溯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恐怖主义诞生于欧洲,在法国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向——从政府对公民的暴力变成了公民对政府的威胁,而后又加入了反殖民的色彩,即使是对于美国这样的长期话语制定者而言,恐怖主义的指向也在随外交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变换。而当“例外状态”不断日常化,生活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交织的现实中的普通人,面对暴力,已成为了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的“神圣人”。
在今天,人们倾向于将“恐怖组织”一词与中东局势联系起来,认为其主要指代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等极端宗教主义圣战者。然而“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其实最早发源于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其含义和所指在之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几经变迁,直到近40年才与极端宗教思想产生联系。
美国雪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维雷纳·艾伦布希-安德森(Verena Erlenbush-Anderson)在《恐怖主义的谱系学:革命、国家暴力和帝国》一书中,以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了“恐怖主义”概念的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恐怖主义”的概念在全世界不同的语境之下有着不同的发展——艾伦布希-安德森所梳理的谱系绝不是其唯一的发展路径,但对我们理解目前美国主导的恐怖主义话语有着极大启发。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热月党人让-兰伯特·单临安(Jean-Lambert Tallien)使用的。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月后,单临安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反思革命政府的执政原则。也正是在这个演讲中,单临安第一次使用了 “恐怖主义”(terrorisme)这一概念,来称呼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 下的革命政府。
罗伯斯庇尔本人的确曾使用“恐怖”(terreur)一词来表达他的革命和执政理念。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人人都能在正义法律的统治之下,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在他看来,只有卢梭式的、由公共意志统治的全民政府 (popular government)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确保全民政府有效运转、不被腐化的关键在于美德(vertu)——这美德是对于祖国及其法律的热爱,是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考量,以及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统一。
然而,罗伯斯庇尔认为,当时法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为了保护用美德和理性领导人民的新生共和国,用恐怖手段对待国内外试图瓦解共和国的敌人仍然是必要的。
“如果说全民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主要动力是美德,那么在战时就是美德与恐怖:没有美德的恐怖是灾难,没有恐怖的美德软弱无力。恐怖就是即时的、强硬的、没有回旋余地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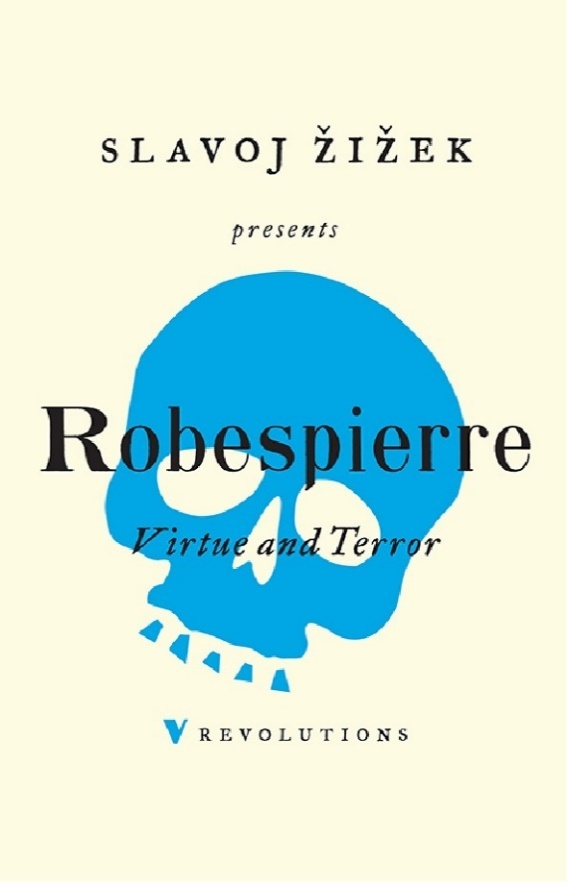
罗伯斯庇尔对于战争状态的判断以及有关恐怖手段必要性的论述,正是单临安在其演讲中反驳的重点。在单临安看来,人民的头号敌人——皇权及其追随者——已经被推翻,使用恐怖手段不过是延续战争状态、制造更多恐怖。单临安将这种制度称为“恐怖主义”,明确指向罗伯斯庇尔个人的政治理念和策略。
热月政变发生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办报人巴贝夫(Babeuf)希望雅各宾专政的结束能够使得1793年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及自由最终得到落实。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当解散热月政府的公众请愿遭到回绝,巴贝夫意识到热月政府与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并无不同。他犀利地指出:“热月政变摆脱的仅仅是一个死人,或是一个暴君;但这场所谓的革命并没有改变暴君制度,只是换到了另一群人手中……废除暴君却不推翻暴君制度,又有什么意义?” 在巴贝夫的指控中,“恐怖主义”所指代的已经不仅是罗伯斯庇尔或热月党人,而是任何无法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政治制度。
“恐怖主义”含义的又一次转向发生在1795年——共和三年宪法出台和督政府成立前夕。为平息社会动荡,“保皇派”和“恐怖分子”被视为革命所面临的双重危险。在越发激烈的党争中,恐怖主义所描述的不再是某种政策或政府机构,而是个人的政治立场或身份。随着党争发酵,热月党人的任何反对者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无论其是支持雅各宾派、持有某种政治观点还是参与了反叛行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恐怖主义一词就从政府对公民的暴力变成了公民对政府的威胁,成为区分“好公民”与“坏公民”的工具。
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是恐怖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在民族问题之外更涉及种族、文化与宗教上的冲突。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动荡成为法国在19世纪进行殖民扩张的动力之一。殖民扩张的支持者认为,法国境内穷人、流氓、罪犯等群体应该被安置到海外殖民地,从而保证本土秩序稳定。然而,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敌意和抵抗是前所未见的。1841年,托克维尔前往阿尔及利亚考察,发现殖民者所面对的并非传统战场上的敌人,而是种族之间的矛盾。
托克维尔记载,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居民主要是卡拜尔人和阿拉伯人。卡拜尔人是柏柏尔人的一支,居住在阿特拉斯山脉。比起阿拉伯人,他们从外貌到生活习惯上都与欧洲人更接近:他们有着绿眼睛、浅肤色,头骨形状也与欧洲人相似;他们过着定居耕种的生活,家庭也按照专偶制形式来组织。至于阿拉伯人,托克维尔则做出了如下描述:“如同所有的半野蛮人一样,他们崇拜权力和力量、鄙视贸易和艺术,他们热爱战争、排场和骚动……他们行为过度,总是感受多于思考。”在他看来,卡拜尔人比阿拉伯人更加先进,后者的社会发展程度仅仅达到欧洲中世纪水平。
由此,法国殖民者建立了一种文明的秩序,即与欧洲越相似的文明就越发达。线性发展的历史观也为殖民者们提供了殖民的道德正当性——为了帮助落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学家马尼亚·拉兹雷格(Mania Lazreg)指出,二战之后涌现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一种“颠覆性战争”,撼动的不仅是殖民主义政治秩序,更挑战了欧洲建立的整个道德秩序。
在殖民者看来,恐怖袭击是这种“颠覆性战争”中的新型武器,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应用显得尤为突出。1956年6月19日,两名阿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在狱中经历种种折磨后,在阿尔及尔被送上断头台。这引来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报复。解放阵线领袖沙迪·雅希夫(Saadi Yacef)下令屠杀除女人、小孩和老人之外的所有18-54岁之间的欧洲人。6月21-24日之间,雅希夫的部队共杀死49名欧洲平民。8月,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区内一栋民族解放阵线居住的房屋爆炸,附近居民也受到伤害。共有70名穆斯林在此次爆炸中丧生,而策划此事件的是曾任阿尔及尔警长的法国人安德烈·阿奇亚里(André Achiary)。9月,在法国摩勒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和平谈判破产后,阿尔及利亚人开始针对欧洲人居住区实施更大范围的爆炸袭击。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被授予军事统治全权的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在回忆录中谈到,恐怖袭击不是阿尔及尔之战以后才出现的新武器,但恐怖袭击在战争中系统性、大规模使用却是新现象。即使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恐怖袭击也只是个别事件。阿尔及利亚人采取的这种系统性恐怖袭击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慌和混乱。
马絮将恐怖主义与犯罪、军事冲突和非常规战役区分开来,是现有的刑法与战争法都无法涵盖的例外领域。一般犯罪发生于主权国家内部的民事领域,军事冲突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而即使是游击战等非常规战争,也不过是战争中的一方掩盖了自己的身份或行踪。但恐怖袭击攻击的对象都是不设防的无辜平民,由此,恐怖主义彻底打破了战争的规则,凌驾于法律之上。
然而,在阿尔及利亚人看来,法国殖民者对他们发动了一场长达一百年的战争;在殖民统治的监视与高压之下,恐怖袭击是他们仅剩的反抗途径。不仅如此,所谓“恐怖主义手段”在战争中的应用其实也并不新鲜。反帝国主义文化批评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英译本题为《垂死的殖民主义》)中敏锐地指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所采取的行为策略与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组织并无不同;炸弹袭击、破坏铁轨等行为都是法国抵抗运动士兵在纳粹德国占领下曾经采用过的反抗手段。阿民族解放阵线与法国抵抗组织所处的境遇也类似,他们所反抗的同样是非法占领——只不过一个来自法国殖民者,一个来自纳粹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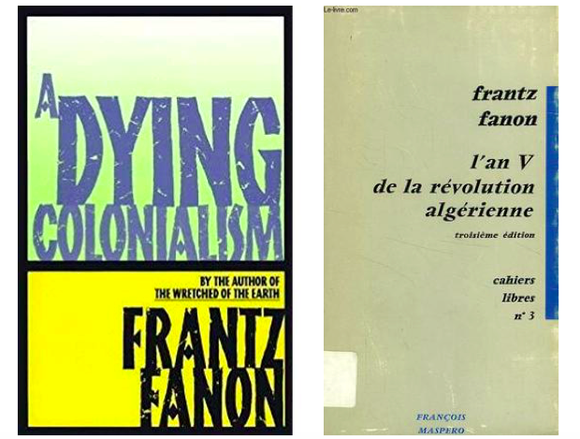
“恐怖主义”在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发生了两种尤为重要的转向:一方面,它隐含着殖民统治下的政治与道德秩序,而恐怖主义试图从政治或文化上颠覆这种秩序。或许正因为如此,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才被视为恐怖分子,而反抗纳粹德国的法国抵抗组织则不会。另一方面,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一种暴力行为凌驾于刑法和战争法之外,既不是犯罪,也不是战争。
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于当下恐怖主义研究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美国军方在反恐新行动中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2003年8月,五角大楼组织了一场特别放映,影片是意大利导演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于1966年执导的《阿尔及尔之战》。这部电影以接近纪录片纪实的手法,展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中最著名的这场城市游击战。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领袖雅希夫也有出演并参与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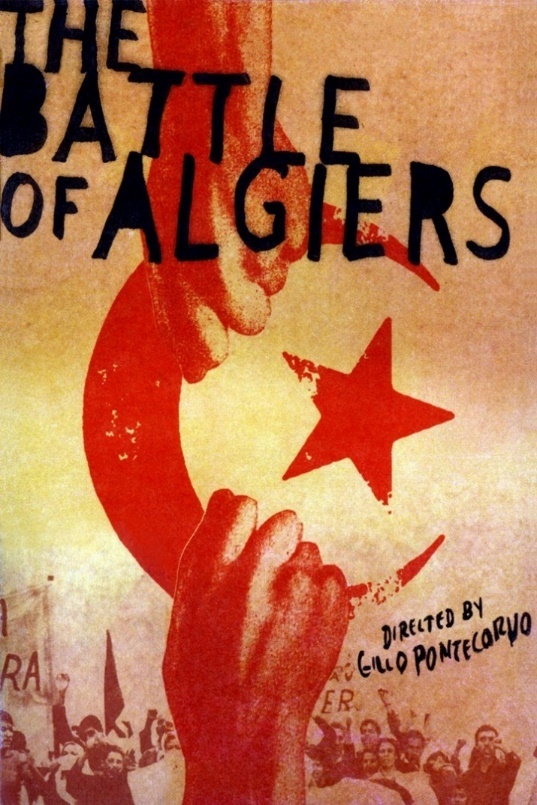
五角大楼这场特别放映的宣传语写道: “儿童在街角突然向士兵射击。女人在咖啡馆里埋下炸弹。很快,所有阿拉伯人都陷入狂热。听起来熟悉吗?法国人有办法应对。他们在战术上成功了,却在战略上失败了。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请来参加这部电影的特别放映。”拉扎雷格指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阿尔及利亚革命即使不是灵感来源,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当然,美国所面对的恐怖主义并不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冲突的简单重复,我们必须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情境下对其做出理解。
197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上台,通过一切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而阻碍这一进程的对手,都可能构成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直到苏联解体后,美国反恐的矛头才由共产主义转向极端宗教思想。一些如今臭名昭著的 “恐怖主义组织” ,例如塔利班,也仅仅是从那时起才登上美国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在198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塔利班还因其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占领而被视为 “自由斗士”“值得支持的盟友” 。
在今天,“恐怖主义”除了定义模糊之外,其边界也有扩大的趋势。这不仅仅由于霸权对于“恐怖主义” 话语的垄断,其背后还有着更加复杂的成因与更加深远的影响。
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行动往往都凌驾于常规法律之外,而法律的悬置为不受约束的暴力提供了正当性。正如马絮在回忆录中指出的,现存刑法与战争法都无法理解或规范恐怖主义行为,这种说法与德国政治哲学、神学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imitt)所讨论的“例外状态”遥相呼应。
在1919年出版的《政治神学:新主权概念四论》一书中,施密特提出,国家主权的本质并不在于对于规则和强制力量的垄断,而是对“例外状态”决定权的垄断。在题为《如何理解全球政治中“例外状态”的“常态化”》的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旭在解释“例外状态”这一概念时讲到:“‘例外状态’是法律规范所无法容纳和规定的政治实在,法律可以统摄社会生活的绝大多事物,但无法完全应对‘例外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法律规范的理性力量无法延伸到紧急状态的情况,在紧急状况下必须做出决断。”而划定 “例外状态”与常规法律的边界,以及在例外状态下做出决断,都是主权者权力的体现。
尽管施密特由于曾加入纳粹党而受备受争议,近年来学术界却越来越认识到其思想的重要性;他的许多论断,尤其是“例外状态”,在当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现实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回响。
9·11事件一周后,美国国会通过的“911决议”(911 Resolution)批准总统采取“一切必要且合适的军事行动”。由于草案中没有对何为“必要且合适的军事行动”进行具体说明,时任总统布什实际上在确定打击对象和决定打击方式两个方面都有着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今年1月,特朗普同样是绕过国会,直接授权军方对伊朗“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实行了军事打击。
在有关“例外状态”的政治学、法理学讨论背后,或许有其社会心理学根源。正如霍布斯将国家政体与个人身体做比,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进入“例外状态”的情况下,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以及实施的暴力,或许能够与个人恐惧所激发出的自卫行动相类比。在《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一书中,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讨论了恐惧情绪是如何作为宗教和道德的动力来运转的。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恐惧情绪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战斗或逃跑等行为的行动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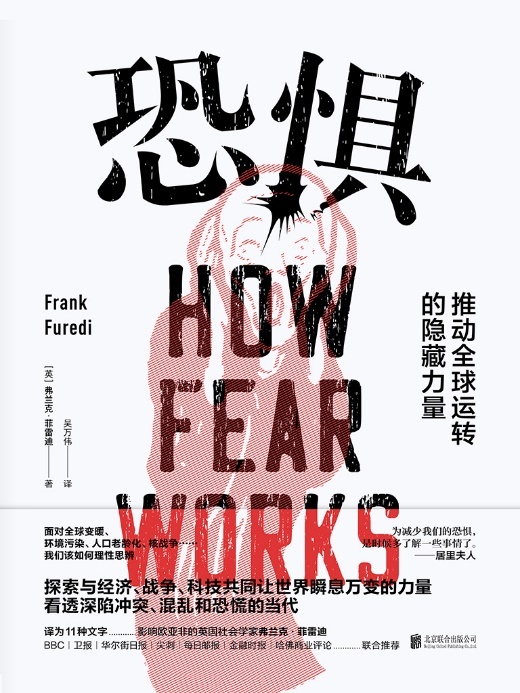
正如“例外状态”独立于法律,恐惧情绪所激发出的个人行为也往往不受理性思维的控制。以色列导演、制片人B.Z.戈德堡(B.Z. Goldberg)的作品以反思巴以冲突、探寻解决冲突的其他出路著名,但他也承认,在恐惧面前,所有这些理性反思恐怕都会灰飞烟灭。在一部名叫《福特传顺》(Ford Transit)纪录片中,戈德堡坦诚地说道:
有一种迷思是,他们(巴勒斯坦人)都想把我们(以色列人)扔进海里。也许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真有一部分是假,但我们害怕得要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害怕。无论何时、无论任何事情触及到这种恐惧,我们会立马做出强烈的回应……这真的就是问题所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只能像个坏了的唱片机一样,不停地说些我脑子里认同的话,以色列人必须离开占领区,我们必须建立两个国家,我们必须追求平等……诸如此类。但我并不相信它们真的会发生!我的恐惧比其他人的权利更重要吗?当我在脑子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自我审视的时候我会说,当然不!我必须要控制我的恐惧,我必须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我的恐惧。但是从情感层面上讲,是的!我的恐惧就是最重要的!任何威胁到这种恐惧情绪的人都可以下地狱了。
通过将敌人形容成对于国家安全、个人安全的威胁,虽然能够为暴力的使用提供一定的正当性,但由此召唤出的暴力并不受法律和理性的约束。将“恐怖主义”概念泛化,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除了失控的暴力,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构成的“例外状态”下的生活同样值得我们反思。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借用古罗马法律中“神圣人”(homo sacer)的概念来描述“例外状态”下人们的生命状态。
罗马法禁止神圣人在宗教仪式中被献祭,但是杀死神圣人却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神圣人可以被任何人杀死而不必承担责任。在澎湃新闻的《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潜能性、赤裸生命等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一文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民安解释认为,“神圣人”字面意义上是神圣的,但实际上是最卑贱的生命,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和政治保护权,最终沦为动物生命或“赤裸生命”(bare life)。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异党、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人,还是从20世纪至今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这一大而广的概念产生威胁的个人及团体,都成为了可以被正当地杀死的“神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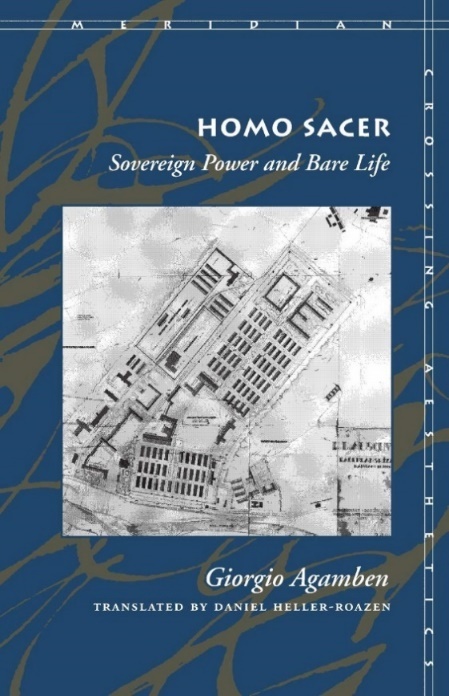
当 “恐怖主义”一词变得边界模糊、无所不包,我们所要警惕的远不只是话语的霸权。其中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反思和控制被恐惧激发的暴力?是否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交织的阴云之下,成为了只拥有赤裸生命的“神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