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幸存者”取代“英雄”成为了喝彩的对象,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均受到威胁。

按:末日来临?暴力事件?子女早逝?人们恐惧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感到恐惧?恐惧情绪四下滋生,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甚至文明?在《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一书中,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弗兰克·菲雷迪指出,虽然无法比较现代人心怀的恐惧是否比过去人更多,但可以认定的是,现代的机构和文化都陷入了极度恐惧之中,甚至“心怀恐惧已经成为了当今半官方的公共教义”——人们被持续不断地提醒要小心翼翼避免冒险,要听从形形色色的专家给出的五花八门的警告。与恐惧文化相关的是,悲观论调层出不穷,“丧失信心”“丧失胆量”“丧失自信”等说法越来越常见了,这也表明了社会对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感到焦虑和紧张。
在这本书的结语部分,弗兰克指出了人类“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的几种可能路径,其中一点便是对历史记忆、对英雄主义、对生存叙事的重新审视。他指出,人类有一种清楚可辨的倾向,即“揭穿”那些暗示英雄主义大无畏行动和利他主义牺牲的历史叙述的假面,并解构长期以来被人们珍视的价值观,诸如勇气、英雄主义和忠诚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叙述中,“幸存者”取代“英雄”成为了喝彩的对象,我们审视历史的方式受到了恐惧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正体现在把当今生存第一主义心态投射到历史场景中的做法——“从历史英雄向历史幸存者的焦点转移反映了脆弱性变成恐惧文化核心特征的趋势,”弗兰克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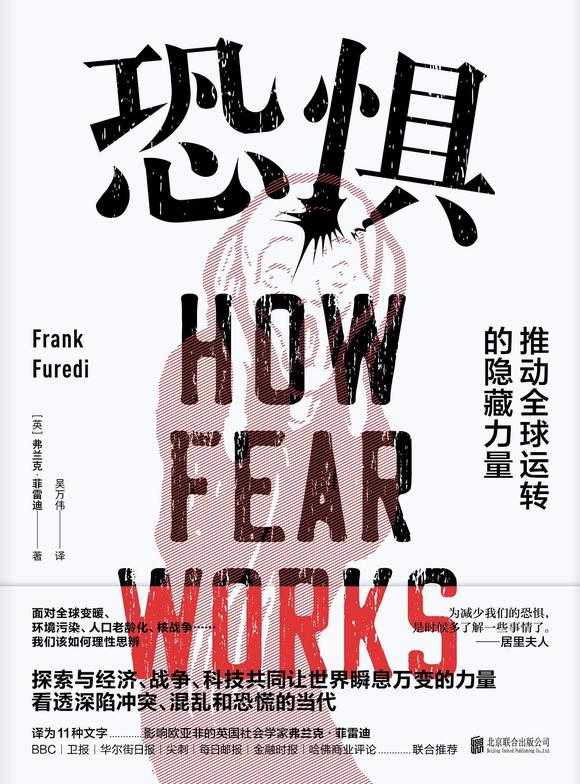
人类要如何与自身的历史相处?历史上的英雄主义能够帮助当代人克服恐惧吗?幸存者与英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下面这段节选中,我们可以找到弗兰克给出的答案。
文 | [英]弗兰克·菲雷迪 译 | 吴万伟
被当今恐惧文化工程向未来投射的末日目的论受其悲观主义和对历史愤世嫉俗所滋养。在弗洛伊德期待恐惧概念的当代版本中,社会对未知的未来危险重重的世界产生了焦虑。人类似乎只能袖手旁观,根本无法改变未来命运。然而,恐惧文化还鼓励社会通过恐惧棱镜来解释过去,由此培养的心态是将过去视为一连串可怕、愚昧的连续事件,人类在其中不仅缺乏方向和目标,而且欠缺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素质。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预防精神可以把当今的许多担忧投射到过去;它还竭力将人类的脆弱性呈现为人生的永恒状态来为当今的恐惧文化辩护;它还传播了对历史解读的怀疑,歌颂英雄主义和英勇行为统统遭到它的冷嘲热讽。
21世纪的心怀恐惧者是过去时代祖先的天然继承者的这一主张背靠当今版本的历史叙述而被频繁提出。人类有一种清楚可辨的倾向,即“揭穿”那些暗示英雄主义大无畏行动和利他主义牺牲的历史叙述的假面,并解构长期以来被人们珍视的价值观,诸如勇气、英雄主义和忠诚等的意义。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所说:“亨利五世于1415年在阿金库尔击败法国人这一决定性胜利,以及莎士比亚使用著名的‘兄弟连’对它的描述,现在统统被认为是有关战争荣耀的‘百年欺骗’,民众都被无情地忽悠了。”

英雄主义经常遭到嘲弄或者被贬低为不真实的东西。一种新型的流行文化和历史叙述致力于揭露过去英雄肮脏的“人生秘密”。有关英雄主义的主张遭到贬低和蔑视。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都被描述为有缺陷的家伙,最坏的情况则是被指责为贪婪追逐权力的骗子。《纽约时报》前文学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说,“以前我们宣扬英雄”,但“现代人的做法是把英雄庸俗化”。美智子认为,传记已经变成一场血腥的运动,冷酷无情地把主人公打得头破血流。 把英雄从神坛拉进人间自然让我们进入这样一种文化中,即认定责任、牺牲或冒险都是违反人性的。在众多叙述中,英雄主义被弃之如敝履,是过时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老古董。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在其书《勇士精神》(The Warrior Ethos)中所言,“我们往往从‘英雄人物’完整的生活中撷取片段用以论证自己怯懦、渺小的合理性,并因此心安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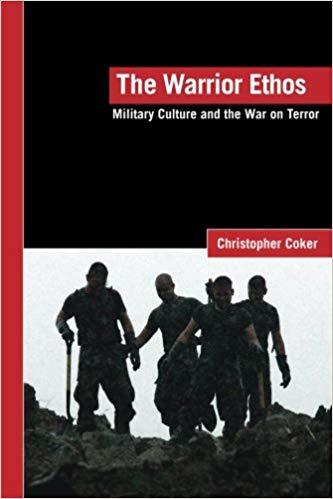
恐惧文化对历史的影响也体现在把当今生存第一主义心态投射到历史场景中这一做法。在众多叙述中,“幸存者”取代“英雄”成为喝彩的对象。科克尔说:“在当今后英雄时代,生存才是真正有道德或情感价值的行为。”
这种反英雄编史往往使用心理学解释来揭露和谴责它所想象的遭受无休止伤害的过去。从历史英雄向历史幸存者的焦点转移反映了脆弱性变成恐惧文化核心特征的趋势。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撰写历史围绕的关键主题是希望宣扬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文化的独有的伟大。民族神话都是有关英雄事迹和光荣壮举的。这些神话不仅被用作称颂过去的材料,还被用来构建人们对未来的憧憬。美国拓荒者神话为社会书写出伟大的命运蓝图;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族神话则用来展现未来无限的可能。今天,历史的撰写则受完全不同的冲动驱使,将过去重塑为“糟糕的旧时代”的工程取代了从前神化“过去的美好时光”的趋势。
历史上的反英雄主义转向的特征之一是负面陈述过去,将其描绘成一段充斥着无止境的人类罪过和苦难的故事。其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回溯历史时重新发现当今时代的脆弱性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状态。鼓吹历史的这种治愈性转向的人认为,人们过去和现在一样情感脆弱、容易受伤,但他们缺乏现在这样的复杂心理意识来理解和诊断心理健康问题。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拒绝接受事实”。现在真的有这样一个产业专门为曾经遭受创伤的人做回顾性诊断。
21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很难承认,过去的人其实是在一套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的指导下经历苦难和困境的。历史声称过去的人用勇敢和坚韧来应对艰难和不幸,现在此说法却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受到蔑视——人们更强调21世纪人们对待危难的态度,而忽视了过去的人如何为了生存而拼搏。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从前的价值观体系赋予了痛苦和磨难意义,人们因而可以应对这些痛苦,心灵不至于受到创伤。
一直到最近,历史学家都忽略或低估了心理健康问题潜在的传播疫情——这种论证常常被用来为撰写的历史辩护。以1966年阿伯芬(Aberfan)的毁灭性灾难事件为例。这是战后英国最具破坏性的工业灾难之一,煤炭尾矿滑坡吞没了威尔士阿伯芬村的学校,造成116名未成年人和28名成年人死亡。当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卫生专业人士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计,这场灾难会压垮这个威尔士小村庄。然而,观察家对村民重建家园和恢复常态的速度感到震惊。例如,仅在灾难发生两周后,幸存的学童就重拾课本,村民们倾向于依靠自己的方法应对悲痛和苦难,这让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无从下手。

灾难发生一年后,威尔士大学的一名家庭和儿童心理学家玛丽·艾塞克斯(Mary Essex)注意到幸存的学童看起来很正常,似乎已经从惊恐中恢复并调整好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总结说:“村民们的灾后重建效果很好,几乎没有接受外界的帮助。”此一时彼一时。该事件过去25年之后,有些评论家对1966年的阿伯芬矿难事件持怀疑态度。在2000年出版的《阿伯芬:政府与灾难》(Aberfan: Government and Disasters)一书中,伊恩·麦克莱恩(Ian McLean)和马丁·琼斯(Martin Johnes)曾明确质疑对灾后威尔士小村报道的可靠性。他们担忧灾后重建是否真的完成。他们猜想“当时,威尔士小村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灾难的长期性影响”,并明确表示“随后的研究的确表明阿伯芬小村很可能受到灾难造成的深远影响”。
当今对人类脆弱性的叙述主导着历史记忆。那些将人性脆弱观念内置化的人很难理解威尔士煤矿小村迅速恢复和适应等行为。评论家们不去探索其适应能力的源头,反而更多地将幸存者视为隐性受害者,认定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的情感需求找不到释放出口。
回顾性研究可以为解释实在发生之事提供一些有用的深刻见解,但是对解释当时人们对逆境的感受没有发挥太大的指导作用。它们既不能用来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个人对逆境做出特定回应,也无法提供洞悉过去人们内心生活的深刻见解。沉浸在历史中拼命寻找蛛丝马迹来证明过去的幸存者同样患有如今已经非常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过是为恐惧文化的典型态度辩护罢了。通过用如此阴暗的、反英雄的方式描绘人类历史,人们为当今的时代精神辩护。末日目的论只有依靠只盯着人类的失败和过错而忽视人类的成就和遗产的历史记忆才能维持下去。正是依靠在对人类局限性和被动性的意识支配下的文化想象,人们对人生的宿命论情感不仅被向前投射到未来,还被向后投射到过去。
几千年来,人类影响自身命运的潜力一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辩论的焦点议题。当罗马人创造出“幸运之神垂青勇者(Fortune favours the brave)”这句话时,他们表达的是对人们运用主观意志塑造美好未来的能力的坚定信念。随着启蒙运动兴起和科学知识开始发挥支配性影响力,相信人类的创造性和变革潜力的观念兴盛起来。现如今,这些观念却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威性。虽然现代社会远比以往更加依赖科学和知识,但我们对它们的宣扬和肯定都远远赶不上在19世纪或20世纪所做的。
当今社会其实并不怎么重视知识和文化遗产。有些历史学家声称,欧洲人在心理上刻意与过去保持距离,甚至到了不需要历史培养身份认同的地步,他们不再依靠历史来认清自己是谁。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梅耶尔(Christian Meier)说:“很显然,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已经被远远抛弃在脑后的历史的幸存者,他们并不把历史视为安身立命之根基。”他接着说:
他们并不乐于参与历史(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以更好的方式)。因此,对于祖先千辛万苦取得的成就,他们并不感恩戴德。相反,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并不理解(和正在竭力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事情上,如战争、不公正、女性歧视、奴隶制等现象。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历史脱节,总的来说,他们越来越无法想象历史的严肃性。
梅耶尔用欧盟对摆脱欧洲历史的企图作为证据来证明这种趋势。他说:“据我所知,欧盟正在成为现代第一个不需要自身历史和历史定位的政治实体。”
社会与其历史和文化遗产越来越疏远,这对人们理解和看待未来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过学习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来指导自己应对未来挑战:对历史以及历史所提供的意义网络的理解在帮助人们克服恐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文化遗产还包括信仰责任、勇气和自由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培养人们在面对威胁时能采取更明智的取向至关重要。重新思考这些价值观并拿来当作自己的价值观将帮助我们形成一种更自信的未来观。
历史描述往往贬低人们尽职尽责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这显然有利于风险规避。这种态度是恐惧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指导人们向命运低头,在此情况下,人类的确无力阻止定时炸弹的爆炸。难怪恢复历史记忆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充当解毒剂,用以消除仅以恐惧视角感知未来这一单一维度倾向的毒害。

严肃对待过去并不要求社会不加批判地将“过去的美好时光”浪漫化。社会需要的不是美化过去,而是具有历史意识的视角。正如我们对恐惧历史的反思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应对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方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历史意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应该对这些变化负责:人类过去通过在今日看来是迷信的实践活动勇敢面对遭遇到的威胁,后来,人类逐渐明白,他们创造的宗教与赋予恐惧意义的需求间接相关。从18世纪开始,许多人得出结论,理性和科学就是掌握恐惧最有效的工具。从那时起,人类就或采用或拒绝了无数应对不确定性和恐惧的策略。
历史意识证明了恐惧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并帮助社会找到一种更具创造力和活力的方法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开明的社会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并研究如何发挥文化遗产的精华,帮助社会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最重要的是,若要对抗占支配地位的宿命论思想,驳斥令人沮丧的历史观至关重要。
人类的历史并非令人羞愧之事。古希腊负责让人类习得哲学精神,并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科学的大门。西方世界从犹太教和基督教那里获取了一系列至今仍被奉为理想的道德原则。我们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对法律和法律体系的珍视——正是这些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安全和秩序。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现,自由理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原则。古代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智慧与基督教哲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有机结合帮助巩固了人们对大胆尝试的开放性态度——正是这些尝试使得理性和科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尽管历尽挫折,人类毕竟学会了如何应对形形色色的挑战。
历史是阐明人们如何驯服恐惧并勇往直前的重要知识性资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真正创造历史的里程碑事件:人们利用古人的经验质疑当时盛行的假设和偏见。吸取历史教训能帮助激励新一代在面对未来时,采取更加积极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无所畏惧的勇敢态度。
书摘部分节选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