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对美国和世界的前景曾有乐观的预想,站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他还能认出这世界吗?

惠特曼(来源:yahoo.com)
按: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惠特曼诞辰二百周年。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当我们二百年后回顾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惠特曼?对于当代诗歌、当代生活,惠特曼能给予怎样的启示?事实证明,惠特曼仍可以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
文 | 秦立彦(《读书》2020年1期新刊)
惠特曼对美国和世界的前景曾有乐观的预想,站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他还能认出这世界吗?他所热烈歌唱的美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闪光,他预言的人类共同的乌托邦也并未到来。如果他目睹了“一战”与“二战”,他会怎么说?在《荒原》之后,在卡夫卡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惠特曼?
惠特曼作为诗人的很多品质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现代诗人大多敏感、孤独、悲伤、脆弱,而从《草叶集》中浮现的惠特曼骄傲、勇敢,充满能量和希望,不迷惘,不虚无,有明确的目标和自我身份。他的健旺的语气,与比他小十岁左右的狄金森很不同。惠特曼少有异化的感觉,他在大自然里和城市里都如在家中。华兹华斯书写了大都市伦敦的异化感,而惠特曼自豪地称纽约为“我的城”(my city)。走在城市的人群中,他没有陌生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同伴,他没有社交恐惧症。他拥抱现代性,拥抱现代机器。在他看来,“现代”这个词是英雄性的(the heroic modern),是应当歌颂的,而“现代”的前沿与代表就是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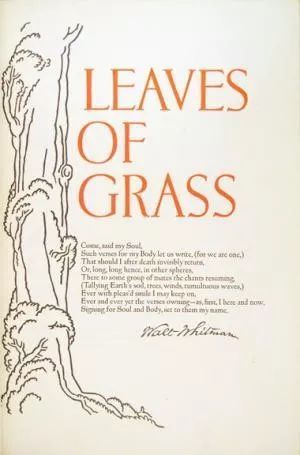
惠特曼笔下的劳动不异化、不辛苦,劳动者都强壮。他参与了美国南北战争(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志愿的医护人员),目睹了惨烈的伤亡,但这并未打消他的热情。战后他没有感到幻灭,也没有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笃信自由、平等、民主与个人,相信这些将最终胜利。
钱锺书从“兴观群怨”的中国诗学中,提取了“诗可以怨”这一条古今中外名诗的特点,就是诗歌主要用以抒发郁结,这样的诗也容易写好。钱锺书援引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一种依据:文艺是作者日常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的替代。钱锺书所引的清代陈兆仑之言尤其具有启发性:“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浅深别矣。”“诗可以怨”是在中外文学中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惠特曼却是一个醒目的反例。然而作为纽约人、当代人,难道他没有感受到当代人的忧郁与危机?他如何以诗歌处理个人际遇,尤其是其中的伤痛?
惠特曼的自我定位是美国的国民诗人,扩而广之,是人类的诗人,甚至诗人自身就像大自然一样是无所不包的,神一般的。“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与你没有差别,也就没有隔阂。“我”歌唱自己,也就是歌唱一切人。“每个男人女人都是我的邻人”,“我的同志”(my comrade)。惠特曼与他人合一,他相信,自己要说的也是人人都要说的,他就是人人。他一直关注读者,他的许多诗都是对读者的召唤,虽然《草叶集》第一版销量甚少,虽然至少在较早的时候,大众并不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言人或“同志”。
从这样一个视角,惠特曼作为一个独特个人的品质和他个人的悲喜,在他的诗中就并非很重要。他确认自己的诗歌主题是“事物是多么令人惊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他写道:“我在宇宙中没有看到过残缺,/我从来未见过宇宙中有一桩可悲的前因或后果。”他歌唱人类的集体身份,歌唱一个超越了个人“小我”的自我。他爱自然的部分与华兹华斯类似,但爱人类的部分相当激进。他写自然的部分要少于写人的,人是他最重要的关注点。人人平等的观念使他尊重女性,尊重黑奴,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面。虽然他最著名的作品题为《我自己的歌》,然而这首诗并非歌唱惠特曼自己,而是歌唱每个人的 “自我 ”,也召唤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歌唱。正如他另一首诗的题目是《普遍性之歌》(Song of the Universal),他写的是普遍性,而较少写具体之人或物。
在《草叶集》中,名词常常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惠特曼多次使用“all”这个无所不包的、超越式的、淹没了个体的代词。他有一首题为《一个女人在等着我》(A Woman Waits for Me)的弘扬性爱的诗,诗题里是“一个女人”,而在诗的正文中则写道:“我要做那些妇女的壮硕的丈夫。”(I will be the robust husband of those women.)类似地,他的男性爱人们在诗中也没有名字或具体生平,常表现为复数。
复数,多,是惠特曼的力量之一,他的句法也促成了这样的效果。他的诗歌风格是此前的西方诗歌史上不曾有过的。大量并列的名词、同位语、分词,如同滚滚不穷的海浪(catalogues)。在排比之中,诗行的前后顺序并非固定,在长诗中多一行少一行对全局也没有大影响。他的句法不是碎片与切断,而是难以句摘,有一种贯穿的淋漓之气和强烈的激情。他不甚关心炼字、炼句。甚至许多诗如同同一首诗,是对同一主题多角度的反复表达。我们可以将博尔赫斯诗歌中有惠特曼风的排比列举法与《草叶集》对照,更能看出两位诗人各自的特点。博尔赫斯大量列举静态之物,句子不长,不追求力量,而惠特曼则有一种“奔流到海”般的腾涌。
惠特曼的复数与长篇列举,形成宏大而众多的效果,在这中间,单个人的面目一闪而过。他的诗歌写法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针对具体事物的精雕细琢,如福楼拜做到的那样。我们可以说惠特曼的视角是全景照相机式的,而不是显微镜式的。他很少写一朵花、一只鸟。以他的诗《一只沉默而坚韧的蜘蛛》(A Noiseless Patient Spider)为例,这首十行的小诗写一只蜘蛛,但并非像华兹华斯或狄金森那样对自然界中微物的凝视,而是以这只在虚空中释放蛛丝的蜘蛛,比喻诗人的灵魂在无限空间中寻找落脚之处。蜘蛛在虚空中结网,诗人的灵魂也如此,诗的结尾的声音是有信心和安全感的,仍归于自我。类似地,另一首写于一八八八年的诗《老水手柯萨朋》(Old Salt Kossabone)写自己的一位已经去世的祖先——他九十多岁的时候日日坐在扶手椅上遥望大海,最后一天看见一条挣扎的船终于找到了方向,然后就死去。这首诗的目的也并非记录一位祖先的生平故事,而是以他作为惠特曼自己面对死亡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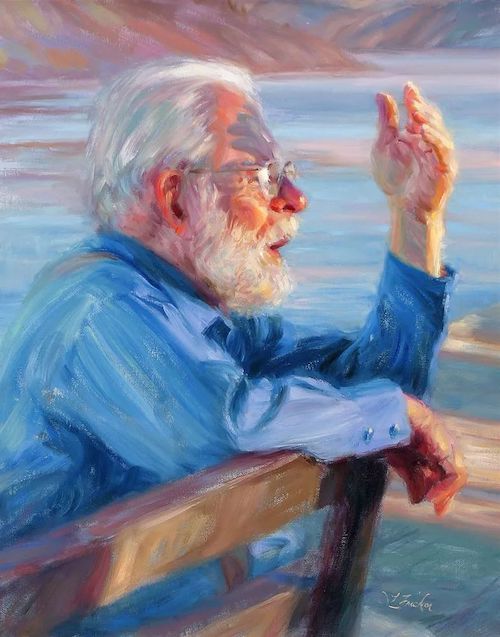
惠特曼的诗具有某种英雄性和公共性,诗人尤其书写失败的英雄:“失败的人们万岁!/战舰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自己也沉没在海里的人们万岁!”在对南北战争的死伤者的描绘中,诗人不只感到他们生命的可贵,也感到北方士兵为之而死的事业的可贵。那种失败就具有了崇高感,诗人本人也被英雄们所激励。作于一八七六年的一首诗《在遥远的达科他峡谷》(From Far Dakota’s Canons ),赞美在达科他州的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中,一百多名美国士兵英勇战斗而死。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诗人的自我:“就像在艰难的日子里坐着,/孤单,闷闷不乐,在时间的浓厚黑暗里找不到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惠特曼对日常生活的阴郁描述,近似于华兹华斯对一些低落时刻的描述。但惠特曼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当代寻找英雄性。在这首诗中,他书写的英雄就鼓舞了他。在此诗的几个段落中,包含着“我”与那些死去的英雄两类人物,英雄在西部的战场,“我”在东部城市的房间里,形成鲜明的对照。勇于赴死的无畏战士,正是他觉得自己应具有的面对生活重负的态度。惠特曼笔下的华盛顿、林肯、格兰特将军也是英雄式的。在英雄主义视角下,日常生活的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惠特曼乐于以士兵自比,为什么他在战后对战争岁月有留恋之意。惠特曼不是反战的。这固然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可以视为一场正义战争、民主国家的阵痛,一种为未来付出的值得的代价,同时也因为恰是在战争中,惠特曼强调的人们之间的同志关系(camerado)能够实现。《列队急行军与陌生之路》(A March in the Ranks Hard-prest, and the Road Unknown)一诗,非常真切地书写了战地医院里的情景、气味、死亡。在美国诺顿出版社二○○二年版的《草叶集》中,编者对此诗中的战地场面颇为赞誉,加脚注说这些描绘很“现代”,不亚于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和海明威。但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是,惠特曼所写的战争是正义的,在正义战争的框架下,血腥与残酷可以得到解释,而不导向绝望与虚无。

惠特曼也多次写到死亡。他关于死亡的诗时间不一,显然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主题在他晚年的时候尤为凸显。虽然他没有明确的关于死后的主张,但对于他而言,死亡不是终结。一八八八年的《将结束六十九岁时的一支颂歌》(A Carol Closing Sixty-nine)一诗中,他说自己身体虽然衰残,但欢乐与希望之歌仍将继续。他的这种态度使他能够承受死亡的到来。一八七四年的《哥伦布的祈祷》(Prayer of Columbus )以哥伦布的第一人称书写,而哥伦布显然也是惠特曼。诗中“我”老朽失败,但仿佛看见“在远方的浪头上航驶着无数船只”。作为熟悉纽约和大海的诗人,惠特曼多次以水手、船、航行等意象,将死亡比为重新出海。惠特曼以英雄主义和探险者的身份对待死亡。虽然他不舍此生,但死后未来的不确定性变为一种期待,死亡是另一种开始。

除了战争、死亡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或许更难以乐观处理的是当代平庸的日常。惠特曼的诗是诚挚的,但不包含很多的个人色彩。在《草叶集》中,人类的每一分子都是诗人的朋友,但他写具体人物的诗并不多,最突出的就是写林肯总统的,亦有写格兰特将军的(格兰特战后也担任了总统)。林肯与格兰特都是公共人物,并不是惠特曼私人生活中的人物。惠特曼很少在诗中具体写到他的父母、爱人、朋友、兄弟。他仿佛与一切人都亲密,而并没有固定的亲密者。
在《有那么一个孩子出得门来》(There Was a Child Went Forth )一诗中,惠特曼列举各时节的自然风物与人,并很罕见地写到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健壮,过于自信,男子气,难对付,发脾气,不公正,/打人,尖锐地大声骂人,苛刻论价,诡计多端。”在这里我们仿佛窥见了惠特曼的秘密,找到了他原生家庭的缺陷,然而这一点私人信息埋藏在他的大量列举之中,父母在众人众物之中并不醒目。惠特曼在母亲去世八年后,有一首纪念自己母亲的十行小诗——《死亡也走到你门口时》(As at Thy Portals also Death),写自己的母亲“那理想的女性,务实的,富有精神性的,对我说来,在所有大地、生命和爱情之中是最好的”。但这样一个完美的母亲在惠特曼的诗中很少露面,只有这一首小诗是专门为她而作。

虽然惠特曼不断提到“我”,大部分诗都采用“第一人称”,但他并没有在诗中融入很多的个人生平信息。他很少说到自己生活中的具体欢乐烦恼,从他的诗中很难勾勒出他的生平或年谱,连他的个性都是不怎么清晰的。他自己或许也看到这一点。在他的诗《在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As I Ebb’d with the Ocean of Life )中他写道:“真正的我尚未被触及,被说出,完全没有被抵达。”(the real Me stands yet untouch’d, untold, altogether unreach’d.)
博尔赫斯有一文一诗论及惠特曼的作品和他的生平之间的这种差距。博尔赫斯曾翻译《草叶集》,在译序中说,看过“炫目与晕眩”的《草叶集》的读者再去看惠特曼的传记,会有上当之感。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到处游荡,爱人众多,而在生活中他并未去过多少地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博尔赫斯由此认为有两个惠特曼:普通记者惠特曼,以及“惠特曼想成为却并不是的另一个人,一个有丰富爱与冒险经历的人,一个游荡的、热情的、无忧无虑地在美国游历的旅行者”。博尔赫斯的诗《卡姆登,1892》(Camden, 1892)也循着这样的思路(惠特曼一八九二年死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垂死的惠特曼看见镜中老朽的自己,但感到满足,因为“我曾是沃特·惠特曼”。两个惠特曼,与博尔赫斯许多作品中的多重自我类似。博尔赫斯的言下之意是,生活平淡的惠特曼创造出了另一个与自己迥异的文本的自我,作为一种补偿,这也是惠特曼的天才所在,而那个日常的自我在诗歌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博尔赫斯是将惠特曼进行了“博尔赫斯式 ”的解读,正如博尔赫斯在另一首诗里将塞万提斯描绘为忧伤失败、失去了祖国的人。
我更愿意相信惠特曼并非在诗中掩藏了日常的自我。如果我们在一切过往的诗人中都看到一个当代的脆弱失败的诗人,文学版图将趋于平面化、单一化。惠特曼异于当代诗人的部分,也许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另一种资源。

惠特曼也有纯然书写痛苦与焦虑的诗,但很少,篇幅也不长,且不进入细节。《泪水》(Tears)一诗特别沉重,写一个人晚上在海边痛哭,而白天他那么整齐有序(regulated),我们不知此人痛苦的具体缘故,诗中也没有说那人是谁。《然而,然而,你们这些懊丧的时刻》(Yet, Yet, Ye Downcast Hours )中,惠特曼说自己对懊丧的时刻十分熟悉,但语焉不详。在别的诗中,他告诉我们他完全理解那些邪恶的人,因为他自己也“充满邪恶”,但同样没有细节。《你们这些在法院受审判的重罪犯》(You Felons on Trial in Courts)写“我”与那些罪犯和妓女一样,“在这张看似冷漠的脸下面地狱的潮水不断在奔涌”,然而从这首诗看惠特曼并无罪感,而是接受这些底层犯罪者,将他们也纳入世界的神圣秩序。
更多的时候,生活苦痛只在《草叶集》的字里行间出现,较少作为诗的主体。惠特曼的处理方法之一是将其埋藏在长篇的列举中。在《我自己的歌》中,他列举了众多健康的劳动者,包括木匠、农夫、纺织的女子,然而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几个不和谐的人:一个被送进疯人院的疯子,手术台上一个血肉模糊的畸形身体,还有“自杀者趴伏在卧室里血淋淋的地板上,/我目睹了尸体和它黏湿的头发,注意到手枪落在什么地方”。《草叶集》中共有两处提及“自杀者”(suicide),然而“自杀者”并非这两首诗的题目,没有被突出地集中书写,也并不醒目。在《我自己的歌》大量健康的人物谱中,几个不和谐者几乎被淹没,是大幅群像里的几张痛苦的面孔。我想这并非是惠特曼将世界的阴暗面隐藏在诗中,而是在看到这些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许多健康者,他的心思和笔都没有在黑暗的部分过久停留。当诗人的视野放宽,容纳了众多的人与物时,黑暗也仿佛得以冲淡。或以他的名诗《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为例,诗中之人从鸟和大海那里听到的是爱与死的主题,与惠特曼大部分诗中的明亮色彩不一样。此诗加入了鸟的哀声,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这也是《草叶集》从开篇到此唯一一首哀伤痛苦的诗,然而那是一只鸟痛失爱侣,而且那是使一个诗人觉醒的时刻,是他的起步和开始。鸟是诗人的启发者和唤醒者,这也减弱了诗的哀伤。

在惠特曼的几首关于忧郁的诗中,我们瞥见了熟悉的忧郁诗人形象,读到了华兹华斯的很多诗中、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中的那种对尘世生活的抱怨,读到孤独。然而惠特曼很少表达逃世的想法。他没有想变成西风、夜莺,没有在过去寻找梦境。他是未来导向的,不像欧洲浪漫主义者有时指向中世纪的过去,也没有想象到远方无人的幻美之地躲藏。在他的大部分书写忧郁的诗歌,也就是“怨诗”中,他都找到了鼓舞自己的办法。
他有时以士兵的勇敢对待痛苦。《啊,贫穷,畏缩,闷闷不乐的隐避所》(Ah Poverties, Wincings, and Sulky Retreats)列举日常的许多痛苦,最后宣布:“我还会作为一个赢得最后胜利的士兵那样站起来。”他的“怨诗”中常自带解决方案,尤其是老年,当他非常看重的美好身体变得衰朽的时候。《你那欢乐的歌喉》(Of That Blithe Throat of Thine)写一个北极探险者听到一只孤鸟的歌声,诗人也如那被冰雪包围的北极探险者一样,被老迈所包围,但那只鸟给诗人以教导。鸟鸣改变了一切,包括“老年被封锁在冬天的海港内——(冷,冷,真冷啊!)”。《致日落时的微风》(To the Sunset Breeze)中,“我,老迈,孤独,患着病,给汗水浸得筋疲力尽”,但一阵清风吹来使“我”重生。这些诗有杜甫的“秋风病欲苏”之感,甚至题目都不是痛苦的。诗中对老年困境的描写令人动容,但诗人主动突围和自救。惠特曼把诗笔献给那些安慰之物,而并不在痛苦之上过多“逗留”。他是可以安慰的,不沉溺于自怜。

我想,我们不应当将这些品质视为惠特曼的幼稚,或者他“不够现代”。我们所处的现代阶段并非多么令人自豪,我们对悲伤知道得更多,而不是快乐。也许我们可以从惠特曼身上获得灵感与鼓舞,以减轻我们的现代负担。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呼唤勇气和乐观,不过多耽留于悲伤与怨诉,更注目于我们共同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悲喜。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博尔赫斯这位与惠特曼如此不同的诗人,会乐于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而且视惠特曼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