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国际形势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沮丧,但19世纪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书迷早已见识过这一幕了。

福楼拜写道:“我想给读者留下一种极度疲倦与乏味的印象,让他们以为这本书只可能是一个白痴写的。” 图片来源:Nadar / 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我们是否正深陷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真人版之中?
1月3日,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遇袭身亡,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相互矛盾的说法。
苏莱曼尼计划要袭击美国人?美国副总统彭斯错误地断言苏莱曼尼与9·11事件有关又该怎么说?还是像意外寄送到伊拉克政府的信函所说的,美军一直在计划撤军?
特朗普是否只是想要转移人们对弹劾审判的注意力?对于这样一个恶毒的自大狂来说,这次袭击是否只是条件反射式的决定?还是在伊朗连续数月的挑衅之后做出的合理回应?
民主党在为苏莱曼尼之死哀悼吗?还是说他们也要为此次袭击负责?
每一轮的指责和辩解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公众反响和专家意见,大家都在努力纠正这一充满敌意而又无比荒谬的说辞。
许多人可能会为此感到困惑和沮丧,但19世纪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书迷早已见识过这一幕了。
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法国作家福楼拜记录下了自己的沉思:“我们何时才能将事实书写为宇宙中的一个笑话,就像上帝从高处看到的那样?”
他在1857年出版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这本书出版于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一系列的虚假消息和敌对政治派别的支持助益了这位法国总统的独裁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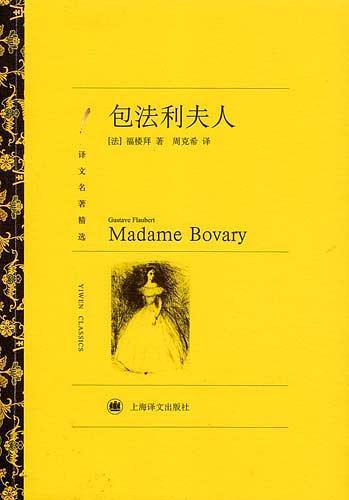
《包法利夫人》的叙述风格是一种故意的无意义,或者正如文学批评家利奥·贝尔萨尼所说,它体现了“语言本质上的随意、呆板、无关紧要”。
故事的主人公爱玛·包法利读过很多浪漫小说,对自己在乡间的平庸生活感到很是失望。她不断地追求刺激与逃离,最终不但与他人偷情被骗,还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这样的故事背景很常见,但《包法利夫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坚信叙述描写、言语措辞都是不可靠的。书中所有的角色,从稚嫩的情夫到善良的老实人,全都免不了老一套的陈词滥调。爱玛和她后来的情人里昂都说自己喜欢海边落日,尽管他俩谁都没去过海边;药剂师郝麦总是告诫别人要谨慎,尽管没有人听他的,他自己也是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小说的结局就是郝麦收到了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里昂告诉爱玛,他死后下地之时,想要用爱玛送他的毯子裹住自己,尽管小说的叙述者揭露了这是句假话。
并不是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在撒谎,一些真挚的角色真的是言行一致的。问题是,语言本身由于缺乏诚意、反复讲述和夸大其词而早已失去了意义。小说中有一个著名场景,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镇上的居民都在专心听着那一长串单调无聊、冗长散漫的农作物介绍:“这里有葡萄藤,那里有酿酒用的苹果,再往前还有奶酪和亚麻!”最后,作为当天压轴活动的烟花哑火了,但报纸还是报道说焰火燃放十分顺利,称其为“名副其实的万花筒,一幅真正的歌剧舞台背景”。没有人在意这段描写是编造出来的。
福楼拜宇宙笑话最终的点睛之笔是,叙述者自己就很善于制造微妙的困惑。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开始讲述故事,把自己定位成艾玛丈夫的一个同学,随后又突然转变为第三人称。他的一些叙述直截了当,不带感情色彩,另一些叙述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对男孩帽子、结婚蛋糕和医疗设备的描述如此详尽,却又如此令人困惑,读者甚至无法想象它们可能的模样。
后来,福楼拜在接下去的文学项目计划中写道:“我想给人留下一种极度疲倦与乏味的印象,让我的读者以为这本书只可能是一个白痴写的。”
福楼拜不是在真空中写出《包法利夫人》的。1851年,他开始写这本小说时,正值当选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一场政变,从总统变成了皇帝。
路易-拿破仑将重要的职位给了他的追随者,提醒士兵们他们曾经许下过“绝对服从”的誓言,并镇压了国会暴动和农村起义。
大约一万名政敌被驱逐流放。维克多·雨果是政变的坚定反对者,逃往了布鲁塞尔,而托克维尔为了避免加入该政权而直接退出了政坛。

法国公民也感到十分困惑和迷茫。1868年,记者兼政治家尤金·特诺撰写了一篇讲述此次政变的报道,他警告读者,“法国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此次事件的真实报道……在动荡时期书写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偏见、夸张、不公,甚至是恶意。”
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称之为“阴谋的温床”。1852年1月,他通过了新宪法,并且一直在指责某些蛊惑人心的人散布“假新闻”。1852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了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始了。
路易-拿破仑被称作是“第一个现代独裁者”,也是“第一个通过宣传进行统治的现代领导人之一”,他从法国第一任民选总统变成了法国最后一个皇帝。第二个帝国持续到了1870年,皇帝意识到自己的声望在不断下降,于是对普鲁士宣战,结果战败了。
法国的政治动荡、假消息战争、不时的起义和公众的困惑可能给福楼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重复、虚伪和愚蠢的无尽漩涡之中,而今天的美国人可能会对此产生共鸣。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技术进步。在过去的十年里,层出不穷的研究都在揭露媒体过度饱和、信息过载、数字图像泛滥,及其对大脑产生的影响。持续的刺激和干扰会导致记忆障碍和思维混乱,政治斗争的时机已然成熟。
媒体研究教授达斯·弗里德曼在2014年出版的《媒体权力的矛盾》(The Contradictions of Media Power)一书中写道,在政治不稳定时期,“当下的叙事都面临着压力,受众自身也在积极寻找新的视角。”信息战和假新闻在政治动荡时期似乎是家常便饭。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正生活在福楼拜所想象的那个宇宙玩笑的极端版本之中。冗长乏味的谎言、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空洞浮泛的哗众取宠让美国人的幻想破灭了,就像书中的爱玛·包法利一样。略万先生在农展会上乏味、怪异的发言如今也有了现代版——想想特朗普散漫的集会演讲,或者想想他抱怨冲厕所难,抱怨风车噪音致癌。目前,共和党众议员德文·努内斯正以诽谤罪起诉一头社交媒体上虚构的牛,另一边,特朗普则单方面“宣战”不会让激进派更改“感恩节”的名称,他的支持者为这次声明欢呼雀跃。
苏莱曼尼遇袭后,人们一如既往地公然漠视真相与现实,就像《包法利夫人》书中呈现的不成句子的话。彭斯提到苏莱曼尼参与了9·11事件,这种论断完全脱离了现实,就像在爱玛的想象中,古罗马废墟旁边有老虎、骆驼、天鹅,还有苏丹和英国女人。
真真假假的消息只会继续有增无减。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伊朗是否会成为21世纪美国的普鲁士。
本文作者Susanna Lee系乔治城大学法语与比较文学教授。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