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埃尔曼凭借长篇小说《纽伯里波特的鸭子》获2019年金史密斯奖。她谈了谈为什么她更欣赏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所写的书,以及她想象中那个非父权制的理想世界。

露西·埃尔曼在她爱丁堡的家中,她说:“我曾想当一名雕塑家。” 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露西·埃尔曼一位是英裔美国作家,著有八本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甜品》(Sweet Desserts)和《咪咪》(Mimi)。她的最新作品《纽伯里波特的鸭子》(Ducks, Newburyport)是一本长达1000页的书,全书几乎只由一个意识流长句所组成,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位母亲的脑中所想:从枪支管制到训练(孩子)上厕所、从她的脚踝无力到“白人至上”,一切都令她担忧。该书入围了本年度的布克奖,并获得了金史密斯奖和10000英镑奖金,以奖励它“为长篇小说的形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卫报》:在你最开始创作《纽伯里波特的鸭子》时,已经计划好了成书的形式吗?
埃尔曼:不,过度计划是行不通的。我的小说都是因为发自内心想写而产生的。当时我坚持的原则就是,写我想写的书。否则,写什么都没意义。
《卫报》:你是如何开始构思这本小说的?
埃尔曼:它是从短语“事实是”(the fact that)开始的:一个黎明,我在一张纸上写满了以“事实是”开头的句子,我喜欢它所呈现的效果。它可以是强调性的,也可以是舒缓而慰籍的,并且它具有悬念:你不知道这个句子会如何结尾。我决心看看能否在整本长篇小说中一直使用这个短语,看起来我似乎可以做到。
开始写作这本小说时,我的想法源于人类对环境的所做所为使我愤怒和绝望。最近一次演讲后,有位女士来找我说:“我真高兴我不是你。”她对我的深度沮丧感到吃惊。我倒是对她的应变能力感到吃惊,以及她对讽刺装聋作哑的能力。
《卫报》:你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埃尔曼:我曾经想当一名雕塑家,但我并不真正享受艺术学院那种冷酷而肮脏混乱的氛围。我缺乏信心。回想起来我认为,人们对女性雕塑家也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偏见,它微妙地损坏了我(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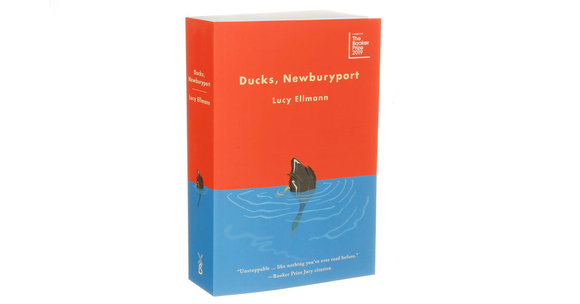
《卫报》:你不怎么读当代小说。为什么呢?你的床头柜上现在放着哪些书?
埃尔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和威尔士作家卡拉多克·埃文斯的短篇小说集《我的人民》。前者与英格兰上层中产阶级角力,后者则是与威尔士。
我发现当代写作的年度庆典——2019年圣诞季书单——相当令人反感。它看上去太自负了。那些书单表明,被选中的书必须是最新出版的。简直愚蠢可笑。人们当然会对新的创作感兴趣,特别是当自己拥有一部本年度的新书时,但是面对现实吧,这是一种营销策略。他们想卖掉一些书,并且这样他们就可以站在“现在的”光环中。但人人都知道,阅读《尤利西斯》、伍尔夫或卡夫卡,会使读者受益更多。《私探》(Private Eye)杂志的商业胡吹式报道无聊透了。那如果有些作家彼此认识怎么办?这很难避免。英国的文学圈很小。前不久,我基本决定只读(二战时,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所写的书,当时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工业革命已经够糟了,但核武器确实是晴天霹雳。
我并没有严格这样做——但我常常感到,在战争和资本主义使我们沦为纯粹的货币单位、炸弹工具,并变得极度自我保护之前,那时人们的想法和文学创作阅读起来更有益。那时自然世界也还没变成塑料和核废料的垃圾桶。
愤怒和疏离已经产生,它们是很好的(创作)主题,但有时你也愿意记住文明史上的更高点,还有尚未被污染的自然世界。例如《项狄传》中深刻的幽默、纯真、性感和戏剧性——它可能在广岛事件之后写成吗?《巨人传》呢?《堂吉诃德》?《爱玛》?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父权制的过错,生而为人已丧失了很多乐趣,而我喜欢那些以较少约束的方式看待生活的书。
《卫报》:关于《纽伯里波特的鸭子》,很多评论家都认真地撰写了文章,同时也竭力强调它的长度、文学特质和挑战性。你对此感觉如何?
埃尔曼:作品的长短不能代表全部。我能够理解那些截稿时间紧张的评论者,但假如你不能驾驭审读某些作品,你总是可以拒绝的。这本书必须写得很长,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但我从来不希望它变得不可理解。某些男性评论者关于该书长度的评论中有性别歧视的痕迹,他们大概还会进一步气恼,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女人,这个叙述者或作者,怎么敢占用我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再谈谈这本书“由八句话组成”的谣言吗?恐怕这是从《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开始的。我不知道“八”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但那篇评论之后,这个消息真的传开了。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错误计算,因为将这部作品写成八个句子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
我打算在我的墓碑刻上“一句话而不是八句话”。那应该能解决问题,对吧?但抱怨那些评论文章,似乎是我太刻薄,而他们大多很慷慨。

《卫报》:在《纽伯里波特的鸭子》中,叙述者(一位母亲)认为:“我现在害怕所有的年轻女性,因为当我看着她们时,我看到了又一个可能仇恨母亲的人,事实上我现在一直想知道,她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妈妈。”你是一位母亲,同时对“母亲身份”既持捍卫态度又持批评态度。你如何平衡这些立场?
埃尔曼:让我担心的是,我偶尔会观察到母女之间的巨大鸿沟。我怀疑父权制是这种敌意的背后推手。当女性相互排斥时,你必须寻找事情的源头,谁在渔翁得利?非常遗憾,因为所有这些女性对女性的愤怒本可以一致对外,以针对女性的压迫者。
我与我自己的母亲曾经非常亲密,并感到母性的力量和意义被广泛忽视了——再一次,为了父权制服务。不过现在我们处于气候紧急状态,越接近零生育率越好。我确实很佩服那些因为环境因素而决定不生育的女性。我认为这是动人、高贵而慷慨的,也是非常明智的。人们并没有充分地谈论为人父母的劳累、无趣、暴躁、费时,昂贵且吃力不讨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继续假装那是一种愉悦?当然,也会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元素:孩子们可爱而迷人,并且如果你有孩子,你就可以再次玩玩具、阅读孩子们的书,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但是,(随之而来)疾病、担忧、冲突、空间拥挤、日复一日的烹饪、驾驶、丧失隐私、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教育的困境、缺乏就业前景,以及所有令人沮丧烦扰的青春期叛逆——这些都是很大的困难。
你看到人们怀孕,然后知道有20年他们将在情感和理智上受到影响。思想、知识、成年人的对话和至关重要的政治行为都可以被搁置,而这种不必要的物种持续繁衍却被优先考虑。生孩子是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可以被原谅的冲动,但这也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就像婚礼或在爆米花上涂黄油一样。
《卫报》:布克奖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你对今年同时授予两位作家奖项,有何看法?
埃尔曼: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五位评委——他们无法达成民主共识吗?但他们决心今年(也)要奖励一位有名的作家,只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公正而合理的投票办法。该奖项的荣耀显然可以变成双倍,而不是一人一半,那样会很好。但是让两位获奖者分享奖金,似乎就不太好了!你究竟为什么要让第一个赢得布克奖的黑人女性只拿一半的奖金?这是严重的错误和缺乏尊重。
而我喜欢注册慈善机构布克奖基金会(Booker Prize Foundation)的原因,在于它与英国皇家盲人协会(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的协议。所有入围的书籍都会为盲人录制成语音读物,而这是一种荣誉。
《卫报》:你的书都是毫不掩饰的、强烈女权主义的。《咪咪》以一项宏大的宣言结尾,呼吁创建全球性母权制度以拯救地球。如果是你在掌管着这样一个世界,你将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做出哪些变革?
埃尔曼:如果“我在掌管”?这是一种非常“父权制”的概念!女性应该集体掌管。这种该死的“领导者”(制度)似乎并没带给我们任何进步。不过,我们会改变什么呢?这是我的计划,基于史前的母系文化(顺便一提,它们被称为“史前”,仅仅因为它们早于男性统治):三个小时的工作日、免费医疗服务、开放边界、财富重新分配、公正地累积资源、对共同利益的奉献、尊重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多的暴风雪、尊重动物、更多的个人用土地(我只是喜欢它们的外观)、零暴力、禁用所有武器、结束一切监禁和美貌崇拜(那是另一种监禁)、并暂停谈及宗教(如果必须要奉行信仰,请把它变为一件自己的私事)。其中包括了将“运动”视为信仰:慢跑、瑜伽、健美操、去愚蠢的健身房(其实你可以去户外种树!),还有正念(mindfulness)、塑形手术,以及其他所谓“自我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会扰乱人类。我们的资本主义掌权者降低了我们对事物的关注,我们需要增强探讨。为此,我们应当重新将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专注上,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大成就。
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吃中国、印度、西班牙或意大利的食物。啊,反正我会的。
本文作者Sian Cain是英国《卫报》文化板块编辑。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