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入人心》中,乐评人伊恩·彭曼重新审视了詹姆斯·布朗、艾维斯·普里斯利等歌手的人生,并提出了一个疑问:音乐批评该如何评判有道德缺陷的歌手?

詹姆斯·布朗
今年,CNN发布了一篇关于詹姆斯·布朗的三段式调查报道,内容围绕他2006年骤逝疑云及其10年之前便已离世的第三任妻子艾德丽安·布朗(Adrienne Brown)展开。该报道详述了这名“灵魂乐教父”充斥着强奸、虐待、谋杀等恐怖细节的私生活。其中包括家暴指控在内的部分信息此前就已公之于众,文章同时还留下了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被自己奉承者谋杀的布朗本人是否也是受害者。直到现在,每当听到《I Feel Good》这些节奏紧绷的爵士乐,依然令人不安大于惊叹,总感觉这首歌之所以如此紧张,就是因为乐队成员们担心自己一旦错拍,这位暴躁的老板就不知道会做些什么。
英国评论家伊恩·彭曼(Ian Penman)在2012年阅读R.J.史密斯为布朗写的传记《独一无二的他》(The One)时,也有过类似感受。彭曼因布朗的暴躁而深感焦虑不安,觉得读者可能很想“放下书本出去听听音乐,来提醒自己为何如此烦恼,如果你没有彻底关上音乐的话,就会一直如此”。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数不清的著名艺术家展示出暴力行为或是令人反感的政治观。布朗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痛恨社会福利,认为黑人必须像自己一样为了成功艰辛劳动。如果这些艺术家的音乐动动手指就能关上,那究竟为何还要继续听布朗的歌呢?彭曼从个人视角提醒我们,是因为“教父”最好的音乐充满远见和宣泄,更别提它无处不及的存在了。那么我们能让艺术和生活达成一致吗?“怎么做?”彭曼发出疑问,“难道被艺术允许的疯狂、夸大其词、欲望,能在现实生活的灰色迷宫里找到栖息之处吗?”
《布朗》一文是《歌入人心》(It Gets Me Home,This Curving Track)收录的八篇文章之一,除第一章节研究了摩斯文化从上世纪60年起源到随后多次复兴的变化历程之外,其余每篇文章都集中关注了一位美国男性音乐偶像,他们的歌曲已经成为文化经典,个人言行上却有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彭曼尊重每一位文章主角,包括布朗、查理·帕克、法兰克·辛纳屈、艾维斯·普里斯利、约翰·费伊(John Fahey)、纳德·费根(Donald Fagen)、普林斯,但同时也绝不忽略“艺术家身上值得深思的复杂色调”。与其为这么多摇滚明星写部流水线一样的传记,他更试图解开艺术家“棘手甚至绝望的私生活与其极度优雅的歌曲之间互相纠缠的辩证关系”。
彭曼发现笔下的这些人物很难被列出规范的方程式。他们身上的东西依然彼此分裂:和其他对立面不一样,人们身上的好与坏并不是纯粹的两极。就像他在书中所说,“对布朗而言,演奏永远是工作,但工作从来不意味着演奏。”重要的是,“你从他音乐里总能找到这种感觉:这些歌曲即便有最明确的仁慈和恳求,也始终带着疯狂固执的、近乎恐吓的控告。”在个人和历史焦虑的蒙蔽之下,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名声、毒品、男性天生的狂妄,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这一切都互相分离又互相作用着。彭曼随后找到了一种“栖息地”或者说“家园”,从远处来估量这种相互作用的流动,来了解这些恶劣却又被宠爱、有才气的男人们现在听起来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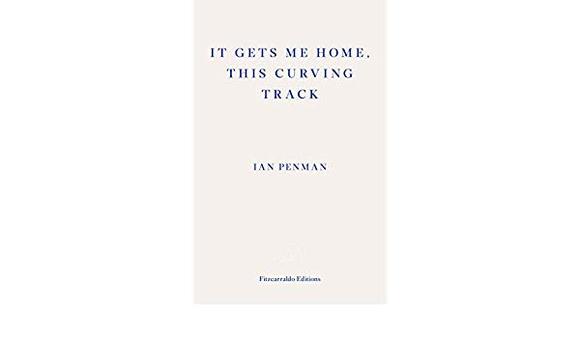
生于1959年的彭曼,从1977年青少年时期便开始为《新音乐快递》(New Musical Express)写稿,当时的他和许多年轻的音乐评论人一样,不仅拒绝接受英国生活与文学,还反对70年代对摇滚的批判。在编辑尼尔·斯宾塞(Neil Spencer)的领导下,彭曼和包括茱莉亚·波契尔(Julie Burchill)、保罗·莫利(Paul Morley)在内的同事一道将《新音乐快递》打造为工党支持派,经常对保守派提出毫不含蓄的斥责。
比起个人音乐品味,彭曼倒是更因他对批判理论生动博学的散文式论述而为人所知。在他早期撰写的对基德·克里奥尔(Kid Creole)等艺术家的评论文章里,经常能发现来自罗兰·巴特、德里达、阿多尔诺等人的名言引用,这些都是在“7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群体”广受欢迎的大思想家。但彭曼高深精妙的文学引用也使《新音乐快递》的忠实拥护者倍感疏远,记者保罗·翰威特(Paolo Hewitt)认为,他们“并不知道罗兰·巴特何许人也,而且……也不在乎。”即便一些稍有文学素养的读者,比如喜欢法国作家加缪的怪人合唱团乐队,也表示读彭曼的文字时感觉很沮丧。1979年,他们还演奏了一首名为《绝望记者》的歌,歌词这样写道:“伊恩·彭曼/他总爱用又臭又长的单词/比如‘符号语言学’和‘粗粒小麦粉’。”对怪人合唱团而言,他的措辞完全是自命不凡:“粗鲁又没灵魂的歪歪斜斜。”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彭曼的作品简直是开天辟地。欧陆性的概念可以帮助阐明音乐背后的构想,引起回忆的歌曲可以帮助晦涩难懂的理论找到合理语境。彭曼在80年代中期离开了《新音乐快递》,开始效力于《独立报》、《视与听》(Sight & Sound)和《The Wire》。他进一步提炼出一种豪爽的批判风格,不再与像劳勃·克理斯高(Robert Christgau)那样迎合大众消费心理的音乐创作家为伍,而更多地向聪明博学者积极靠拢,比如批判家、小说家盖里·印第安纳(Gary Indiana),是10位大力宣扬《歌入我心》的作家之一,还有社会艺术历史学家克拉克(T. J. Clark),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人间天堂》(Heavenon Earth)对一批经典艺术家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评价。到了90年代,彭曼已成为包括西蒙·雷诺茨(Simon Reynolds)、科德沃·埃顺(Simon Reynolds)、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内的新一代音乐记者群体的先驱者,将学术理论作为论证工具,来解开流行音乐棘手的社会影响。
《歌入我心》里的文章从2012年一直写到了2019年,原载于《伦敦书评》以及隶属于保守思想派的《城市季刊》(City Journal),后者倒是有些令人可疑。这些文章对传记进行了详细的历史编纂式的综合评述,引用了更多音乐史学家而非法国理论家的观点。彭曼表示自己致力于创作“非常易于理解”的散文。虽然极少引用欧陆哲学,《歌入我心》依然有建立在心理分析理论和符号学之上的基础:普里斯利和辛纳屈很难逃脱其与生具有的根源影响;费伊和普林斯试图弱化“作者功能”,模糊个人细节,颠覆听众期待(按照彭曼的说法,随后去创作真正平凡大众的音乐)。彭曼自始至终都致力于抹掉流行音乐及图像身上的光辉,让更具说明性的标志展露出来。
但是这些艺术家鲜少明确地表达出来。作为感觉像局外人的局内人,他们尝试着带上种族、民族、性别、声音等各色掩饰面罩,疯狂渴望在自身所处的位置上求得舒适。在彭曼写普林斯的文章里(本书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章,记录了这位艺术家80年代全盛期直至随后的失足衰退期),彭曼坦称自己对文中主人公的了解丝毫没有变多一些。毕竟普林斯总以别人的身份出现。“就仿佛有个人和一些被严苛控制着的图像,”彭曼在引言里总结道,“而在这两者之间……什么都没有。”似乎认识到基础的战后批评主义有所受限,彭曼提出了一项挑战:我们是否能在某一帧瞬间,将这个男人、这幅画面,视若无物?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能够学到些什么?

1988年查理·帕克的传记《鸟》开头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经典名言:“美国人的生命中没有第二幕。”34岁便英年早逝的帕克,的确永远失去了上演第二幕的机会。可以说彭曼笔下其他的艺术家也都没有,经过十年无与伦比的创意产出之后,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本身。通常在那些糟糕的经理人或热衷处方指令的医生们的帮助下,他们会陷入对自己职业生涯第一幕的反乌托邦式视角。“布朗的故事显然展示出美国梦的黑暗一面,”彭曼写道,“偏执多疑,避世隐遁,自我否认。”这个被证明是阈境空间的梦就像炼狱一样,他们的评价判断有时也会在某些程度上落到我们头上:批评,聆听,了解一系列流行歌曲和被公开的私人生活细节。我们该如何塑造艺术家的人生第二幕呢?
彭曼在2012年写下的短语“自我否定(self-cancelling)”并不带有今日的含义,但2019年的读者可能听到了耳边的“否定文化(cancel culture,指公众人物出现道德污点时,停止支持或抵制其作品的行为)”。对于那些和青少年发生性关系、虐待伴侣或者跟杀人犯混在一起的男人而言,毒瘾或道德松弛绝对无法成为洗脱罪名的借口。
在写到辛纳屈的章节里,彭曼仔细审查了这位歌手在60年代晚期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努力。或许并非出自本意,辛纳屈录制了一些像《Downtown》这种热闹时髦的新曲,还有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的《Both Sides Now》。在彭曼看来,这些演唱很有启发意义。在《Downtown》一歌中,他听出了这位歌手的悲情与苦痛,感受到“一种来自喉咙的汩汩作呕声,就像是那天早上宿醉恶心带来的酸味”。辛纳屈还在1970年录制了阴暗且不受赏识的专辑《Watertown》,被彭曼认为“引人深思,带有宿命论的色彩……能让人消除疑虑完全信服。”《Watertown》的力量不仅在于证明了辛纳屈的职业生命线绝未下滑,还展示出他生活与作品之间不确定的交流。对于辛纳屈来说,绝望能够同时锻造出好的和坏的艺术,催生出沉思与鲁莽。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对称的两面性,他后来时期的音乐才更应该被人们听到。
米歇尔是少有的几位从始至终都出现在《歌入我心》里的音乐家。如果辛纳屈是通过看向米歇尔来弄清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么无形之中,她也帮普林斯做了一次重新校准。在90年代和千禧年初,驱使着年轻的普林斯藐视音乐、种族和性传统的残留物已经凝结,而他的新歌也只能让人嗅到他如今模样的臭味。不过后来的普林斯开始改变了。“他又开始演奏那些过去的音乐:只有他自己,一架钢琴和一支麦克风……或许重访埋藏在歌曲之中的情绪,能帮助他把某些内在的东西推松动。”彭曼想起米歇尔2002年的专辑《Both Sides Now》,这张唱片水准不错,还有一首她改编自早期成名曲的新版同名主打歌。“她把这首歌的内核唱了出来,”彭曼写道,“用她57岁的嗓音和歌中包含的一切:爱、渴望与沮丧。”
这便是我们最后所留神倾听的东西,至少是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音乐。正如彭曼借由费伊和阿多诺所表述的那样,音乐无法像语言那样表露意味,它很少能成为真理或政治话语的有效导引。同时,音乐也十分抵触语言上的错误指向,去说些人心里并不真实的想法。“成堆的书都力图发掘那些美好歌词背后的‘含义’,”彭曼写道,“但通常正是一些被人遗忘的零散的旋律击中了我们。”如果他对不愿直抒胸臆的艺术家表示赞成,那是因为此举打开了新意义产生的大门,一字一词都能因为不同的阐述方式得到重新编码。正是一段情感充沛的聆听经历,让彭曼关于个人传记、历史和音乐的辩证法最终贯穿到一起。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条附加线索:听众。在一篇关于普鲁斯特的文章中(该文后来还成为了彭曼的题词内容),瓦尔特·本雅明发出疑问:一名艺术家的人生与作品是否总能“镇定自若地揭开他所属的最稍纵即逝的、最多愁善感的也最脆弱的生命时刻”?本雅明按照自己的句法节奏品读着普鲁斯特:比起狂妄自大,这个错误显然没那么致命。但更重要的是,本雅明认为这位艺术家的脆弱时刻意味着读者能将自身带入作品之中。“当普鲁斯特在一篇著名短文里描述这段时间是他自己的时候,”本雅明一边读着一边说,“他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我们自身由此便被编织到了艺术家的生命之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能开启一段解开美好的旅程了。
本文作者Joe Bucciero是一位作家,出生于芝加哥,现居普林斯顿。
(翻译: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