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大或小,每个家庭都有秘密。在一个“坦白从宽”的世界里,埋藏这些秘密有什么好处?

《窗边的女人,正向女孩招手》,雅各布斯·弗雷尔(画作局部,1650年前后) 图片来源:FondationCustodia/Frits Lugt Collection, Paris
每个家庭都有秘密。创伤、不忠或丑事,多少都会被有意掩盖。秘密以信任为纽带,促使家庭团结,但也常会发展为不堪承受之重。秘密可能会撕碎一个家,留下伤感和一堆未能解答的问题。这些秘密是来自过去的包袱,有时还会世代相传。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主动披露,乃至于向大众公开秘密,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时代精神。从更新状态到记录心路历程,再到播客亮相,一波无休无止的自白狂潮正向我们袭来。祖母精神分裂、父亲家暴成性、兄弟自寻短见、姐妹意外怀孕、叔伯忽然出柜,还有我们自己的嗑药史。让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吧!秘密贻害无穷,泄密不仅使人自由,还有益身心健康——至少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允诺。
不过,反思一下这种对秘密的攻击,或许也是个不错的点子。尽管家庭秘密的历史堪称一部恐惧、羞耻和压抑的历史,但它也是一部信任、温情和忍让的历史。秘密可能令人窒息,但也能救人性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云,抛弃禁忌可能令人如释重负,但坦承心底秘密的冲动本身绝非无辜。表面上是对压迫性社会规范的最后一战,实则可能为更加难以捉摸的权力运作敞开大门。与其对家庭秘密讳莫如深,不如视其为一面透镜,藉此细察家庭及其与社会的复杂勾连。与当代公众打交道时,我们务必要留意究竟哪些秘密才有保藏的价值,确定谁有权以及何时适于披露秘密,或许是重中之重。
美国知名作家、播主丹尼·夏皮罗(Dani Shapiro)可能是眼下对厌恶家庭秘密这一心态有最精到把握的人。她在《家庭秘密》系列播客的预告片里表示:
黑暗中的秘密会不断溃烂。它们会变得更庞大、更恐怖,具备于不经意间左右我们整个生活的力量。但一旦我们让这些秘密见了光,便会发生最奇妙的事: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其实并不孤单。
恶化的溃疡这一意象以及光与影这一老生常谈的隐喻,无疑凸显了秘密的不光彩和消极一面。夏皮罗给自己立下了令秘密摆脱此类污名的使命,甚至也包括“要命的”家庭秘密。她提出,我们正处于一场揭秘革命(revolution of revelation)的中心:
我们身处一个不再有秘密的时代。不管把原因追溯到基因测试、互联网还是反性骚扰运动,踢爆和揭开我们身边的一切秘密,都令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可能在信任他人的同时怀有至深的恐惧,我们最深刻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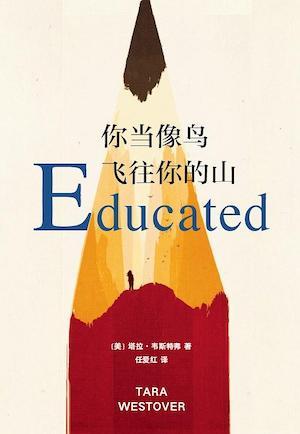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看,秘密当然兼有压抑和破坏性。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加剧暴力,如在某些不承认家暴的家庭里,受害人可能会被迫继续与加害者一同生活。塔拉·韦斯特弗的回忆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对此有生动的呈现。她在爱达荷州乡下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长大,父母是激进的生存主义者,与主流社会相互隔绝、格格不入。年少时,大哥就曾对她施暴,以身心两方面的暴力迫使她屈服。他会拉扯她的头发,在厕所里用水冲她的头,骂她“臭婆娘”,甚至还威胁要杀死她。多年来,塔拉未曾对他人披露家暴经历,甚至自己也不去想它,她接受了大哥的说辞:两人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当她最终鼓起勇气,将此告知父母时,父母不仅对暴力横加否认,更试图以“你有幻觉”来说服她,令她反复拷问自己的记忆力和精神健康。父母不愿面对尴尬事实的做法,最终导致一家人反目成仇。韦斯特弗在接受《卫报》访谈时表示:“在诸如我家这样的家庭里,没有比说出真相更恶劣的罪过了。”
此类保密不仅有害,道德上也成问题,哪怕还算不上彻头彻尾的犯罪。当然,就保密之举本身而言,未必都有韦斯特弗这般痛苦。说回来,论起政治生活中的保密,其矛盾感在许多情况下就要突出一些。
首先,保密与披露之间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尽管人类的一切互动都基于一定程度的相互了解,但也难免会有含混和无知。1906年时,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提出:“在一切个人性的、性质各异的关系中……每一单元在以言辞及行为向他人展示自身时,均有强弱(intensity)与浓淡(shading)之分。”早在诸如Facebook和Instagram这类社交媒体诞生前一个世纪,西美尔就精准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人类始终在有意无意地管理自己的对外表现,即便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境遇(他甚至指出,在亲密关系中,欲望依赖于一定程度的距离——亦即意识到我们尚未完全知晓对方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永远无法彻底向他人敞开,也无法彻底看透他人——还未必能看清我们自己。可以说,一定程度的保密乃是人类的基本冲动,没有它就没有社会生活。
先不论这点,我们或可将秘密定义为刻意不让他人知晓的信息(无论准确性如何),用哲学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秘密》一书里的说法就是“鉴于隐瞒之需而只存在于保藏者心中”。秘密可能只有一个人知道,也可能只有一个人不知道。秘密可能是深刻的,被隐瞒的不只是特定的信息,还包括隐瞒这一行为本身。秘密也可能是表面化的,即有人知道存在隐瞒之举,但不知道被隐瞒的具体事项。秘密有自身的历史,其轨迹可能会随时间而演变。起初为众人皆知的事,之后可能会成为深刻的秘密,或者反过来。
人类学家莫妮卡·康拉德(Monica Konrad)在《无名关系》一书里提出,保密经常会与其它类型的知识活动纠缠在一起:集体发明另类叙事、显见的沉默、含沙射影、选择性的认知以及“主动不去知道(active not-knowing)”。我们或许会产生某种感觉,它几乎完全是内在的,不仅没有告诉家人,还本能性地回避提到它,理由在于我们觉得——不管正确与否——公布秘密会引发不快乃至于造成伤害。面对身怀大屠杀创伤的家庭便是一例。子孙固然知道过去发生了可怕的事,但可能不愿追问细节,因为他们不想让挚爱之人再度沉浸在痛苦中。另外,我们也可能感到家人做了道德上可疑之事却不愿表达自己对此人的的意见或感受。这种隐秘的、情感性的机制,也许正是家庭的题中之义。

从社会和文化方面看,刻意的隐瞒、回避和闪烁其词有其存在的根据:它们有助于抚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或者说自我期望与自身能力或实际作为之间的鸿沟。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在《他们自己造就的世界》一书里指出,“我们赖以为生(live by)的家庭”(神话式的、想象中的、梦寐以求的家庭)和“我们生活其中(live with)的家庭”(真实的家庭)之间判然有别。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家庭逐渐丧失实用和经济上的功能,人们对家庭的构想开始变得理想化,视家庭为情感安全区,以温暖的相互扶持关系、亲密和柔情为尚。历史学家史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的《婚姻简史》提出,爱情不仅战胜了婚姻,它如今已经涵括了整个家庭。现实生活里的家庭当然不同于理想,它可能是不幸的、令人窒息的、冲突不断的乃至于不安全。“秘密的运作,”社会学家卡洛·斯玛特(Carol Smart)认为,“使我们能创造出一个家庭叙事,藉此让现实中的家庭显得更接近于理想或神话意义上的家庭。”
鉴于保密是一种处置灰色乃至于不法之事的途径,所需要隐瞒的事项也会因道德标准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如今,一些做法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被视为基本无害——譬如婚外孕——放到一百年前这可能就是爆炸性新闻。特定的实践——如殴打妻子、体罚儿童——如今已属非法,在过去则广为接受。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某些禁忌今后可能会解除,特定的秘密也会随之浮上台面,继而又有新的秘密诞生。任何社会都有道德禁忌和社会期望,这一切都有助于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难免会有侵犯这些规定的时刻,也经常会设法掩盖此种侵犯举动。无论基因测试和互联网怎样有助于揭发令人不快的事实或可耻之举,保密行为都不大可能消失。
但这也未必有那么可悲。有时,保密是一种护盾,可保护家庭成员或全家,使之免于丢脸和污名化。以性侵犯为例,承认某人的伤痛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受害者也未必愿意让全世界都知道整个过程。当事人可能不愿背上受害者这个标签,不愿被视为因侵犯而永久失能的人或者被打成所谓“残次品”。在这种情况下,只与值得信任的小圈子分享信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进一步看,保密还有助于构建一个让生活可堪一过的空间,哪怕确实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以英剧《唐顿庄园》为例,该剧讲述了克罗利家族及其佣人的故事,其中存在感最弱的二女儿艾迪丝就承载了不少家庭秘密。在婚外怀孕后,艾迪丝起先听了别人的劝,对私生女玛丽戈德不管不顾。然而,与亲生骨肉的分离令她备受煎熬,后来她设法把玛丽戈德带回家,谎称其只是路边捡来的孤儿,自己想要收养她。此后,家庭成员逐渐知道了孩子的真实身世,但都决定保守秘密,让艾迪丝可以放心照料孩子,同时也令一家人免于纷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讽刺。也有观点认为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家庭秘密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起到了保护作用。当然,艾迪丝本身就是特权阶层,在许多谴责婚前性行为的社会里,贫穷的单身母亲几乎不可能有艾迪丝的待遇。

家庭秘密甚至还能救人性命,如在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面前藏匿犹太友人或亲属者,或今天在同性恋构成重罪的社会里协助家庭成员隐瞒性取向的父母和子女。
保密和隐私也有着深刻的勾连。历史学家狄波拉·科恩(Deborah Cohen)在《家庭秘密》一书里提出,保密和隐私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在18世纪,“保密”和“隐私”这两个词几乎可以互换使用。科恩称,如今前者有负面色彩,后者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比较起来,几个世纪以前还有“保密是隐私不可或缺的仆人”一说。人们视保密为一种使家庭免于外来干预的防范措施,有利于构建和维系一个免遭窥视的空间。科恩还提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密通常是中产或上层阶级的特权。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人满为患的宿舍、共享的楼梯间和卫生间、脆弱的墙壁和位置不佳的窗户——令隐瞒丑行丑事变得几乎不可能。家境更宽裕、对隐私投资更多的人群则可以选用单向玻璃,令它一时成为中产和上流阶层的身份象征。
除了维护中产家庭的声誉,保密还会影响家庭的内务。不无启发意义的是,德语的秘密(Geheimnis)一词的字根就是家(heim),其本意为专属于某间房子或某一家的。然而秘密未必只是属于家庭或家族,它甚至对家庭有塑造作用。它可以透过信任的纽带让家庭成员更团结,私密性可能有助于发展亲密关系和相互依赖——且不论其好坏。反过来,它也可能加深最初知晓秘密的那群人和不明就里者之间的隔阂。
秘密在伦理和政治上具有极为复杂的面向,揭秘也是如此。不管是对小圈子还是公众披露家庭秘密,其牵涉面几乎肯定不会限于当事人。这样一来,坦白之举通常有代表他人的成分,也会让他人承担一定的后果。即便没人会有生命危险,不合时宜的揭秘比起保密而言也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譬如,一个人可能打算向不愿知情(或者已经留意到蛛丝马迹)的某人揭露不忠,但又留意到了此举蕴含的风险,感到有保持沉默的必要。有时,察觉养育你长大的父母并非亲生,可能会不必要地加重亲子之间的隔阂,且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但公开指证还另有一些严重问题。公开家丑一般被视为勇敢、诚实之举,大部分情况下也的确如此。秘密越是丑恶,冲击感也就越强——不少事例表明,此类丑陋的真相颇受市场欢迎,书籍的大卖或播客的高点击量经常能为揭发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话说回来,坦白并不仅仅是反映一些固定的内在特性或一组毋庸置疑的事实。相反,这一行为本身就建构了这些现象。揭秘通常基于个人记忆,而它并非随时都可信。韦斯特弗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对此有深入的考察。“我最强烈的记忆,”她在序言里称,“根本就不算记忆。它是我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接着再加以记取,俨然事情真的发生过。”在回顾一段段家庭过往时,韦斯特弗曾仔细地比对各种证词,屡屡发现不同在场者的回忆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出入。
一些公开坦白者也对记忆的歪曲性和创造性怀有担忧。另一些人则不那么在意这一点。
哪怕我们假设坦白者对过往事件和感受的记忆基本准确,仅由个人来担保真相也是成问题的。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观感,每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都会被重述,其动机可能会被议论也可能会被忽视,人们对同一事情的观感有极大的差异。换言之,潜在的真相可能不止一种。但编撰一套有说服力的叙事、将之公开并建构关于个体对象和家庭的公共真相的欲望——或权力——极少有平等的分配。
与其异口同声地讨伐秘密,不如承认有些秘密有害,但有些秘密则有用,最关键的一点或许是,一条秘密可能会兼具赋权和抑制、保护和压迫等特征。这样,我们需要问的便是:秘密保护了谁?它是强化还是挑战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抑或是兼具这两种成分?针对坦白:谁的真相被确立为唯一的真相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
一旦我们跨过与揭秘有关的诸多文化禁忌的藩篱,保密和坦白就将成为一面犀利的透镜,我们可借之检视家庭中由情感主导的微观政治与过去或当下社会里的宏观政治趋势的复杂关联。
本文作者Karen Vallgårda系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现代历史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