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环境政治学者吉迪亚·珀迪在最新著作《这是我们的土地:为新联邦而抗争》中提出了激进环保主义的主张。

图片来源: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气候变化否定论”(climate denialism)又回来了。几十年来,否定主义者一直拒绝有关环境的真相:否认碳排放与全球变暖之间的联系,否认人类增加了碳排放量和气候模型的准确性。气候变化显然已造成越来越多的灾难,这种陈旧的否定论正在崩溃。但在这个气候危机时代,否定主义又有了一面新的幌子,即否定论关乎人类的本性,而不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本质。
乔纳森·弗兰岑是这种“新否定主义”最张扬的倡导者。在《纽约客》一篇极具争议性的文章中,弗兰森嘲讽防止气候灾难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弗兰岑拒绝了过去的否定主义,他确信可怕的气候变化是真的。但他同样确信,我们无法阻止那些恐怖变为现实。他的反对态度基于这一论点,即气候灾难的“不可逆转点”是在全球平均温度升高2摄氏度之时。一旦变暖发生,世界将在一系列快速而频繁的环境变化中超出我们的控制,带给人类很多灾难。为防止这种毁灭性灾难,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严厉的保护措施”并“彻底改造经济”。但是,我们自满、短视、自利的“心理”助长了政府不作为的“政治现实”,因此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造。
弗兰岑写道:“请称呼我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不认为人类的本性在短期内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试图中止滚雪球式的危机既无望又“自讨苦吃”,因为它们将我们的努力转移了,反倒忽略了“有一定现实希望获胜的、更小的战役”。而在这些“更小的战役”中,我们至少可以拥抱“今天的希望”(例如弗兰森的宠物计划,保护濒临灭绝的鸟类种群),而不是“未来的希望……(未来)无疑比今天更糟”。
弗兰岑的这篇文章被广泛嘲笑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小说家被误导后的胡思乱想”,将2摄氏度的升温描述为“不可逆转点”是误读了气候科学。弗兰岑的文章提出解决环境问题是一场零和博弈(而不是面对共同问题的协同作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弗兰岑自己曾花费7.8万美元遗产乘游轮去往南极洲,只为了“在它融化之前看到它”,他的观点因特权而严重扭曲了。的确,作为一个富有的白人,他是最不可能承受气候灾难恶果的人之一。
反对的观点听来合理,但弗兰岑的许多批评者又似乎同意他的看法,即我们人性的缺陷削弱了有效的气候行动。正如一位批评者承认,我们趋向于“自满和拖延”,因而弗兰岑的悲观主义是“合理的”。在整个气候讨论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我们就是天气:拯救地球始于早餐》(We Are the Weather: Saving the Planet Begins at Breakfast)的作者乔纳森·萨夫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提出了以饮食为基础的气候革命,将缺乏集体性的气候行动归因于“情感极限”阻止了我们关注重大问题。同样,《不宜居住的地球:气候变暖后的生活》(The Uninhabitable Earth: Life After Warming)一书的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认为,我们“隔离和否认(事实)的心理”,很可能导致不恰当的未来气候政策。

人们难以接受弗兰岑观点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还需要接受他的预言。对他而言,人类毁灭的临界点是2摄氏度还是4摄氏度并不重要,只要人类的本性中永恒地打上对未来和对彼此的冷漠烙印,那么我们就无法为遏制气候变化而完成必要的重建。弗尔也许认为,放弃肉类的“个人决定”将带来一系列类似的气候保护“浪潮”。华莱士·威尔斯则希望少数“气候论危言耸听者”能促进并推动广泛的变革运动。但在认定人性的不可改变性方面,这两位作者都赞同弗兰岑,否认了将这些小规模变革推动成大规模运动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所持的乐观态度是空洞的,拒绝了“新否定主义”的“新瓶”,却同时拥抱了它所装的“旧酒”。
“否定主义的时期”(season of denialism)正是吉迪亚·珀迪(Jedediah Purdy)在他的新杂文集《这是我们的土地:为新联邦而抗争》(This Land is Our Land: The Struggle for a New Commonwealth)中的主题。珀迪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法学教授,专门研究环境政治,他称这种“新否定主义”源自人类的“缺乏信仰”,而并非对环境真相的“无知”。
《我们的土地》一书通过一系列清晰敏锐的对美国污染情况的探查,以寻找这种“缺乏信仰”的成因。在路易斯安那州石化制品泛滥的海湾、宾夕法尼亚州因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而遭破坏的农场,以及他的家乡西弗吉尼亚州因山顶清除式采矿而干涸的河流中,珀迪遇到了和弗兰岑同样的问题:一种“破裂”的政治,使集体意志“难以团结”。珀迪还认为,气候危机将“加剧”,造成越来越多的灾难性风暴、旱灾,移民和战争。“当绝望的证据如此沉重和清晰,”则人们对拯救环境报以悲观态度“不能算是错”。
不过,当弗兰岑认为自己已经遇到了人类无法改变的缺陷时,珀迪却进一步看到了,环境能够塑造人们的态度和政治意愿:要衡量我们的生存机率,就需要关注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如气候灾难是“人类所造成的”,人类也是其脚下土地自然发展的结果。珀迪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对气候变化采取集体行动的“分裂与剥削,也同样烙印在土地上”。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The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不再主张住房歧视性“红线政策”(redlining),但被隔离的社区仍在反映,该政策带来的影响损害了黑人的财富。本土“宅基地”(homesteading)分配曾使几代以前的定居者获益,但如今成为白人民兵攻击政府管理公共用地的理由。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工会权力急剧下降,与甲烷泄漏一样,是造成二十一世纪阿巴拉契亚煤矿致命爆炸的原因。
我们掠夺世界的力量源头是“使美国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土地条款”。我们是“我们所制造的环境的产物,基础设施中的一类物种”,“集体拥有科技的外骨骼、循环系统和神经网络,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条件。”而基础设施则不仅包括30万亿吨(货运量)的道路、城市、住房和农田,还包括“连接人与人的非物质系统”,例如货币和法律。它是一张权力、资源和规则的网络,要求每个人都通过它来行动,使我们无法真正地“选择人与人、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规则”。想一想关于“少吃肉”的选择,弗尔说:“这可能是个人能采取的最重要行动,以扭转全球变暖。”然而广告和法规却在制约这种选择——它们影响了我们对于食肉的喜恶,并且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金也令这些喜好变得廉价而容易满足。并非是我们的本性、而是我们的经济模式(我们运作世界的方式)——“正驱使人类和非人类生命走向缓慢但正在加速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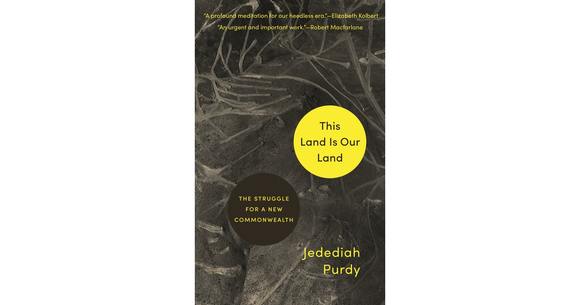
指称“经济是环境灾难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珀迪将这种指称与一个论点结合起来,认为经济“不会自然产生,它或出于‘理性人’的自利,或出于企业家们破坏性的想象力”。他提醒我们,消费和分配模式并不能反映我们天生的偏见、失败和喜恶。市场、价格和追逐利润,与种族、阶级或任何其他社会结构,都可以解释这一切,并且它们从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市场维持着不平等分配,价格反映了过去的偏见,而权力决定了我们的偏好。总的来说,这种“政治经济”向我们施加了“一种概括性的、导致不平等的商品化逻辑”,因此,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不得不成为彼此利益的工具。”
珀迪认为,变革的手段正是《我们的土地》书名中所提到的“联邦”,一种“更强大的共同关怀计划,它可以战胜所有形式的否定主义”,将土地、人民和他们共同创造的果实联结在一起,平等地分享地球的财富。达成这一“联邦”的关键,在于理解“美国的团结行动一再遭到分裂和剥削的阻碍——种族主义、畸形的性别观念,以及(产权)所有者和雇主们或微妙或直接的暴力,这些因素通常交织在一起”。因此,任何希望以“联邦政治”遏制气候变化的计划,都必须首先“推行激进的环保主义”——通过认识到“经济权力、种族不平等和原住民的挣扎,不只是补充性或可选择的工作——它们一直都是工作的核心”。
尽管任重而道远,但珀迪有信心我们可以做到,“如果问题在于我们已建立的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建立另一个世界。”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历史”,珀迪说,历史表明“联邦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式理想:它是激进且可行的”。这段历史记录在了《我们的土地》最精彩的章节中,详细介绍了“漫长的”环境公平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该运动诞生于1980年代,它批评主流的环保主义过于“白人化”、精英化,并忽略了环境问题如何大范围地伤害着穷人和有色人种。珀迪将这一问题追溯至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约翰·缪尔(John Muir)。缪尔的环保伦理与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密不可分:他嘲笑了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附近的原住混血少数族裔(Sambos,如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称他们懒惰、“邋遢且生活不规律”,同时向公园游客许诺“至于印第安人,大多数已经死亡,或已开化成为没用的无害者”。联邦政府兑现了这一承诺,创建了许多国家公园,驱使原住民离开家,为中产阶级白人打理原始荒野。
珀迪还发现,许多环保主义者早在写下“环境公平原则”以前,就已将其纳入考量。例如,他提到了荒野协会(Wilderness Society)的负责人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他曾是推动联邦政府改革中重要的一员,他同时主张保护主义和支持美国原住民的部落主权。然而,当现代环保运动在1970年代兴起时,其领导者无意中将缪尔、而不是马歇尔的观念作为了行动指导。他们所创建的准则和组织并不直接参与权力、种族和阶级问题,并且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不平等中随波逐流(而不是与之抗争)。珀迪宣称:如果我们能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不必被自我分裂的历史所困。”
珀迪只花了很少的笔墨去描述建立“联邦”的具体办法,仅用了几页篇幅介绍了诸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等努力。其中一章描述了将珀迪的乐观理想变为现实的具体建议,或提供了更多的史实以合理化珀迪的观点,这可能比关于2016年大选的形而上的一章更具实际意义。《我们的土地》全书不到200页,作者可能有意省略了一部分。最好结合法律和政治经济运动萌芽的背景来阅读本书,它尝试将民主和权力的概念带到法律学术、教学和实践的最前沿。《我们的土地》可能就是上述运动的环境信条——它是修复地球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信条,正如珀迪所说:“如果没有观念和构想提供蓝图作为目标,就无法推进权力的实质性变革。”
珀迪是“法律与政治经济项目”(Law & Political Economy Project,始于2017年春季在耶鲁法学院召集的一次研讨会)的联合主管,他知道他的书只是一个起点,还有细节需要补充、原理需要修订,以及有待活动家、学生、学者和从业人员起草行动项目。如此一来,《我们的土地》就重申了它最基本的信仰主张: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因为世界“在各个层面上本就非常多元,并且……我们共同身在其中”。要跟随这种信念行事,就需要我们超越弗兰岑的失败主义观点,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性是有缺陷且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类是环境的产物(由某种经济体所定义,而我们又可以重新定义这一经济体),我们会发现,通往气候拯救的道路是真实可行的,并且,我们无法在这条路上独行。
本文作者康纳·德威尔·雷诺兹(Conor Dwyer Reynolds)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环境法律研究员。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