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不止是变成另一种性别这么简单。

图片来源:Chloe Cushman
我们在出生时被指定了一种性别,却从小觉得自己属于另一种性别……这种感觉(无关性欲)愈发强烈,直到在“错误的性别”中的那种生活似乎已不值得过下去。于是,我们作为跨性别的女性或跨性别的男性,来到了我们的所爱之人和医生的面前,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勇气、荷尔蒙,甚至手术,然后我们终于能活成本来的样子,感觉好极了。
以上故事讲出了许多跨性别者的生活,它的一部分也讲述了我的故事。这也是“顺性别”(cisgender,指出身时的性别与自我性别认同相符的人)人群相对容易接受的故事版本,并且是直到最近为止,流行文化通常讲述的一个版本。但许多医疗人员需要一个更详细的故事版本。直到2011年,被广泛接受的医学标准都会强制要求我们在没有摄入激素的情况下,以我们实际的性别生活三个月或更长时间,以证明我们是真正的跨性别者。他们还规定,我们需要尝试看起来像男性或女性,但并不被认为是同性恋。
这样的故事不包括那些经历了跨性别后又后悔或逆转性别的人(一些人如此,但更多的人没有后悔)。这里排除了性别和性经历更为复杂的人。并且,他们排除了非二元性别的人,那部分人以两种性别或没有性别的方式生活,经常使用“TA”作为代词。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了——不光是生活故事,还包括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跨性别者的小说、诗歌、漫画、电影、论文。其中一些故事可能会赢得跨性别读者的共鸣,或帮助非跨性别的读者接纳他者。其他故事则旨在“破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故事。
安德烈·隆恩·楚(Andrea Long Chu)是破坏者之一。她是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研究生(doctoral candidate),是一位作家和评论家,其作品曾许多次刊载于《n+1》杂志、《Bookforum》杂志和《纽约时报》。在2018年初,她发表了一篇名为《像女性一样生活》(On Liking Women)的文章,该文章在推特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文章拥护1960年代的剧作家和挑衅者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她是《SCUM宣言》(SCUM = Society for Cut Up Men,谴责男人协会)的作者,并差点儿成为安迪·沃霍尔(的刺杀者(她曾于1968年尝试枪击他)。楚狠狠反击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所描绘的那种单一的、易于理解的跨性别故事。她还瞄准了一些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后者将跨性别女性视为不情不愿的男性。
“我从来没有能够分辨清楚‘喜欢女人’和‘想要成为女人’之间的区别。”楚承认。她并没有将自己的年轻时代描绘为“已经是一个女孩”,而是一个“恐惧的异性恋男孩”,“我永远不会想去过他的那种生活”。至于《SCUM宣言》,在楚看来,它暗示了跨性别女性“不是要‘确认’某种先天的性别认同,而仅仅是因为做男人愚蠢而无聊”。
而宣布她的女性身份,对于她和像她这样(以及老实说,像我这样)的跨性别女性来说,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赋权式的选择,而不是单单为了求生。她总结道,“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选择跨性别,”从激进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异性恋的”笼子中爬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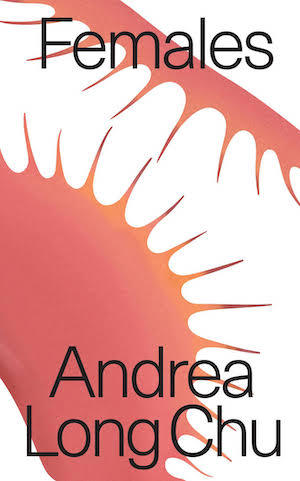
楚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观点的?在她的第一本书《女性》(Females)中,你找不到清晰的答案,这本书简短而令人气愤,既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像某种宣言。它更像是一种挑衅,上面充斥着楚本人所说的“不可辩驳的主张”。“每一个人都是女性,”楚写道,“而每个人都讨厌这种性别。”在这种特殊的哲学意义上,我们都是女性,因为我们都“为另一个人的欲望腾出了空间”。你也应该让“别人为你的欲望做点什么”。
用楚的话来说,男性,是指行为举止像男人的人,符合男性气概原型的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获得。但她对索拉纳斯的观点进行了拓展,楚认为,没有人是完全独立、完全主导、完全满意的——这意味着任何试图成为“男性”的人,都得接受持续的失败。如果说女性意味着脆弱性和依赖性,那么我们都是女性,而“父权制的性压迫”的作用,就是“掩盖”这一普遍真理。男人认为他们必须是“男性的”,但他们又做不到。他们从色情影片中逃离这种双重约束,那时候被动的、受到羞辱的、正在手淫的观众可能会同意“(他们)不是拥有权力,而是放弃权力”。
如果以这种方式看待男性,那么合乎逻辑的问题不是“是什么促使某些人成为跨性别者”,而是“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或尝试成为男性”?一个答案是,男人别无选择。另一个答案是,阳刚之气让人感到痛苦和局限——在你并不想要它的情况下。比如,像我一样,你会宁愿成为一个女孩(楚回忆说:“我讨厌作为一个男人,但我认为那只是女权主义该有的感受。”)。第三种答案是,我们可以试图重新定义男性,并讲述其他的相关故事。在这个方面,跨性别的男性可能可以领路。
美国演员和作家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的“弟弟”赛勒斯·格雷斯·邓纳姆(Cyrus Grace Dunham)写了一部出柜回忆录、一本名人回忆录,和一本富裕的年轻作家关于青年危机的回忆录。但这同时又是一种“反回忆录”的做法,即邓纳姆、或你、或我,反对一种关于我们生活的始终如一的叙事。经过数月的暴饮暴食以及与抑郁症的斗争,邓纳姆已“非二元性别”和“跨性男”(transmasculine,与男性跨性别者相似,但跨性男并不一定完全或只认同自己为男性,可指任何在往更男性身份认同转变的人)的身份出柜。他们在专业的语境中以“他们(they/them)”作为代词,但并不完全像一个男人,在朋友中,也使用“他”作为代词,“他们”还接受了手术(双乳切除术)。
《没有名字的一年》(A Year Without a Name)可以被视作一种复苏性文学,提出了一些“他们”感到不得不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姐姐的名声(“一种有毒物质”),以及“他们”在“酒精、克他命、可卡因”中的冒险。我们还有关于该领域的其他回忆录。但这一本相对其他而言更加易读。邓纳姆可以从早期跨性别者那里继承术语的使用,还可以谈论和写下关于色情欲望的变迁,以及欲望如何影响了性别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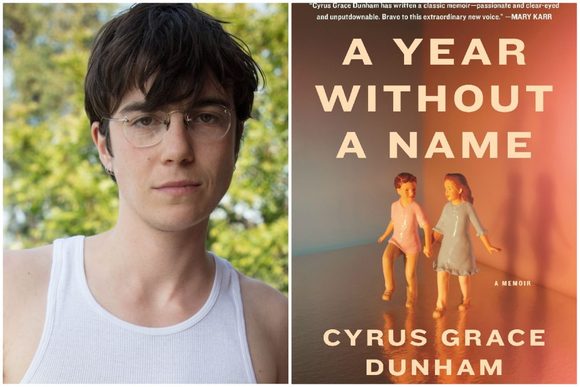
对于邓纳姆而言,探索性别和性意味着探索包容和不确定性。“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似乎并不想拥有明确形式的身体中,并在其中产生性的感觉。邓纳姆发现,这幅身躯更像是一个蛹、准备“变成黏糊糊的,然后重塑”。在床上,在跨性别之前,邓纳姆坦言“相比自己的欲望,总是更重视我的伴侣的欲望”。邓纳姆迷恋着一个迷人的派对女郎,曾经“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女孩,自我意识太强了,反而无法做对任何事情”。相反,“他们”目前的恋人认为并接受邓纳姆是一个善良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性感的男人。邓纳姆发现,对于束缚和统治式性体验的试验,有助于了解使用和释放权力的感觉,从而为“将自己视为男人”提供了条件。
也许你也必须接受不确定性,然后才能成长和改变。我曾被很多人这样告知,甚至是非跨性别人士。而像邓纳姆或我这样的跨性别者,则必须走出那些“错误的确定性”——坚称我们现在以及永远都只能是基因赋予我们的身体,永远只能是我们出生时的性别。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不止一次地努力。邓纳姆总结说:“我的价值不在于我的永恒性,而在于我能够在洪水之后恢复、再恢复,以及重塑自己的韧性。”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跨性别的且需要重塑?你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跨性别者(就像人们可能患有糖尿病)吗?跨性别的反对者认为,跨性别身份是新出现以及新潮的,当今的跨性别青少年正在追赶潮流。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错误的,从萨摩亚到南亚的许多文化中,都有跨越性别界限的身份,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关紧要:我们的被接受与否不应该取决于这种身份出现了多久。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然而,这个起源问题使我们想起了一些有用的历史。安妮·李斯特(Anne Lister,1791-1840年)喜欢并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在穿着和举止上都非常像男人。她在约克郡的邻居称她为“绅士杰克”,尽管在今天,像她一样行为举止的人可能是贵族的女同性恋,而不是跨性别的男性。相比之下,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1789–1865)博士从成年后就始终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男人,从他在爱丁堡的大学时代到担任军事医官的几十年间。他改善了大英帝国前哨基地的卫生条件。
在美国,卢·沙利文(Lou Sullivan,1951–1991年)首先知道了自己是跨性别者,然后才对此发表言论。但是他不仅简单地预言了现代身份。他帮助这些身份变得可见并生存下来。他于1980年出版了《关于女性到男性变装者和变性者的信息》(Information for the Female-to-Male Crossdresser and Transsexual),撰写早期旧金山跨性别男性杰克·贝·加兰(Jack Bee Garland)的传记。以及,用沙利文的话说,与医护提供者合作,确保“从女性到同性恋到男性的转变,是正式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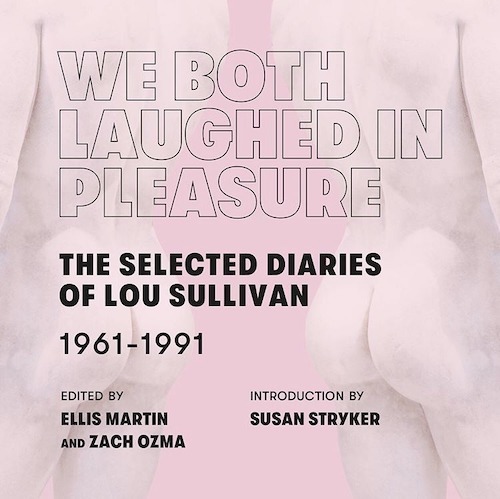
像李斯特一样,沙利文保留着丰富的日记。现在再阅读它们——马汀(Ellis Martin)和奥兹玛(Zach Ozma)编写的精简版《我俩放声欢笑:卢·沙利文日记集》(We Both Laughed in Pleasure: The Selected Diaries of Lou Sullivan )——是要找到跨性别读者可能会认同的情感。 “我想看起来像我本来的样子,”他很早就沉思着,“但并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样子。”“我一生都梦想着自己是另一个人,但没有人会相信我。”就像我数十年以来所做的那样,沙利文有一种感觉,即以跨性别的身份出现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能的,直到他决定采取这一步。他说:“真是太好了,允许我说‘我是一个男人’真是太好了。”首先,他不得不搬到旧金山,离开他温柔、难以相处的长期恋人:“如果J不曾在身边,”他沉思着,“我会肯定会早一点儿成为男性。”
沙利文选择了自己想讲述的故事后,便可以帮助他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在加利福尼亚,他看到了著名的跨性别男人史蒂夫·戴恩(Steve Dain)“向一名18岁的女性提供咨询,她说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同性恋男人……所以我们确实存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然而,沙利文并没有因此而在他的探索中受到阻碍,“只是为了刚发现自己身份的女性-男性跨性别者证明,‘我和你们一样’。”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随着他因艾滋病而去世的临近,他写道:“他们告诉我……我不能作为同性恋男性生活,但看起来我会像一个男同性恋那样死去。”
你可以将沙利文的生活描绘成一场悲剧,但他的日记却洋溢着欢乐,部分原因是它也充满了性爱内容——这是跨性别者不得不进行的自我教育。“我用袜子做了一个捆绑式阳具,然后戴上睡觉,感觉好极了。”“我想以男人的身份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凭借着想像力,和塞了袜子的内裤、睾丸激素,以及后来的双乳切除手术,他做到了。他最令人回味的作品传达了他核心存在的欲望。“在我寻找完美的男性伴侣时,我找到了我自己。当我需要一个躺在床上的男人时,我使自己脱离身体,而我的身体变成了他的。”
跨性别的接受程度不应取决于我们必须隐藏或对我们的性生活说谎。楚描述了一名跨性别女性,其治疗师根据她的性趣拒绝了对她的治疗:“真正的男性到女性跨性别者不会这样做。”被接受也不应该取决于我们是否以相同的感觉度过每一天,是否匹配男性或女性的严格二元性别的定义。我们的故事可以变化,并且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我们的故事进行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是正确的: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以各种方式在尝试“成为别人想要的(那种人)”。我们既寻找其他能够接受我们的人(就像沙利文在旧金山所做的那样,就像邓纳姆正在做的那样),也寻找我们想要成为的未来自我。如果这种寻找这是个问题,那么它也是解决方案,就像邓纳姆的回忆录和沙利文的大量日记所记录下来的。“够了吗?”邓纳姆问。“他们”会成为“真正的男人”吗?还是会一直并且仅仅是“痴迷于男性的女孩”?
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吗?沙利文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吗?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很在乎。邓纳姆也是如此,我认为楚也是如此,沙利文也是如此——即使在垂死之际,沙利文也使自己成为了湾区骄傲的跨性别历史学家。他写道:“我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男人,直到我的身体完整,我可以自由地使用它而不感到羞耻。”这样的目标可能是你永远也无法达到的。尽管如此,无论努力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还是一连串较小的时刻,我们当中仍有许多人在试图到达那里。我们分享我们的故事,如果发现不合适,我们就会制造新的故事。然后,我们将新的故事传播到世界上,看看什么能引起人们对我们的共鸣,哪些可能救赎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人。
本文作者Stephanie Burt是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著有《不要读诗》一书。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