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沃森再次接受界面文化采访,与我们谈了谈他眼中的20世纪,以及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时隔一年,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再度来到中国。
2018年,他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在中国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鸿篇巨制以南方古猿为起点,讲述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过程,包罗万象地讨论了艺术、文学、科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人类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给不少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之感。也同样是在去年,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提出了一个热议至今的问题:“从宋朝到现在,中国向我们当下的生活贡献了哪些思想呢?”
在过去一年里,对沃森来说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是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于201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在他看来,这本通过讲述中东和远东贸易史来重写世界史的作品再度验证了他的观点——在思想领域,中国和东方自宋朝以后便被西方赶超了。日前在上海再次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沃森表示:“当中国产出杰出的哲学家或律师,当我们开始遵循中国的法律观念时,我们才算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此次沃森来华的契机是他的《20世纪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中文版在十余年后再版,这本书也是沃森最早写作的一部思想史作品。尽管《20世纪思想史》仅仅关注过去一个世纪的思想发展历程,但其篇幅和知识密度不亚于放眼古今的《思想史》。
在采访中,沃森回应了部分书评人对他过于求全的历史书写方式的批评。他认为历史书写在本质上就需要有大局观,在思想史的领域尤其如此,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往往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发生的。在他看来,科学、自由市场和大众媒体是推动20世纪发展的最重要的三股力量——若将《20世纪思想史》和《思想史》相对照,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些新思想在之前更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却都在20世纪开花结果。
20世纪尽管承受了种种灾难,但在思想方面大获全胜,沃森认为,在21世纪的当下,人类又站在了某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档口。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对互联网发展至今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忧虑、在面对混沌现实时当下年轻人的“受害者心态”,以及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威胁。
沃森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左翼对“社会公正”——即平等——的过度强调。在他看来,左翼追求的绝对的平等反而让他们成为了历史中的反动力量——最后他们既没有获得平等,也似乎没有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沃森就赞许右翼。他在《20世纪思想史》的结语中写道,尽管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自由市场制度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右派理论就是真理,“无论福利国家如何令人不满,但它确实改善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如果遵照放任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这种改良就不会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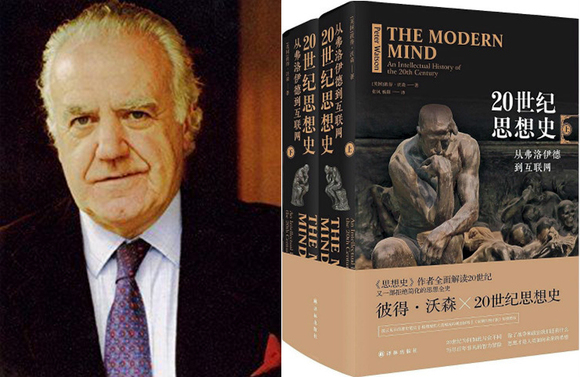
《20世纪思想史》在英国出版时的首版标题是《惊骇之美》(A Terrible Beauty),取自爱尔兰诗人E·B·叶芝的诗句:
“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
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
而中文版的书名沿用了美国版的“现代思想”。与“惊骇之美”所强调的20世纪苦难与成就交织给人带来的震撼相比,这个书名或许更加强调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契合中国当下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代”状态。沃森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不过近几十年来,它又一改过去的封闭,向整个世界敞开了胸怀,如今正跻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行列,并将目光投向未来。”在沃森展望的未来之中,中国的哲学、法律、艺术不仅应为全世界的现代思想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能成为引领者,而这样的未来,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界面文化:这两本思想史作品读下来,我能感觉到你对个人观点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你自己是如何看待20世纪的呢?
彼得·沃森:鉴于20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世纪。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很长时间里没有大型战争的时代。在那段时间里,自由民主的表现不错。当然现在自由民主正在遭到威胁,全球各地有不少独裁主义者上台。如果我现在来写这本书,我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即“民主”的概念遭遇了威胁、独裁主义领导者被票选出来。这本身并不让人担心,让人担心的是我们该如何行动。技术正在操纵民主,无论你当下在写怎样的史书,这是一个你无法忽略的问题。
界面文化:在《欧罗巴一千年》(Centuries of Change)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认为,20世纪最大的变化是交通、战争、预期寿命、媒体、电子和电气设备。在你的书里,科学、自由市场和大众传媒被认为是塑造20世纪最重要的力量。能谈谈你对莫蒂默的观点的看法吗?
彼得·沃森:显而易见,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我不认为它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它改变的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被照顾,而这显然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家庭的概念正在瓦解的时候。
中国或许在家庭照顾老人这一方面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这也许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优势之一——家庭能够照顾老人——西方就没有这种观念了,因为照顾老人的社会成本就很高。我同意预期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至于交通……从没有火车到有火车,从火车再到高铁,哪个变化对世界来说意义重大?交通是一个19世纪出现的事物,而不是20世纪出现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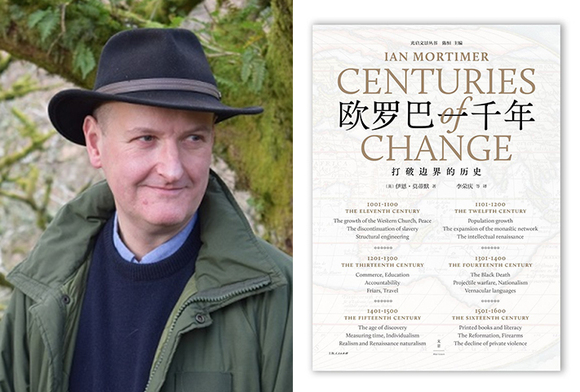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和伊恩·莫蒂默都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20世纪是被科学支配的世纪,科学也将持续成为21世纪的一股主要力量。在写《20世纪思想史》的时候,你是如何处理科学和其他思想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呢?
彼得·沃森:科学硬生生地挤进了历史之中,比如说物理学,它除了是一个知识突破之外,还带来了原子弹、人造卫星、宇宙学等重要发现与发明,而这些又跟数学重合。如果我们真的开放心态,我们还会发现它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冷战。
所以它真的塑造了20世纪,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我认为我们无法回避科学。很多人认为“科学”这个词令人反感,所以我尝试更多从具体学科的角度来写作。我认为继物理学之后,另外两个非常有趣的科学学科是遗传学和人类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种多样性、人类生活经验和传统的多样性超过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科学。但它的曝光度不如基因学和物理学,因为它是“软科学”。
界面文化:科学的崛起和文科的式微是20世纪的一个显著现象。实际上你也在书里写了,哲学家和艺术家不再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某种新的思考方式,他们的作用被科学家取代了。这种力量转移至今还在发生,我们看到全球各地的大学文科的规模都在缩小。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也在《画地为牢》一书中指出,像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软科学”虽然是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它们的重要性也被大大低估了。你对此怎么看?
彼得·沃森:我刚刚说了,人类学被低估了,对此我同意莱辛的观点。社会学,在我看来,因为和政治学太过重合而遭到了不少损失。就拿英国来说吧,社会学科基本就是左翼学科。尼采说过,世上本无事实,只有阐释。我认为人们对社会学表示怀疑是因为它提供了太多左翼答案。
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法国的书,我阅读了很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资料。法国大革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关乎自由,而关乎平等。事实是,你不可能同时拥有自由和平等,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当人们开始担心平等问题时,恐怖和暴力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这是法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自那时起,法国人就一直担心平等诉求背后是否潜藏着以暴力相威胁的暴民。
所以我认为,很多人对社会学冷眼相对,是因为它只能给出政治性的答案。没错,我们是会做社会调研,但社会调研得出的结果是有待解释的数据而不是事实,而我们有各种方法去解释数据,所以人们不太相信社会学了。但我不认为莱辛的说法完全错误,人类学施加的是正面的影响,它的确让人们意识到了种族、文化、传统、信仰的多样性。

我在想文科式微是否是个伪命题。在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学习文科的学生数量又变多了,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STEM学科。但数据的确告诉我们文科正在结束颓势。
界面文化: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两天前我读到一篇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中国无需在意文学奖、和平奖或经济学奖,只需将精力放在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这些科学类奖项上就好,因为对于人类未来而言,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科学领域。
彼得·沃森:对此我没有答案。不过说老实话,我认为人们已经不在意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奖项授予了太多不值一读的作家。但如果你赢得的是“硬科学”奖项——医学、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是一项备受关注的成就。我同意那位文章作者的观点。
界面文化:在去年的采访里,你提到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但没有为思想史,特别是科技革命做出太多贡献,而科技革命又恰好是过去一千年以来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你上次中国之行时曾因这一观点收到过一些负面的反馈。如今,你对这个问题是否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彼得·沃森:过去一年里我读了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那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作者讲述的中亚历史通常是被从西方史里剔除的。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书里没有涉及任何中亚提出的新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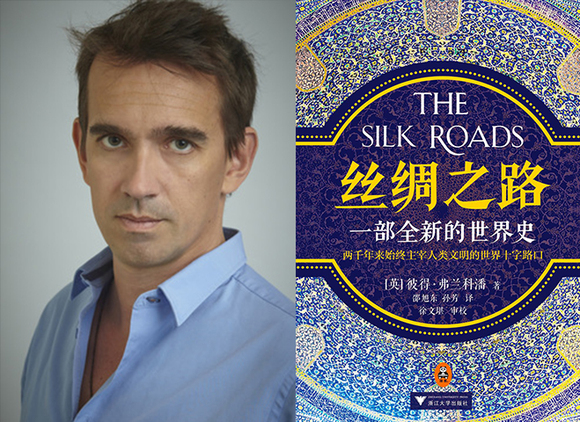
我认为21世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将为世界做出何种贡献。你刚才提到了诺贝尔奖,是时候由中国人获奖了,是时候让我们来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了。是时候让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和特朗普总统起争执的政治实体,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和科学实体了。你不这么觉得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已经引领世界了吗?你希望看到那一天吗?
但说实话我对当代中国文化还不太了解。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西方看到过不少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它们很棒,但我不认为当代艺术能够起到引领人类社会前进的作用——这不仅仅针对中国,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旅英华人作家张戎(Jung Chang)上周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新书,在英国收获了不少好评。我指的是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作家和中国科学家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界面文化:对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化来说,20世纪的主要任务是与现代性和解,特别是向西方学习。在我看来,思想史之所以被西方思想家们垄断,原因在于是西方制定了现代世界的规则。但既然现在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场游戏了,我们是否还能相信过去的文明等级?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又应该从什么角度衡量文明等级上的位置呢?价值观或者生活经验?
彼得·沃森:不。文明等级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你说的没错,显然西方以自己的方式制定了现代世界的规则,但文明等级在二战时就濒临瓦解,先是有印度人援助英国参战,然后是1949年的新中国革命。如今的文化位阶已经展现出了变化,中国和日本的建筑师正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实力,比如说来自中国的贝聿铭;日本人的橄榄球也打得很好。是的,旧秩序需要瓦解。但我认为,当中国产出杰出的哲学家或律师,当我们开始遵循中国的法律观念时,我们才算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这需要一些时间。
对于衡量标准我没有答案。也许会是中国引领世界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那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中国提出了一个新政策,所有其他国家都跟着做。
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想象力。
界面文化:20世纪以“现代主义”为开端,以“后现代主义”为结尾。正如你在《20世纪思想史》中所写,传统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战争。我们现在是否还在“文化战争”的余波中?在当下,我们能给这场争辩提供哪些新的观点呢?
彼得·沃森: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退却得很快,除了建筑学领域。20世纪建筑学发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玻璃,它让建筑师得以将外部环境引入室内。至于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真理与权力,我认为人们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回归到历史叙述就是讲述事实的认知上,尽管没有人否认我们同时有更多不同的阐释方式。
后现代主义已经被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所取代,这些问题是当下人们关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女权主义正在接近尾声,人们已经接受了它的观点,然后将注意力投向别处。好吧,我知道很多女性会说我现在还是面临很多歧视,但社会整体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性别歧视正处于从人类思维中根除的阶段。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我们还没有为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找到一个新的词汇或新的概念。我的意思是,你刚才说后现代主义被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取代了,但这两个词都不是一种统摄一切的概念,它们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后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曾经是。
彼得·沃森: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警觉主义”(wokeism)。在很多国家,年轻人都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这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或你也可以认为是我们时代的反时代精神。
在英国和美国,大学被普遍认为应该是一个政治安全的地方,不应该挑战任何主流观点——这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一点极具代际性。对我这一辈来说,我们认为大学就应该是挑战既有观点的地方,如果你不曾直面质疑,如果你未曾在矛盾性面前败下阵来,你压根就没有活过!当然,这一切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之一就是所有观点应该被一视同仁,某样东西占据卓越地位这种事是不存在的。
界面文化:20世纪许多思想家参与了资本主义的讨论。在2019年,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越来越大的经济不稳定和意识形态冲突中。所以谁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谁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
彼得·沃森: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下神坛了——我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点犹豫——因为它与自由民主显然有着很大重合。在19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我们认为自由民主是唯一的前进方向,历史已经终结。事后看来,那是一个多么天真可爱的想法啊!历史当然没有终结,虽然民主还活着。
我认为2008年以后,资本主义就发生了改变。我们迫切需要看到一本讲述2008年的书,因为很显然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但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2008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金融运作的方式出现了重要变化。我不认为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替代方案,但真正的问题是民主政体的运作方式。大银行家是否因为他们的不端行为获罪?显然是没有,因为银行“大而不能倒”。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但它的光芒的确在2008年后黯淡下来。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大清理。在某个阶段,我们需要承认一些机构是失败的,一些人需要为此负责被送进监狱。

界面文化:近些年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极端右翼和民粹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者似乎正在快速失去阵地。回顾20世纪,左翼似乎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后就开始失去动力。自由主义者可以从20世纪中学到怎样的教训呢?
彼得·沃森: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自由主义”有两种含义。一些人相信自由主义经济,一些人相信自由主义道德,要对两者加以区别。我认为在道德层面我们是越来越自由了,没有人真正反对这方面的价值。经济自由主义却在面临一些威胁。
但我认为一个根本性的、但没有人提起的原因是这个:你知道“房间里的大象”这个词吧?现在最大的房间里最大的大象是遗传学——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聪明。这个说法政治不正确,我们不能放到台面上说。但问题是,这就是很多异议出现的原因。在未来,中产阶级将需要照顾工人阶级。在英国,51%的国民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太穷了。他们的贫穷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吗?还是因为他们思路不清、难以做出最佳的个人理财决策?可能两者都有吧,但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很多人意识到在社会工程上下功夫是有限度的,你可以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它不能持久。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芬兰和加拿大都尝试过给穷人发钱。但这个政策太昂贵了,实验持续六个月就不得不宣告失败。人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人就是永远无法爬出生活的黑洞——当然左翼是反对这个观点的。基因层面的分析听起来很残酷,但如果它是对的,就意味着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需要照顾经济状况较差的人,需要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显然,我们需要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政策。但我认为基因学决定了不是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当然,较为贫穷的群体里也有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但其数量远远少于那些不够聪明能干的人,那我们就需要找到方法帮助那些有希望的人。
21世纪,人类的寿命会延长。人们必须赚很多钱来照顾自己,也帮助他人,社会中一半幸运的人需要帮助另一半不那么幸运的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税收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向国民提供国家经济服务,比如说在两年时间里你需要以最低薪资工作,所得薪水上交国家,然后你可以回去做你平时做的工作。我们需要沿着这些思路去思考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2008年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当下的负债我们永远不可能偿还得清,我们需要有新的经济、社会和道德思考。永远不要忘记,亚当·史密斯不是以经济学家,而是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写出《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指的不仅仅是效率,也指向道德。
界面文化:我们刚才聊到了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右翼常常指责这是左翼在玩弄身份政治。你是否认为身份政治是自由主义的绊脚石呢?
彼得·沃森:就某个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从定义上来说,左翼可以说是贫穷翼,因此他们的政策反映的是他们眼中的社会公正,你甚至可以说反映的是他们的复仇。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社会的运转方式。有人认为社会是对个体的打击——这里我又要引用亚当·史密斯了——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极端左翼的政策是无法实现的,二战后的东德就是一例。之前我提到了法国大革命,人们深受平等观念的吸引。人们可以在“一人一票”上平等,可以在神的面前平等,可以在尊严面前平等——我相信这些,但我不认为我们能在其他方面实现平等。
界面文化:《20世纪思想史》最早在2006年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今年我们迎来了再版。它与《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两本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彼得·沃森:我在1997年开始写《20世纪思想史的》,当时正值20世纪末,写作一本这样的书恰逢其时。坦白说,因为那本书太受欢迎,出版商就与我商量能否写一本20世纪以前的类似作品,于是就有了《思想史》。英国市场上还有一个再版版本是插画版四卷本,标题就是《思想史》(Ideas),从史前文明一路讲到万维网的诞生。
界面文化:你是怎样开始《20世纪思想史》的写作的?
彼得·沃森:1997年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文献,并找了30位专家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等等,与他们讨论他们所在的领域。我在采访过程中提问了在他们各自领域中诞生于20世纪的最重要的三个思想是什么。我本来以为会收获各种各样的答案,但事实上他们给出的答案有很多重合。这帮助我选出了那些值得放进书中的内容。
在写《思想史》时,我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所以基本上,我是借助专家的智慧、汲取他们的观念来形成一本书的结构。
界面文化:写这两本书时,你咨询的是同一批学者吗?
彼得·沃森:只有一两位是。比如说剑桥大学文化史学者彼得·波克(Peter Burke),还有来自北爱尔兰的科技史学者彼得·鲍勒(Peter Bowler),他在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意见。
界面文化:包括《卫报》和《纽约时报》在内的不少媒体曾在书评文章中评价你是一个“大局至上主义者”(Big Picture man),你的写作就像是百科全书式的人名集合。你是如何权衡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的优缺点的?
彼得·沃森:我觉得我的大局观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认为,一本书最好能有一个结构,有结构你就更容易记住很多东西。很多人抱怨互联网提供的只是信息不是知识,原因就在于此。在我看来,如果你在书写历史,那你本质上就是在关照大局,你要做的就是赋予它一个结构。所以人们说我是一个“大局至上者”的话,我认罪。(笑)
思想史或文化史的有趣之处在于,我认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一本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化史和政治史之间关系的书。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渴望能阅读这样的一本书。在政治史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治家出生和死亡,协议生效和失效,君主上台或下台,你都能看到一个日期,政治史是被日期驱动的,但我们不能这样看待思想史。
在写《20世纪思想史》时,我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当时BBC采访了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他被问到在漫长一生中最非凡精彩的事是什么——他于1909年出生,1999年去世,所以他的人生就是整个20世纪。他回答道,我见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俄国革命、一战、二战以及其他的战争,绝对的恐怖,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被疯狂所支配。在政治上,20世纪发生了太多糟糕的事情;但在文化上,比如在科学、绘画等方面,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想想这个反差,多么不可思议——一方面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坏事,另一方面那么多好事也发生了。
界面文化:你是否想过从微观角度书写历史呢?
彼得·沃森:我有想过。我写过一本现代德国思想史的书(《德国天才:欧洲第三次文艺复兴、第二次科学革命与20世纪》),我觉得那也是一本关照大局而非微观层面的书。我如今正在着手写一本关于法国的类似题材的书。
所以我的答案应该是不。(笑)我的意思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有趣的历史书已经有很多了,但到目前为止这不是我感兴趣的方向。
界面文化:你如何评价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最新的作品《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呢?那也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以胜利者的语气为科学理性和自由人文主义做出了辩护。
彼得·沃森:他阐述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的寿命更长了,更健康了,但我们真的更幸福了吗?我不想批评那本书,我认为那本书不错,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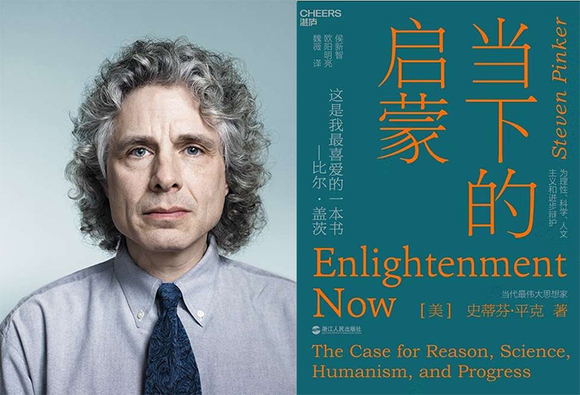
如果他能讨论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岂不是更加有趣?我认为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并不全部都是正面和健康的。不过我开始认为,我们正在接近互联网第一阶段的尾声——我们开始驯服网络,而不是让它统治我们。过去的许多技术进步都是如此,人们一开始忧心忡忡,然后随着新技术被驯服,人们的担忧消退。有证据显示,年轻人开始认为除了互联网之外还应该有真正的生活,互联网应该被正确地使用。
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有怀疑精神。我很肯定他也会自称是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但在那本书里没怎么反映出这一点吧?我始终觉得,保持一点怀疑精神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