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集中的精神不安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沮丧。

“非常聪明,非常反传统的”……扎迪·史密斯。
《大团圆》(Grand Union)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汇集了11篇新作与之前出版过的作品。她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电台采访时说,她不喜欢整洁的外形:“完美的形式让我很反感。我的小说也是这样——我知道它们应该简短而克制,但相反,它们就是个垃圾袋。”
她的五部长篇小说并不是“垃圾袋”,它们由人物和故事主导,而非由形象主导。即使是像《论美》这样统一的小说,也不会像契诃夫的小说那样,在隐喻中寻求声音和感知的结合:它对跨越时间和不同视角的喜剧太感兴趣了;它对情节发展太感兴趣了,就像小说所应然的那样。
然而,在本书的开篇故事中,史密斯恰如其分地将她各种自然的能量注入到了一个狭窄的契诃夫式框架中。《辩证法》和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一样,故事发生在欧洲的一个海滨胜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试图享受假期的单身母亲忙碌而焦虑的心境中,并呈现了鸡的形象:被烧烤然后被吃掉,骨头埋在沙子里,最后结合了扎迪对迁徙和性别的思考——在一家工厂里公鸡母鸡被区分开来,所有公鸡都被“扔进巨大的磨缸,被活生生地切碎”。
下一篇《感伤教育》也采取了经典短篇小说的形式,一个年长的叙述者(在这里是另一个紧张的母亲)的声音和年轻时的她(一个奋发努力的剑桥学生)的所做所为,二者交织在一起,像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一样闪闪发光。人物卷入其中,观察令人振奋,动作性感而滑稽,因此我们并不介意这个故事溢出其形式,而年长的叙述者最终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不过,我们可能很期待阅读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在这之后,小说形式激增。有自传体小说,推理小说(包括一个很有创意的片段,讲述了迈克尔·杰克逊带着伊丽莎白·泰勒和马龙·白兰度出城逃离911的都市神话),也有推理小说和寓言的混合体。《两个男人来到一个村庄》中有一个完整而可怕的布莱希特式寓言,还有大量元小说都在努力剥离叙事元素,其中一些——比如急躁而曲折的《父母的清晨顿悟》——让人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然而,小说《受阻》逼着我们对这种不安分的实验吹毛求疵。在这里,陪伴我们的这位作家早已取得成功,但不知何故失去了信心。她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平行项目”中,继续工作,养狗,寻找残缺的能量。“这些天我喜欢碎片。我不认为碎片有缺陷或不够完整。正是完美主义者模式让我一开始就陷入这样的麻烦。现在我赞扬半完成的、未完成的、破碎的——碎片!我凭什么拒绝碎片?我凭什么说碎片是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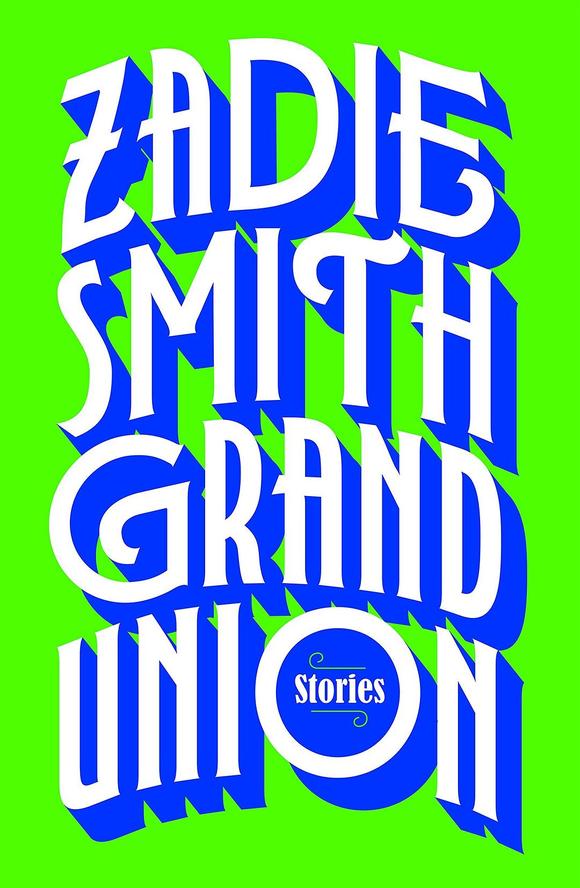
当然,我们凭什么?在《大团圆》中,我们没有一刻不被款待,也没有一刻怀疑我们是在与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为伴。唯一真正的遗憾是,有时史密斯自己似乎在怀疑这一点——或者也许是被许多关于她身份的说法所压倒。我们本来会跟随《刚刚好》中生动逼真的孩子们进入一部小说,但这个故事让人感觉被抛弃了,而不是被精心雕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们大学里围绕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羞辱而产生的焦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并不需要精心设计的推理小说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教授们将巨大的箭头指向彼此。在自传体小说《懒河》和《闹市区》中,神秘叙述者似乎是史密斯除了作家身份之外所是的一切,其暧昧、半虚构的姿态削弱了敏锐、诙谐、凄凉的观察,因为权威感受到了剥夺。
同样,我们很清楚我们在阅读《凯尔索解构》时(这篇小说重建了1959年在诺丁山被种族主义者杀害的凯尔索·科克伦的最后几天),这是一位巧妙的作家正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关于真实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轻松美丽的场景和随意而完美的对话告诉了我们这点。一些时刻有着同样的优雅,比如,当史密斯从作者角度告诉我们,目击者对凯尔索被杀的描述可以排列成一首令人不寒而栗的诗的时候。相比之下,元小说的闯入令人费解,如凯尔索的女朋友被发现绣了咒语而不是谚语,地铁站写着“托尔斯泰,莫里森”,以及鲁尼医生给凯尔索开了一个处方,上面写着“从YoungIrishWriter@gmail.com到OlderEnglishWriter@yahoo.com”。为什么扎迪·史密斯的故事里需要莎莉·鲁尼(爱尔兰作家,生于1991年——译注)?她是否真的同意鲁尼医生的这个“处方”,即把一个故事说成是“一种寓言或训诫的说明”,是“有点不诚实”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此时有像科克伦这样重要的故事要讲,而且是像史密斯这样的作家来讲述它?
这实在令人沮丧。因为无论是在相当传统的故事——如《束身内衣中的阿黛尔小姐》中,她派一位年老的变装皇后奔跑穿过纽约,还是在超现实主义的幻想故事——如《大团圆》中,女儿和她母亲坐在一起,她母亲“死了,看上去好极了”,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不受约束的史密斯在纸页上自由飞行,这景象是如此壮观。最重要的而且无疑指向史密斯未来的是《献给国王》,它以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挪威作家,著有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的自传体方式,讲述了作家“我”去巴黎见一个朋友的故事。在这里,自传小说的约定将史密斯解放出来,让她完全沉浸在她那非常聪明、非常反传统、繁复多重的自我里。这位叙述者没有停下来为自己的故事担忧,相反,她整晚都在谈论,就像谈论女人和时间一样,她也乐于谈论自己“挺刮”的牛仔夹克,并将困扰这本小说集的许多关于沟通和羞耻的争论,汇集成了几则巧妙的趣闻轶事。
这篇小说也溢出了它的界限:晚餐后,叙述者意识到有一个故事她还没讲过。但这一次的溢流是巧妙的,它意味着:最后一个故事,显然是不由自主地讲给我们听的,是关于一个患有抽动-秽语症的人在火车上的故事。他的呼喊“Pour le roi”(献给国王),透过消除噪音的耳机发出的“布朗噪音”和他妻子的自动回复可被听到,仍然是“一种人类的话语,仍然带有某种形式的意义,无论这意义多么微小”。在这本充满怀疑的书中,这种对语言与交流的信仰声明是一种宽慰,它出现在了一个似乎已自我发现并因而相当完美的形式的故事中,真是令人振奋。
(翻译: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