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孙子辈学生”,史景迁认为,费正清的作品足以改变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费正清
今天是著名历史学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逝世28周年纪念日。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界领袖。他的《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作品,都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必读书目。1955年,他在哈佛创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积极促进以社会科学视角研究现当代中国。在费正清70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此对他学术贡献进行肯定。75岁时,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道出自己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也是从费正清自己的回忆录开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开始回顾和梳理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而他的老师、《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作者芮玛丽(Mary C.Wright)是费正清的学生,所以史景迁自称是费的“孙子辈学生”:“我对他心怀崇敬,就如对待一位在你刚起步的时候关注你的长者。对他和他的力量,我从来都仰慕不已。”
本文是史景迁在费正清退休时期写就,从费正清的个人经历开始,剖析费正清学术作品的贡献,并指出他的治学特色。史景迁看到,他支持中国学者、促成中美学者的交换计划,并对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费正清的作品也足以改变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他称得上是“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的大家”。
文 | 史景迁 译 | 钟倩
从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这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费正清是美国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的大家。尽管现在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一职,但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当年。(费正清于1991年9月14日去世)费正清编辑、撰写或者合著的大量著作涵盖了中国外交、制度史、传教史、共产党组织、军事史和对美外交政策各个方面,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研究即使在21世纪,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和可读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足以功成名就了,但是费正清却还要另辟蹊径,用个人回忆录的方式将之记载下来,这便是《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这是一本值得尊敬的回忆录,运用难以界定的混杂文体,记载了费正清那光荣的人生旅程。这本回忆录兼有三种文体特征——文学、历史学和自传,却又不像文学著作那样创作自由,不像历史学著作那样讲求史料,不像自传著作那样审视自我。

但是费正清非凡的素质,让他能够成功地完成这样一本回忆录:超人的记忆力;珍藏了每一张备忘笺和每一封信件;古稀之年仍然思维敏捷如常;从休伦、南达科他,到威斯康星、哈佛及战前的北平、战时的重庆,费正清的阅历相当丰富;对于学术具有非凡的热情和不可动摇的信念,坚信自己所做是一项兴趣盎然的事业,并且传播给每一个人。如此一来,便造就了这本令人钦佩的回忆录——妙趣横生、无拘无束、言无巨细、惊喜连连。
和很多杰作一样,书中费正清所描述的也是一段旅程——一段走向外面世界的旅程。在此期间,费正清从一个视野宽广、雄心勃勃的青年人,靠着超于常人的不屈不挠和勤奋努力,靠着福星高照和无可挑剔的文化交流,成长为一个眼界更为开阔、依然满怀雄心的中年人。到了七十四岁的高龄,费正清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了他的凌云壮志已经得以实现。但是,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年轻冒险者的超然和热忱,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坚信法律胜过道德,并且宣称厌恶“非理性的信仰”。费正清写道:“我所取得的信仰是哈佛以及它在世俗的世界中坚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相信我们那些致力于培养思想自由的制度。”
费正清的回忆录包括七个部分:负笈求学(1907—1931),我们首次发现中国(1932—1935),学会当一名教授(1936—1940),二战时期的中国,中国地区研究及与麦卡锡主义战斗,建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53—1971)和越南战争,晚年的反思及70年代再次访华。
或许是由于所关注的是早年时光——也因为更容易理解,且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我发现前面四个部分更加引人入胜。它们非常有感染力,甚至偶尔充满了抒情的情调(这并不是费正清通常的风格)。无论是早期的哈佛执教,还是在牛津大学获得罗德奖学金研究中国学,抑或在战前的北平邂逅了他年轻的新娘费慰梅(Wilma),费正清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出色。其间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例如,拜访了声名显赫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结识了魏尔特(Stanley Wright)、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及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不过,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文章还是在讲述中国的朋友——在费正清看来,这些友谊是他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绝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成为他事业的巨大动力。这里,在众多美妙的记忆当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蒋廷黻的细致描述,对年轻而才华出众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爱情的记载(林徽因曾是才华横溢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的恋人,梁思成是改革家、哲学家、学者梁启超的儿子),还有在难忘的战争岁月中结识的“万能先生”陈松樵。
实际上在我看来,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未来史学家来说,这本回忆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有关重庆的记载,以及北京高校的教师纷纷流亡西南,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残酷而短视的政策下,在昆明穷困潦倒的点滴着墨。

通过他的战时游历,费正清带领我们清晰地、我相信也是坦诚地见证了他意识形态变化的过程:他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稍稍偏左的中间自由派人士,越来越不欣赏国民党,而对于不太了解的共产党心存善意和好感。费正清对国务院的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警惕有加,对他的副手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心存怀疑——费正清崇敬谢伟思(John Stuart Servic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的现实主义和悲悯情怀,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这两人因为正直而遭受攻击、事业受挫,费正清更是如此。
对于我来说,费正清对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黑暗岁月的记载出奇地平淡——大概是伤口仍然太深(而且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依然健在),从而不可能无所隐晦地率直而言的缘故吧。但是费正清确实也暗示,他的表现不可能一直如己所愿。他机智地揭示出,麦卡锡主义的致命伤害在于,它不断地迫使自由主义者进行不必要的道歉,迫使他们表现出既空洞又虚伪的意识形态上的“纯粹性”,迫使他们完整地采取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自保方式,而这正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所试图攻击的。
但是,对于学生对越战的愤怒、这种痛苦对他们思维和事业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东亚研究中个体之间越来越大的断裂,费正清的处理似乎有些草率和漠然。对于这一代大多数人而言,1960年代末期与费正清的友人所生活的50年代早期同样苦闷。“我一一做了回答,其他人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费正清在《亚洲学者集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上回忆起那些辩论。但是,这代人的苦闷远远不止于此。我发现试图接受这种情感非常困难,战争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后果在于没有人能够富有远见地在哈佛开展越南研究。在这一点上,费正清过于自责了。
当我仔细地阅读这本非同凡响而又引人入胜的回忆录时,一个声音反复回响在脑海。当费正清有趣地自嘲,灵巧准确地击中目标,避免与敏感的感情问题正面冲突,谈到长期目标和对人类命运的奇思妙想,坚持努力的重要性的时候,我脑海中的声音便尤其响亮。几乎是到了文末,我才突然明白了赫德先生的话的含义。赫德是186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也曾被这些细枝末节所困扰。“我希望这是有意义的,”赫德曾经写道,“思想指导了工作,也促使了这些工作的成功;否则,我看不到这些工作的回报,也不认为这些思想有什么意义。”赫德没有必要担心他的工作和声望,费正清也没有必要担心他四十余年的努力。这是值得的,成就是永恒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再有另一个中国研究的“总税务司”了。
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出版于1948年。此书将中国的制度史、外交史结合起来,在试图从中国历史来理解现实的美国人中间引起了轰动,很快便声名鹊起。在之后的六年中,随着共产党政权的稳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中断。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费正清一连出版了五本著作,以惊人的数量奠定了他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首席学者的地位。在这五本著作中,一本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文献介绍;一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掌权的文献汇编,附有详细的翻译和注释;一本是介绍如何分析和翻译中国历史文献的教学手册,对于研究生特别有用;还有一本是重要的两卷本专题论文,是在费正清早期在牛津大学的博士生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关于1842年到1854年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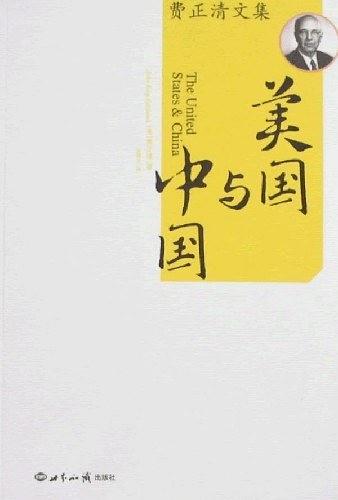
这些成就非凡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费正清毫不懈怠的充沛精力,另一方面得益于费正清慧眼识英杰,与他合编、合著的研究者都具有出色的才华。此后,从19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费正清和学者持续不断地合编、合著或自撰了有关远东的教科书,关于中国军事史、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儒家思想和实践,以及传统清代官僚的作品等数卷论文集;还出版了更多带有注释的文献汇编,整理汇编了大量的赫德信件,并分别出版了五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如果查看一下费正清1983年到1986年间的作品,研究者可能会感到震撼,但并不会惊讶,此间费正清至少出版了六部作品,当然还有其他并未记录的学术作品。这都不足为奇。到了八十岁高龄,费正清仍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笔耕不辍。
在他最近的六部作品当中,费正清的研究依然覆盖了很多学术议题,如同他刚开始学术生涯时一样。与苏珊娜·巴内特(Suzanne Barnett)合编的《中国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hina)一书,就收录了很多现代学者对于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早期著作的评论。费正清总是提醒中国研究的学者,不要忽视教会档案中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资料,为保护和研究这些档案,他还孜孜不倦地寻求经济上的资助。这本书中汇编的文章证实了费正清的观点:教会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于社会阴暗面的研究,例如,在传统儒家礼教边缘的中国教派和秘密社团,以及受过一点教育的文人想通过继续深造来摆脱社会底层地位和繁重劳动的循环。名落孙山的洪秀全,受到了梁发散布的基督教小册子的影响,后来一举成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声势浩荡的太平天国反清救国运动的领袖。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还是默默无闻的,思想的交流仅仅局限在很小的范围,胜利也很小,抑或是欺骗性的。正如费正清在前言当中所反思的那样,传教士先驱“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可能要比对中国宗教的影响大得多”。
从牛津岁月起,费正清便开始关注西方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与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合编的《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回顾》(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是现代学者研究茶叶、丝织品、烟草和石油贸易的杰出代表作。费正清在这本书的开篇便指出,贸易的双方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利润,但是在感情交流上却意义重大。非常矛盾的是,费正清认为只有看到了贸易盈利是多么微乎其微,才能够估量“在美国想象中”的中国的分量。
《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Reading Documents)和《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Entering China’s Service)这两本著作,是费正清与杰出学者合作的成果,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为中国历史教学准备专业参考资料,以及整理和分析相关档案。这也是费正清非常重视的部分。但是《阅读文献》为我们展示了自费正清1952年发表第一本文献著作以来,中国历史研究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本书中,费正清主要着眼于外交政策,着眼于中国满汉官员如何理解、应付令人困惑的西方侵略者,以及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海洋问题。到1986年,编纂者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地方史,开始研究农村的艰难困苦、土地税的形式、婚姻和亲属血缘、对不公正的抗议、小规模非法招兵的形式,等等。中美关系的改变,一直是费正清的核心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引人注目。本书首次收录了很多北京明清第一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献照片和相关资料。
如果说《阅读文献》是一本专业性的著作,未能展示费正清的真实风采,那么《步入清廷仕途》则完全体现了大师风范。此书收录了中国清朝海关的缔造者罗伯特·赫德(后称罗伯特爵士)的大量日记,由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Katherine Bruner)和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共同编纂。这些文字今天看来,不免有些恶作剧和讽刺。费正清喜欢使用双关语和俏皮话,显示出对人性缺点的宽容。如同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我们所认识的费正清一样,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宽容欢快的学者形象。在两句很有个性的话中,费正清总结了他与年长的中国海关末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L.K. Little)的交往。李度已经解甲归田,移居新罕布什尔州,他非常关注赫德日记的出版工作。正如费正清所言,“李度先生性情开朗好动,期望能在一年后将其印行,但实际工作一做就是七年。”

赫德日记原稿现存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图书馆,并有抄本—这本身就是一项丰功伟绩了。根据日记手稿录制的磁带—常常伴以刺耳的枪鸣,听到阵阵的爆炸—之后被送到了哈佛大学,供费正清及其合作学者研究整理。费正清整理的赫德日记从1854年到1863年,这段时间赫德先后担任英国领事馆官员、中国海关官员,后来成为负责收缴西方进口物品海关税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然,中国海关当时是在西方国家控制下)。这些年,赫德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后来成了清朝颇具权势的人物。考虑到赫德的字迹辨认相当困难,口述磁带录音的效果不够清晰,整理出来的手稿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所以当这批手稿被运回贝尔法斯特时,又一一对照原稿进行了校正。费正清对于史料及其用途一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种细枝末节的活儿他最喜欢了。
对于赫德日记的史料编纂还存在其他问题,因为赫德在华生活早期阶段的资料部分或全部遗失。经过仔细研究,编者们发现空缺的这段时间正好就是赫德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阿姚婚恋的时间,其间他们育有三个孩子。1860年代中期,三个孩子被赫德送到了英格兰,从此便与亲生母亲分离了,赫德后来的新娘也无从知晓他们的存在。1866年赫德与他的新娘海丝特·简·布里登(Hester Jane Bredon)在贝尔法斯特成婚,并将她带到中国。在后来公开的日记当中,已经删掉了这段感伤的经历。编者评论说—这确实是费正清的风格—今天的历史学家觉得他们有必要去考察并记录这段被删除的感情:
在赫德时代,按照维多利亚女王时英国的双重标准,有些被称作放荡和见不得人的事,在20世纪末叶的传记作者看来则是有意义的经历。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旧时代的道德标准和实际需要使我们看不到赫德作为中国居民长大成人的记载,包括1859年初期在广州领事馆工作和1859年中期到1863年中期在海关工作的开头几年。
编者所遗憾的,并不是三个孩子的命运,亦非造成这一切的社会环境,而是指丧失了19世纪外交史上珍贵的文献资料。
这本书中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是关于赫德与海丝特的婚姻逐步被披露的过程,直到1870年代末才为世人所知。编者用一连串尖锐的问题重塑了这些瞬间,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的真实性。这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费正清的风格:
赫德于1878年夏天在巴黎和妻儿会面。博览会后,他们有段时间去奥地利的巴特伊霍,再由那里去巴登—巴登。赫德正在忍受着令人无法工作的头痛症—全面衰竭的那一种,其原因一直也没有弄清。他是否工作过于辛苦,过于专注?是不是在中国事务中有什么不可预见的危机使他烦恼不安?是迅速扩大的中国海关业务已非一个人所能管理?是越来越看清楚他的婚姻从来未能成为一种亲密的伴侣关系?—而这或许只能归咎于他那传奇式的天真的求婚,以及对虚有其表的婚姻simplistic acceptance。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甚至无法道这些问题是否提得正确。
提出正确的问题一直是费正清作为历史学家的终身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书评来达成的志愿。他的书评与论文一样出色,《观察中国》(China Watch)便是一本囊括了二十六篇短论文的集子,其中大多是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写的文章。但是,费正清并不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放在一起;相反,他重新编辑、删减、重写和重新组织了段落,使得这些文章能够放在不同的主题之下,因而其价值远非简单的论文之和。论文集的五个标题确实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方面:新帝国主义观、毛时代中国之内幕、中美关系“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和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当然,对于怎样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以及从何处寻找答案,费正清有着自己独到和清晰的见解:从历史当中找寻答案。他耗费了大半生来论证:只有从中国的历史当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将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那些受到他嘲讽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研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知半解。费正清并不认为社会科学的近期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中国,他也不同情那些新加入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研究者(new practitioners),即使他最近合著的《阅读文献》让他注意到新一代学者所能够获得的丰富史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史料实在是汗牛充栋,”费正清写道,“对于政治学家来说,史料又实在是纷繁复杂。”
那么,费正清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着眼的有价值的课题是什么呢?例如,对于西方社会相当普遍的人权问题而言,他是人权相对论非常坚定的信仰者。他相信中国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有着不同的方法;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和谐而非斗争的观念;中国人对历史上的领袖和时机也有着不同的见解。费正清试图展示,这些不同源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包括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官僚体制的本质、统治和皇权的理论,以及史料记载本身的影响。我想费正清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这些不同和根源,才导致了美国在过去两百年中对华传教、商业、外交和军事冒险的失败。(在这本引人入胜的集子中,最好、最睿智的论文当属关于麦克阿瑟和史迪威的文章,费正清从容地思考了二者的自负、对中国的无知和狂热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是,当费正清试图将过去与现在相联系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例时,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说,以下是费正清对“大跃进”根源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场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农业、工业和民族士气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所有的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治理国家(经世)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分析“大跃进”,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徭役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妙方法有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常平仓”和在边境上利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防范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学者型官僚的这些巧妙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效果如何,至今基本上没有答案。这些学者型官僚,代表着统治者实实在在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管制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们的生活。
当然,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在字里行间还蕴含着深意。但是,人们可以争辩,正是那些“一窝蜂”进行社会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让我们最好地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关联性。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儒家官僚体制下的经典文献中跳出来,开始真正地发现土地所有制的模式、宗族组织、中国城市的寄居者、争取社会公平权利的妇女团体,以及大量的地方现象、价值观,从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众人愿意臣服于这种统治模式。
正如费正清在这本书的空白页漫不经心地写道,“汉学就是吹毛求疵者的天然栖息地”;而人们之所以欣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这些语句,不过是因为费正清激发读者去深入思考更复杂的历史因素及其影响。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书的开篇,费正清更是直接挑战他的读者,引发更多读者对被义愤激荡的中国近代史的兴趣。它婉转地暗示,只有费正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中国的过去相联系。但是,他确实是一位机智的学者,认识到了作为“一位退休教授,他不用关心任期,也不用在意声望”,他的下一步任务就是充当“下一代学者的阶梯”。费正清的这本“家酿”没有任何注释,因为他觉得注释会“引起误解、讨厌和不当”;这本书也没有任何参考书目,因为费正清已经花了大半生的功夫来整理文献,“已经够多了”。除此之外,费正清还按照个人偏好使用了罗马拼音系统,因为没有任何现存的拼音系统让人满意。简而言之,这像一场斗志昂扬、知识渊博、妙趣横生且时而令人愤慨的中国革命历史之行。显然,费正清很享受写作的过程,让读者也乐在其中。
尽管费正清尽量避免让《伟大的中国革命》显得过于学术,但这本著作确实是学术界最新的成就,这与费正清编纂或合编了历史跨度从19世纪、20世纪到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不无关系。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杰出的汉学家对于这段冗长复杂的历史的总结。为了表达他的敬意,费正清将这本书献给这些学者,并且在附录中罗列了相关文献。这本编年史涵盖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在西方冲击之前中国原生的商品经济、对抗国家政权的地方分权势力的崛起、汉族自由主义精英的形成,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人身羞辱的意味。费正清一次又一次敏捷地捕捉了这些经历。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奇耻大辱,费正清写道:
对于极讲面子的中国人,在包括许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内的冷嘲热骂的群众面前挨打和受辱,就像剥他的皮一样。
如此简洁的语言强而有力,颇能感染人。所以,用简短的语言描述特别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技巧,从而让读者随着文字感同身受。
太监们多半来自华北,割去了睾丸和阳具,然后用塞子堵住尿道伤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后尿出来了,这个太监就有用了,否则他很快就会死去。
像这样生动的旁白,常常能够吸引读者—费正清是否担心读者会走神?—即使并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关于嫔妃是如何被送上龙床的细节,费正清告诉我们,这都是“民俗学”。臭名昭著的好色军阀的阴茎大小也有记载,尽管“这些资料都没有得到证实”。试图验证这些史料的做法,显然会贻笑大方,也会太学究气了。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五十年来不断阅读和思考中国的过程中,震撼他的、愉悦他的、激怒他的和吸引他的所有精华。他促使我们去思索“革命”—无论伟大与否—正如朝代更替的周期一样,是永恒变化着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是我们的,并非深藏于中国社会,而我们使用时就要后果自负。确实,中国一直在试图“逃脱历史的羁绊”,但即使是一场革命,可能也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费正清在此书的开篇就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节奏、历史进程的浓缩及历史在地理上的集中,让人难以想象,由此也难以正确地估量:
中国四千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尼河,恺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如费正清这般完成如此多高质量的汉学著作。而今他仍然笔不停辍,沉浸在他喜爱的议题中,让读者甚感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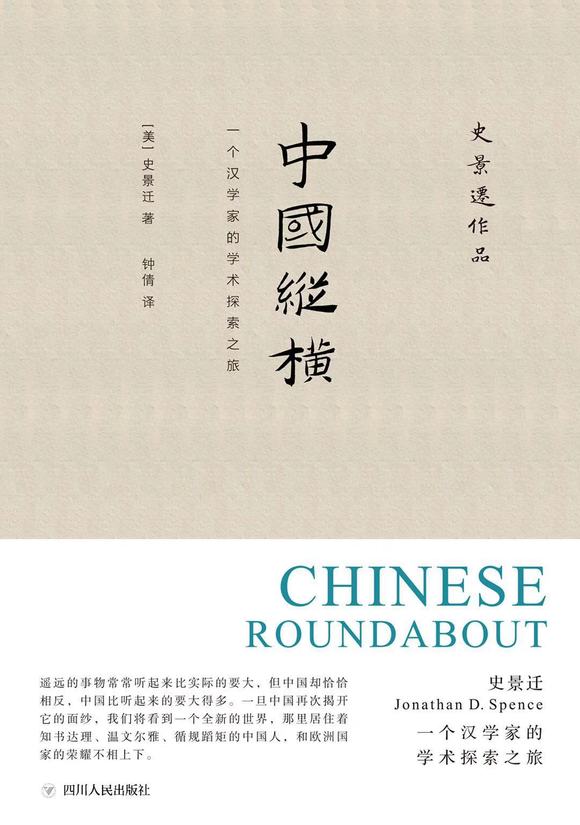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一书《费正清》一章,较原文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