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辛辣的讽刺作品,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地下出版物,都曾是冷战时期文艺领域对抗的武器。

乔治·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
1991年的一个秋夜,我站在萨兰达一座破旧别墅的屋顶露台上,旁边有三位上了年纪的前阿尔巴尼亚国企高管,这是自1945年以来他们首次回到阿尔巴尼亚。如果用一幅景象来概括冷战的可怖和毁灭,那就是大卫·斯迈利(David Smiley,英国特种部队和情报官员,在阿尔巴尼亚和泰国担任特别行动长官——译注)于寂静中擦了擦眼睛,在科孚岛(Corfu,位于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中的岛屿,隔海峡与阿尔巴尼亚相望——译注)的灯光下望向隔岸冰冷黑暗的海水——1949年10月的一个相似的秋夜,他派出一队反对派,代号“小鬼”(Pixies),意图在阿尔巴尼亚发动叛乱。
与此同时,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反共产主义间谍活动的苏联特工金·费尔比(Kim Philby)发出了线报,斯迈利的手下在着陆时就遭到伏击与暗杀。斯迈利在特别行动执行处的同事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只能私下默默抱怨道:“我们本可以拯救阿尔巴尼亚,但我们没有成功,阿尔巴尼亚成了奥威尔笔下对苏联的讽刺对象。”
在邓肯·怀特(Duncan White)这本关于冷战时期文艺领域明争暗斗的作品、充满野心且收获颇丰的《冷战勇士——文学冷战中的作家们》(Cold Warriors: Writers Who Waged the Literary Cold War)一书中,金·费尔比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严格来说,费尔比并不是一个作家,但他是冷战双方都致力于渗透、理解和颠覆对方的一个标志。而如此说来,这一扭曲的标志便成为了作家的必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美苏双方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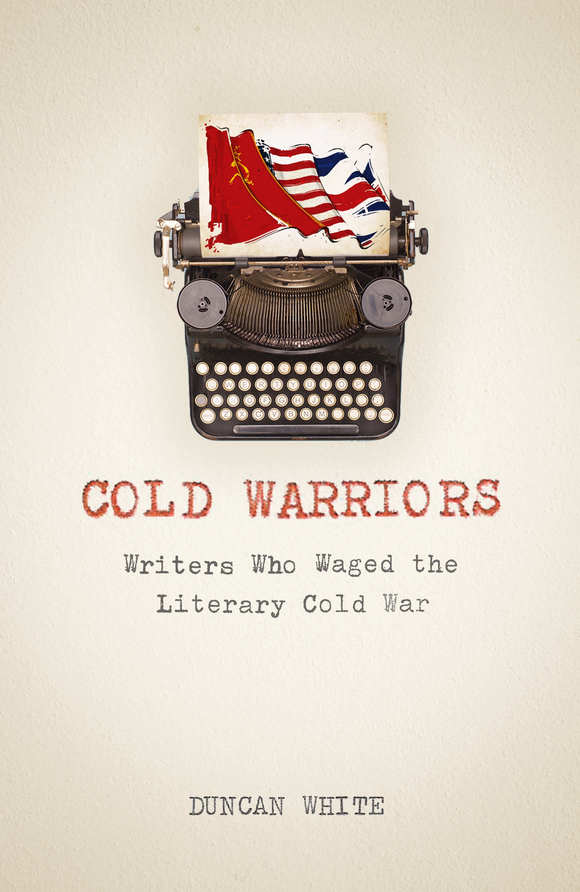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和西方都担心阿尔巴尼亚等弱小国家落入对方的魔爪(帝国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冷战双方都把文学作为斗争的第一线。对于秘密资助《文汇》和《新世界》等左翼杂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来说,书籍是“(长期)战略宣传中最为重要的武器”。在不同阵营的背景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的珍贵笔记和草稿“就像原子弹一样危险”。因此,书籍也像手榴弹一样被扔进了敌人的领土:1952年至1957年间,中央情报局代号为“AE-恐龙”(Aedinosaur)的行动从西德三处地点发射了数百万个10英尺大、内装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一书的气球,这些气球被投放到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上空,而那里的空军则奉命将其击落。
正是“一代人的标志性作家”,乔治·奥威尔给出了“冷战”这一命名(一般认为,“冷战,Cold War”一词最早是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在为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演讲稿中首次使用的——译注)。在西班牙内战中,奥威尔、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和斯蒂芬·斯班德(Stephen Spender)都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奥威尔曾写道:“我们一开始是民主的英勇保卫者,后来却溜过边境,而警察正前脚后脚地追捕我们。”奥威尔不仅被民族主义者的子弹打中了喉部,还被狂热的英国共产主义者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托洛茨基主义,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列昂·托洛茨基,主张工人阶级先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译注),而托洛茨基(Trotsky)则是被斯大林的情报机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特务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刺杀的。在许多年后,我曾见过该情报机构招募的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的遗孀,虽然她与丈夫曾被监禁数年,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们的政治信仰,她也并不后悔,“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读了三四遍毛选1-4卷,”而且“很喜欢他那罕见的幽默感” 。
不过,伊莎贝尔·柯鲁克(Isabel Crook)或许已经忘却了幽默在冷战时期曾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东西。在冷战期间,大约有240万人因“幽默”而入狱: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因写了一首关于斯大林粗壮手指的讽刺短诗而入狱,索尔仁尼琴也因为讲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入狱。而明显缺乏幽默感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则为结束冷战做了不少工作。当捷克剧作家、反对派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提议到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一起抽一支北美印第安部落送给他的“和平烟斗”时,他结结巴巴地说:“但我……我不抽烟。”
虽然有着诸如击落气球的摩擦,但冷战本身就是一场严肃而致命的冲突,尽管在冷战早期时候,人们似乎很难将其认真看待。乔治·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经历的真实记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只卖出了638本。当他的作品与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被审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或者用怀特的话来说,小说,而不是新闻或回忆录,才是“表达极权主义本质最有效的方式”。
美国小说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后来是如此解释的:
读者对他们所认知作家的看法,也许并不是不信任,而是另一种信任……而我们所能做得更好的,就是发现那些可疑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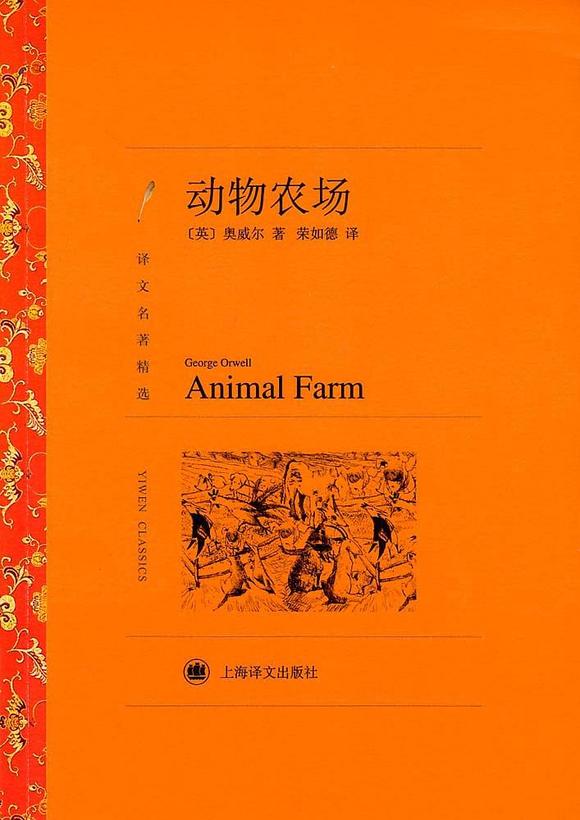
奥威尔在三周时间就创作完成了《动物农场》,这本书讽刺了斯大林主义和他在西班牙目睹的疯狂清洗——“秘密警察维护的特殊世界,舆论审查,酷刑和诬蔑审判。”而他又花了三年时间创作了《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于1949年出版,书中的背景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未来的英国。怀特善意地提醒我们,书里的英国只是大洋国的一个殖民省区,被命名为“第一空降场”(Airstrip One)。而《一九八四》一经出版,立即被认为是“文化冷战中最强大的武器”。
在铁幕之下,斯大林的手下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坚持认为,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因为“除了国家利益,文学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利益”。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鼓励大批作家集体创作关于他们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的小说。而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后果相当可怕。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就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不得不撕毁、吞咽或埋葬自己的作品,她认为在斯大林残酷的统治下“没有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出版。
苏联小说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便是当时无数平庸作家中的一个。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家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他曾在一封信上签字,导致许多作家被捕。而更糟糕的是,据估计,有1500名作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其中就包括曼德尔施塔姆、伊扎克·巴别尔(Isaac Babel)和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但也许法捷耶夫把灵魂卖给“领袖斯大林”的代价太高了,1956年5月13日他选择了开枪自杀。在法捷耶夫的遗书中,他哀悼了文学如何被“贬低、迫害和摧毁的”,以及最优秀的作家们是如何被“肉体消灭”的。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反对派作家受到的待遇稍好一些。在一次反对反共产主义的抗议活动中,有人看到当时美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著名领袖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两手各拿一瓶可乐在战斗”。尽管如此,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e McCarthy)的政治迫害下,法斯特的书还是被烧毁,并从图书馆中移除。法斯特在密尔角(Mill Point)被捕入狱,在那里他构思了自己的小说《斯巴达克斯》,后来该小说还成为了畅销书并被改编成了同名好莱坞电影。
同苏联一样,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也充满了虚伪和阴谋。美国战前宣称的捍卫民族自决的愿望,最终输给了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渴望和寻找资源新产地的强大推动力。比如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朗,美国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就曾联合支持政变推翻了当地的民选领导人。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乏相似的例子,比如美国曾支持南越、古巴(格雷厄姆·格林曾就南越和古巴的动乱创作了《沉默的美国人》和《哈瓦那特派员》)、南美和中美洲的右翼独裁政权,而其中数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Affair,是指美国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后而造成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译注)最为虚伪。
冷战是个很大的命题。怀特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冷战是一场真正全球性的冲突”,虽然他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全面,但足以令人印象深刻:简洁、高效的文章和特别的细节(比如胡志明曾在排队致敬列宁遗体的时候被冻伤)。不过即便如此,他的研究并不十分严谨。虽然怀特对尼加拉瓜很感兴趣,但却把目光移向了更南方的智利,他只用半段文字就概括了美国中情局秘密推翻支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许多拉丁美洲杰出的作家也深受冷战的影响,但怀特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诸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等拉美作家的成就。同样,他也没有关注东德的作家,而当柏林墙被推翻,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等东德作家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关紧要。而更进一步讲,怀特的书中也缺乏来自不同阵营深思熟虑的声音——比如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这种似乎跨越了分歧的诗人;又或者像小说家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e Cela)这样获胜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者一方的代表,塞拉身为佛朗哥手下的审查官,还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许是冷战的命题真的太大了。
不过,《冷战勇士》一书选择的研究领域依然令人着迷,并让人有些怀念那个文学生死攸关的时代。怀特写道:“很难想象一本像《日瓦戈医生》或《古拉格群岛》这样小说的出版,甚至会引发地缘政治危机。”
至于冷战的未来,捷克前总统、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曾预言了两种可能性:冷战结束时, “独立的社会生活”的一方将会获胜,而社会将会不断发展,直到巨变发生的那天到来。又或者,我们注定要面对的是发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事情——“某种可怕的、奥威尔式的、一个完全被操控世界的设想。”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