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用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帮助美国掌握了苏联军事设施的发展状况,导致美苏之间的军事较量天平偏向了美国这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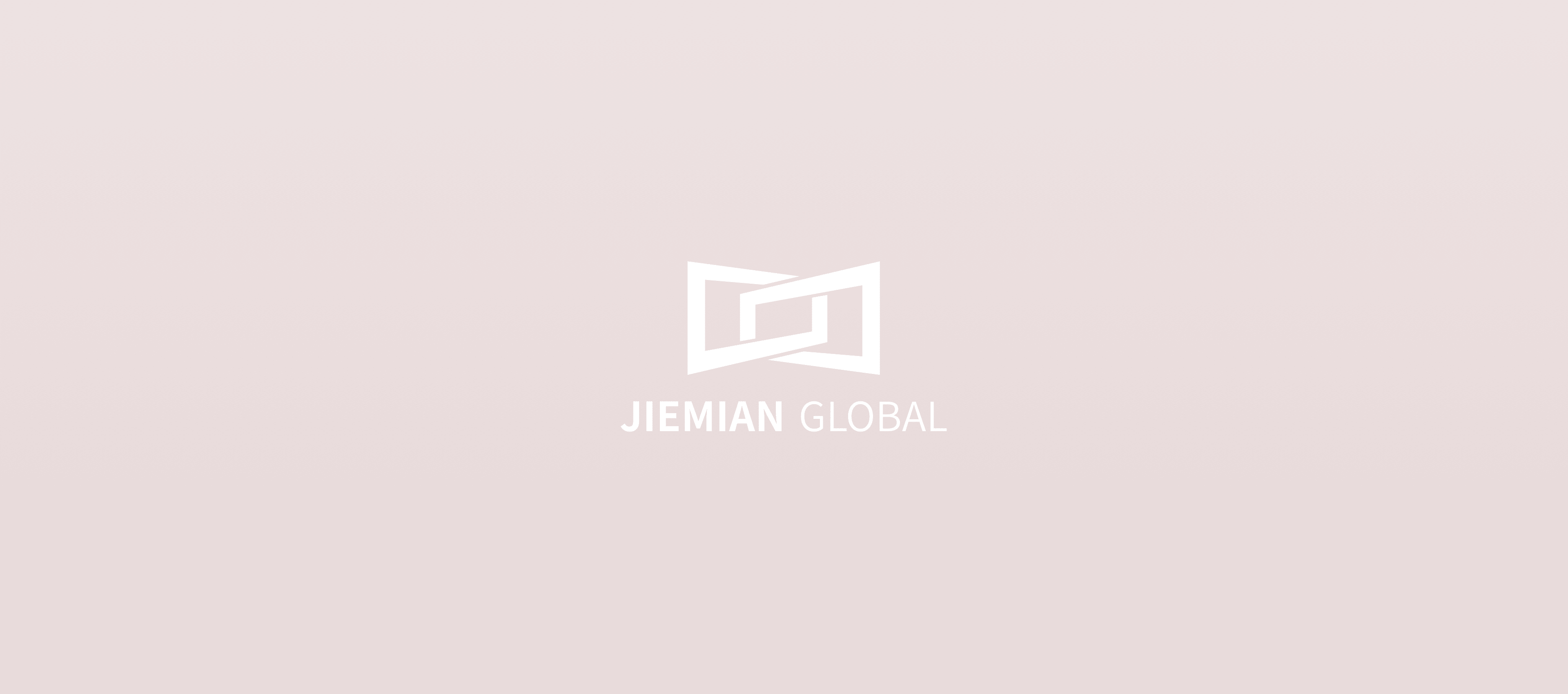
来源:网络
在现代史中,美国最重要的一次情报收集行动发生在冷战最白热化阶段的莫斯科。
从1979年到1985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了“邪恶帝国”演讲、1983年美苏空战、苏联3名总书记相继辞世、大韩航空007号客机被击落、苏联入侵阿富汗。在这种种事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深潜在一所重要的苏联军用实验室的间谍那里不断获取高价值的情报。
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Tolkachev)是苏联国防机构下属的雷达开发实验室工程师。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在莫斯科与中央情报局官员会面21次,并向美方传递同苏联研发的下一代雷达系统相关的重要信息和电路原理图。为了赢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托尔卡切夫煞费苦心:他花了2年时间试图联系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和外交人员,有意或无意地接近挂着美国大使馆车牌的车辆。
在中央情报局终于对托尔卡切夫委以重任后,他带来的信息彻底颠覆了美国对苏联雷达探测能力的了解,这在美军接下来十年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前,美国情报部门并不知道苏联战斗机具备能够侦查飞行在战斗机下方的敌军目标的能力。多亏了托尔卡切夫,美军得以重新设计战斗机和可携带核弹头巡航导弹,在苏军最新研发的雷达系统中找到漏洞加以利用。
苏联对美国知晓苏方军事科技动态一事一无所知。托尔卡切夫将美苏之间的军事较量天平偏向了美国这一方。他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冷战末期苏联造飞机未能在战斗中击落一架美军轰炸机。

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E·霍夫曼(David E. Hoffman)的新书《值10亿美金的间谍》(The Billion Dollar Spy)是关于托尔卡切夫的间谍行动的最权威记述。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一窥现实生活中的间谍行动如何进行、了解情报官员与线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见识中央情报局探员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交换情报。
这本书也记录了间谍行动的失败:在1985年,一名名叫爱德华·李·霍华德(Edward Lee Howard)的中央情报局训练生因多次测谎失败被开除。心生不满的他向苏联投诚,将本应保持联系照应的托尔卡切夫交给了克格勃。
Business Insider近日采访了霍夫曼。他于2010年凭借《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荣获非小说类别普利策奖。这本书讲述了冷战最后10年的美苏军备竞赛。
霍夫曼谈到了托尔卡切夫这个例子中值得学习的地方。成功的间谍行动就像“探月”,霍夫曼说,只有当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可变因素被一丝不苟地组织好后才可能成功。
霍夫曼称,他的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留意了这样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
“你可能已经读过很多关于间谍行动的书,但你极少有机会了解一起真实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霍夫曼说,“这是我的书所具备的。”为了撰写此书,霍夫曼翻阅了中央情报局和托尔卡切夫来往的900余封电报。
这些档案资料与霍夫曼为撰写此书进行的几十个访谈让他获得了关于真实间谍行动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洞见:“和托尔卡切夫接触的探员们追求完美,但与此同时他们做的很多事可能或已经犯下错误。这两点都让我感到惊讶。”
以下是采访片段:
你用这本书记录了中央情报局的胜利:他们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将线人安插在莫斯科,获得大量情报。但这也是一个关于组织性失败的故事:这样一起成功的间谍行动随着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的叛变而瓦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是否向我们揭示了情报收集的本质以及美国情报部门面临的挑战?
首先,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启示是,为了获取情报人力资源是不可替代的。这个观点在当下仍然有效。
在当下这个时代,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技术冲昏头脑了。从窃取电邮信息到卫星监测,总有新技术能帮助我们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报。
但写这本书时我意识到有一个类型的间谍行动是无法被取代的:看着人的眼睛,找到卫星无法捕捉到的事实,搞清楚在技术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卫星无法读取人类的思想。它们甚至不能洞穿档案柜。
即使在网络时代,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有个特别的间谍去做别人无法做到的事:进行实地考察,在必要时插入USB驱动器下载机密档案,了解没有记录在案的信息……
托尔卡切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事迹告诉我们有时候获得重要情报除了“深入虎穴”没有其他办法。

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人们把它称为制度性功能失常,但我认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反间谍行动……
情报活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你还需要对敌方的渗入有所防范。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攻击力量和防御力量都在持续不断地活动,反间谍行动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案例中,反情报活动是失败的。
我认为他们对待霍华德的方式可以称作制度性功能失常。与其说那是反间谍行动的问题不如说那是能力不足的问题:他们炒掉了一个雇员,和他失去联系,而他急于复仇。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或者说整体上看——中央情报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反间谍行动不甚上心。从奥德里奇·艾米斯(Aldrich Ames,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31年,于1994年2月24日以间谍罪被捕——译者注)、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前FBI反间谍行动探员,被指控向苏联传送机密资料——译者注)到1985年到1986年期间的中央情报局苏联部门的人员损失,都是反间谍行动的失败案例。
中央情报局的确有严重的弱点。在本书的结尾,托尔卡切夫被一名心怀不满的、一心想复仇的前中央情报局训练生出卖。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反间谍措施,在那之后中央情报局还有许多其他的损失。
这起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探员们在间隔数月的诸多短暂会面中掌握了托尔卡切夫的心理状况。这非常有趣。在这些会面中他们试图搞清楚托尔卡切夫是怎么样的人。现在看来,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做得相当好。
为了激发探员的欲望、了解探员的思想状况,这些问题你必须试着去找到答案。这不仅仅是为了行动总部的安全,也是为了你自己。把间谍行动视作心理学的运用有时候的确是个意志上的考验,因为掌握心理有可能非常困难。
在行动早期,托尔卡切夫有那么几次透露他对苏维埃系统深深的憎恶。他说在内心他是一个政治异见者,他描述了他有多么厌倦苏联的运行方式。
他对他岳父岳母的悲惨遭遇语焉不详,但我有机会亲自前往莫斯科做调查。我发现他妻子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她的母亲被处决,父亲在斯大林的政治清洗中被关押多年。托尔卡切夫为此非常痛恨苏联。
在他成年的那段时间里刚好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及政治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成为政治异见者的时期。
所有的这些过往经历都隐藏在他那双冷漠的眼睛底下等待着喷薄而出。但这并不是说他拿过来一本书,上面写着我是一名政治异见者,这是我的申诉。实际上,他提交了一些他的秘密计划并说道,我是一名政治异见者,我想要摧毁苏联。
这场持续不断试图读懂一个人的心理战是间谍行动最不可预计、最困难的部分。拿这个案例来说,我不是很确定它是否是成功的。
间谍行动指挥官们的确意识到托尔卡切夫意志坚定。他表达过自己惊人的决心,从他连续两年通过敲打美国大使馆专车的门窗来引起注意中我们就能看出来。
当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时,他提供了了他自己设计的行动方案,其复杂程度甚至需要数年多步骤的筹划。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决心的人。但他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指挥官们并不总是清楚。
我们如何把托尔卡切夫的故事放到冷战末期的军备竞赛中考量?
苏联总是能引起有趣的讨论。他们有大把的资源,国土面积辽阔,政治体系庞大,军用工业是国家机器的大头。他们总是制造许多硬件。
事实上,苏联有许多防空战斗机,他们的防空军事基地遍布边境。对我们美国来说防空不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对苏联来说,敌人就在家门口,就在欧洲。他们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境线。从防御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知道苏联所有的军事部署,但也有证据显示苏联的军事训练薄弱、操纵军事设施和武器的人员资历不够、飞行员受到地面控制员的严密指挥没有太多自主权。
在当时,关于苏联是否有向下探测打击雷达的情报真假难辨。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认为没有。托尔卡切夫帮助美国认证了这个问题。
在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弄清楚了他们有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托尔卡切夫让我们了解到了10年内苏联的发展方向。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假设你是美国空军的一员,你在考虑如何对付苏联的防空措施,能够得到对方10年内的研究发展状况的一丁点资料都是无比珍贵的。
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多年以来一直为高度机密的场景还原。你凭借电报研究和访谈做到了这点。在书写美国国家安全的暗黑地带时,你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关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了解很多,但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叙述中有许多部分如同缺失的拼图块一般。如果你是那种循着一个线索追踪历史真相的人,你会发现很多部分都遗失了——尽管是历史中微小的细节,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细节。
在这个故事中,我也需要去填补许多历史空白。我有足够多的资料来讲好这个故事,但至始至终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了解到了全部的真相。
我依然认为托尔卡切夫带来的情报中有很大一部分如今仍然有用,仍然属于国家机密。虽然这起间谍行动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其中的一些情报仍然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