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克伦曼指责称,耶鲁大学兴起的“平等主义浪潮”压制了学校培养具有“优秀品质”的未来领袖的使命。

安东尼·克伦曼 插画:Ben Kirchner
安东尼·克伦曼(Anthony Kronman)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大学度过,他曾担任过法学院院长,目前执教于“巨作”(Great Books)人文项目。如今,打量一番挚爱的校园,他注意到自己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有害的变化。人类的伟大和超凡成就一度受到敬重,但如今他却看到追求平等的欲望正在压抑学校的根本使命。克伦曼相信,这一使命有赖于对贵族制(aristocracy)的推崇,该词的原本含义就是“由优秀者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克伦曼似乎认为耶鲁的使命一般地看也是高等教育的使命,它旨在选拔出有能力对诸如人生的意义这类永久性的问题展开沉思的优秀个体。这些人类的榜样属于“民主之海里的卓越群岛”及居于其上的“对话共同体”。
如今,他又在新书《对美国卓越的攻击》(The Assault on American Excellence)里提出,这些优美的灵魂正蒙受“在美国校园里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的平等主义浪潮”的威胁。
与许多赞同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1987年的畅销之作《美国精神的封闭》基本观点的人类似,克伦曼也希望让读者相信他对自己所偏爱的、突出选拔性的大学的担忧,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其实也有决定性的意义。追求平等的欲望正在毁掉他的耶鲁大学,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对常春藤联盟的威胁,而是“对美国卓越的攻击”,整个国家都在危急中!如布鲁姆在学术界的见闻所表明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学校园充满了各种偏见,让严肃的学习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他抱怨称,学生们从小学以来就被灌输了一种偏见,即宽容是最大的美德,每个人都应该获准坚持他自己的真理。此假设导向一种追求平等的教条: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些信念是真的,我们就应该一概尊重。
众所周知,布卢姆曾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对平等盲信盲从,拒绝判断各种观念的真假,并且不许别人以相应的严肃态度追问诸如“人应当如何生活”或“什么是好的生活”这类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周围的学生自认为心胸开阔, 但这是一种鄙俗的“冷漠型开放(openness of indifference)”。过去三十年来,他的批评被不少学术评论者反复提起,以攻击左派教授(“享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遵从主流的本科生(“完美的绵羊”)或者受到过度保护的学生(“娇生惯养”的心态)来为自己的论著吸引愿意买单的广泛客源。
回顾自己在耶鲁的40年经历,克伦曼如今也加入了这群心怀不满的学者的行列,他们发现学生已经危险地与过往的优秀青年拉开了差距。克伦曼告诉读者,在自己也积极参加学运的那些年里,抗议固然也很激烈,但他们“承认政治和知识探究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如今的本科生不尊重这个区分,也不承认精神生活的较高价值。他屡屡援引一些同样认为平等威胁到了(他所觉得的)优秀品质的名人名言(如托克维尔和H·L·门肯),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克伦曼坚信,自己挚爱的校园正受到以宽容为掩饰的政治正确的宰制,真诚的讨论或积极的争辩正在被“平等派”破坏,他们更关心依旧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细枝末节,而非“巨作”所探究的人生意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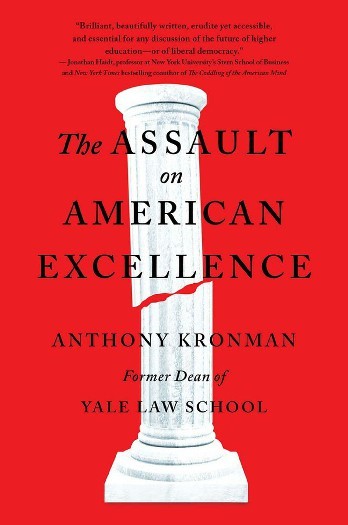
在论述“卓越”与“言论”的章节里,克伦曼肯定了与乐于探究如何更好、更充实地生活的学生进行开放讨论的价值。尽管他承认只靠几场大学讲座就让学生变得更有美德属于奇谈怪论,但他还是相信“两者之间总归有促进作用”。他指出,对话有其自身的伦理要求,它鼓励学生变得善于反思自己、远离流俗之见以及对对话所营造的“道德上的模糊性”保持一种开放态度。但克伦曼笔锋一转,认为这种教育有助于让学生成为自然贵族制中的一员,发展出“优越的品性”,进而令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机会被拔擢到领导岗位上,以利于国家的存续”。
克伦曼完全没有说明这些更优秀的人具体会怎么统治,但他确实认为这些人活得更像人也更本真(more human and more real)。他没有专门就什么是真正的人给出论证,甚至也没有就什么是优越的品质给出足够可靠的描述。他只是挑选了一些经典言论,试图以此证明自己所偏爱的哲学对话模式确实可以让人出类拔萃。苏格拉底式的谦虚和反讽在作者对自身口味的执念面前已经消失了。
我完全同意克伦曼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学院和大学应该为有志于钻研艰深课题或希望不受市场或政治力量左右地从事艺术、心理学、经济学、生物物理学乃至于追问人生意义的人提供“卓越之岛”。可以说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服务的。只讲职业教育(vocationalism)和将学生视为消费者的做法,对这些“小岛”的威胁事实上比政治正确更大。
克伦曼描绘的校园生活景象存在一定的妄想成分,他诉诸一些早就过时的传闻来证明平等主义浪潮拒绝承认伟大成就这个概念本身,也难以说服我。在许多大学里,学生(和教员)或多或少地都渴求着各种形式的承认——学生追求分数、主修、辅修和各种奖励,教员则追求发表、引用和正面的评价。
我翻到最后一章“记忆”,希望在对于从最优秀的课堂参与者中选拔成员的贵族制的讨论里找到一些安慰,但它和书中其余部分一样,显得格局不够大。克伦曼花了50页来讨论耶鲁大学约翰·C·卡尔霍恩学院(卡尔霍恩是美国知名政治人物,因曾经支持奴隶制而多有争议——译注)的改名争端,但其水准不超过教员休息室里的闲言碎语。我确实很欣赏他的一个观点,即为了让人们了解更多的历史语境,文物还是有必要保留的,不应系统化地抹除哪怕是痛苦不堪的过往。不过,把在学院里抹除白人至上主义的名号与苏联极权主义谋杀和掩盖历史的做法相提并论,在我看来既没有体现优越的品质,也无从体现可靠的判断。
我们生活在一个要求彻底平等的时代。机遇被有钱有势的人们把持着,传统的社会上升通道尤其是高等教育,似乎愈发沦为了特权的再生产工具,而非促进流动性。这是真实的人类所面临的真实问题,然而你在《对美国卓越的攻击》里却找不到相关的讨论。
本文作者Michael S. Roth系卫斯理大学校长。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