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法国女作家不只能聊女性写作和性别平等,更成功地“自导自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当代愚蠢大辩论。

法国女作家白兰达·卡诺纳与新近出版的随笔集《智者的愚蠢》中文版
采写 | 黄月
针对全球出版界的性别不平等现状,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今年3月8日妇女节当天推出了一篇对四个国家四位作家的同题访谈,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女性作家不仅面对着一个更不友好的出版、评论与评奖环境,甚至也面对着一个更复杂、更严苛的读者环境——一些男性读者会只因作家是女性而选择不阅读其作品。
在昨日上海思南书局的一场以“文字来源处的爱与欲”为主题的对谈活动上,法国女作家白兰达·卡诺纳(Belinda Cannone)也提到,虽然在今天的法国文坛,约六成的写作者是女性,但重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奖名单上仍大都是男作家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需要成为女性主义者,女性作家的作品和价值仍需要被认识和发掘,”白兰达说。
与白兰达对谈的是法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袁筱一,她也是出版于2015年的白兰达随笔集《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的中文译者。她评价白兰达是一个“多面写手”,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多种体裁。在翻译的过程中,袁筱一与这位法国当代作家产生了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原因之一在于白兰达惯常以非学术的随笔方式创作文学评论,这也是袁筱一个人很喜欢的一种切入文学的方式,从她今年再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字传奇》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另外,袁筱一认为,“虽然(白兰达的)评论写作十分细腻而感性,但其与理性并不矛盾,”人们倾向于将女性视为对于情感、爱欲更敏感的动物,然而她指出,一方面爱与欲望本身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写作主题,而且写作——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在文学的语境下将感性与理性对立起来。

白兰达也认同这一观点,她认为没有哪个性别更偏向理性或更偏向感性一说,这两者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是同时存在且同样重要的。虽然常常面临着性别的指认和强调,但她在写作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女作家的身份,“我首先是一个人,性别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女性作家这个身份。我塑造的人物也有很多是男性,我并不觉得描述一个男性和描述一个女性或者一个孩子、一个中国人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都需要作家去花费大量心思去构思和描述。问题不在于性别的身份,而在于人。”
然而在法语词汇中,性别的身份被不间断地以缺失的形式对女性加以提醒。现场一位读者指出,法语中的“作家”“诗人”这类词汇只有阳性形式,而没有与女性对应的阴性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作家该如何定位与讲述自己呢?白兰达回应说,在法国这个问题也正在被一再讨论,“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从语言上讲,这个规则进一步确立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他们提议在每一个词后面都加上阴性的词尾,每次说到一个词都呈现出阳性和阴性的形式。”但她并不认同这一做法,“如果真想改造语言,我建议发明一个新的中性的词,而不是把原有的词进行阴性化。”
除了关注和批评文学圈与出版界对两性的区别对待,白兰达也试图在女性作家自己身上找原因,来解释占多数的女性写作者的边缘地位。她与活动现场的听众们分享了一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轶事,与她的第三本随笔集、今年8月最新译介出版的《智者的愚蠢》有关。这本书最早于2007年在法国出版,此后有一位男性作家多次与她就这本书展开交流,并表示自己从中获益匪浅。两年前,这位男作家出版了一部作品名为《愚蠢的天才》,其中一个章节写的正是“智者的愚蠢”——他在书中没有提到白兰达的名字,甚至在参考书目里也只字未提。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相遇时,他为“忘记写上她的名字”而向白兰达致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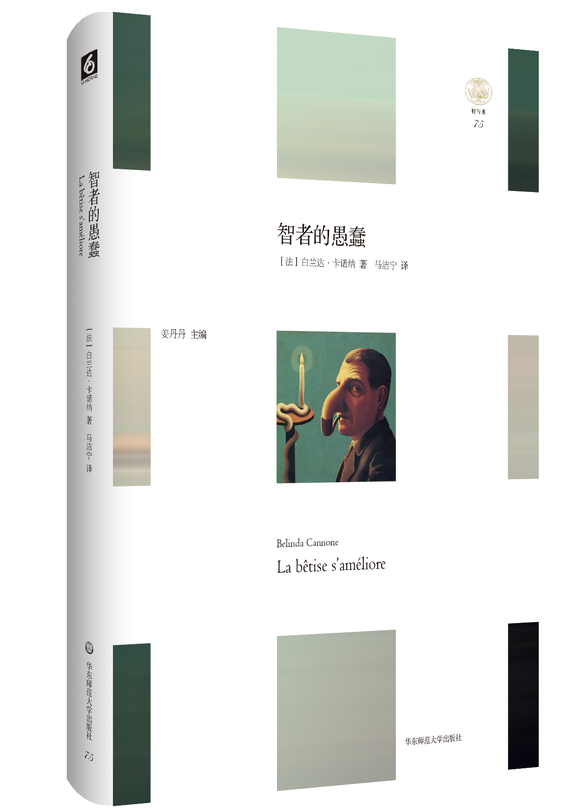
之后白兰达去做了一番查证考据,发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书写过“愚蠢”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需要很多思考、讨论或者按照通常的说法需要理性进行分析,没有女性作家敢于触碰这样的主题,”她说,“因此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思考女性作家为什么会面对今天这样的境遇:一方面当然是社会还不能完全承认女性作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许女性作家自己也缺乏一点儿狂野精神或者大胆精神,要敢于冒险,敢于尝试传统意义上不适合女性的主题。”
联系到日前公布的中国重要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十部入围作品,袁筱一说,中国现当代写作者中女性也占据了约70%,但这份名单上的女性作者相当之少(实际上只有一位),“确实,女性在写作方面话题可能还是受到一定局限,或者并没有勇敢地踏入在传统上看起来是男性作家领域的话题。”
除了白兰达探讨的愚蠢主题,战争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卫报》刊发的《战争中的女性:为何我们难以想象女战士?》一文中,作者、英国小说家莎拉·豪(Sarah Hall)指出,战争劳民伤财,无论男女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虽然女兵比例很低,但历史上战争如此之多,参与其中的女性数量并不少,但是“由女作家撰写的战争小说却很罕见,仿佛是女性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涉足这片想象的领域一样”。
随笔散文也有很多种写法。白兰达·卡诺纳的《欲望之书》曾在2001年获得法兰西学士院散文奖,从《欲望之书》到后来的《智者的愚蠢》,她说自己在这第三本随笔中开始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观点,“把故事或者虚构的层面加入到随笔当中去,试图让一些人物进行对话,由此阐述我的观点,而不是像前两本那样直接陈述我白兰达的观点。”

在《智者的愚蠢》中,她虚构的主角之一是格列佛,与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版于1726年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主人公的名字相同。格列佛是叙述者“我”的朋友,一个和善而谦逊、认为自己愚蠢而实际上颇有智慧的人。这本书的主旨正是出自格列佛之口:“让我耿耿于怀的不只是当代人的愚蠢,或者1881年时的愚蠢,我告诉你,我所感兴趣的是聪明人的愚蠢。他们修养不凡,见多识广,能够自由地(姑且这么想)在任何时候,对任何话题运用他们的智力,然而他们却同时受到了教条的影响。”格列佛在看似随意的吐槽中直击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痛点,“这是一种精致的教条,可不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而是这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内部——聪明人的团体——的意见,他们统治着当代的思想。”占领舆论高地的教条,正是当代的愚蠢。
从这本尖锐而狡黠的散文集中,我们不难发现白兰达所指向和严厉批判的现代文化生活的种种虚伪甚至虚无——再聪明的人也几乎无法逃脱这种愚蠢。相信先锋主义的人其实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意图颠覆的人其实掉进了“要符合秩序,就请颠覆吧”的精神陷阱,很多讨论还未开始便已夭折,因为人们“没有论据,而只是姿态之间的交锋”。
白兰达在后记中说,她总是“想象自己扮演着身为文学沙龙女主人的职责”,于是她一边借着作者的身份组织了辩论,一边以“我”的视角参与了这场辩论。在几乎发明了知识分子这一形象的法国,她看到媒体知识分子正把话语权握在手中,在以用媒体传播文化的方式给自己“打广告”的同时,又反过来汲汲于得到媒体的认同。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大问题,”白兰达写道,所谓知识分子奉行着随波逐流主义,不断重复着“大师”“反叛”“先锋”的陈词滥调,而普通人抱定互联网信息平等的幻觉,坚信“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因特网,能够让人拥有对真理的总体认识”……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做一个不随波逐流的智者?白兰达在《智者的愚蠢》中为我们提供了彼此交错、纠缠或冲突的思路,而智慧的道路究竟通向何方,我们只能独自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