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才开始想象人类的灭绝。这是否标志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经步入了成熟期?

1833年11月12日至13日夜里,北美上空出现狮子座流星雨 图片来源:Wikimedia
1844年,沙俄王子弗拉基米尔·奥多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写下了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未来的人类将会面临人口过剩和资源枯竭的情况,他们迎来了“最后的弥赛亚”,这位救世主命令疲惫不堪的人类将地球整个毁灭,以此来完成人类的灭绝。早一些时候,1836年,意大利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宣称,如果人类灭绝,“地球”是不会“觉得少了什么的”。再往前追溯三十多年,萨德侯爵也曾说过,“没有什么比人类的彻底灭绝更让人称心如意”。早在1756年,法国极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布封伯爵也设想过,“如果人类彻底灭绝了”就会有另一种生命形式来继承我们的地位,攀上金字塔的顶端。
人类灭绝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至19世纪。尽管相关研究不足,但这一观念的历史发展却相当重要,因为它教会了我们,身为人类首先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召唤又对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今天,人们对存在性风险的关注日益高涨,灭绝的想法从启蒙时期就开始提出,至今仍处于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状态。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人类是如何开始关心起自己的灭绝,才能更明确地知道,我们为什么必须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此投入前所未有的精力,因为下个世纪将会是迄今为止灭绝风险最大的一个世纪。
事实上,尽管莱奥帕尔迪和奥多夫斯基给出的预言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但这个故事却一点也不悲观。18世纪,第一次有人提到了人类灭绝的风险,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第一个规避风险的预测也出现了。1824年,拜伦勋爵提出建立行星弹道防御系统来避免彗星撞击地球;1805年,法国作家让-巴普提斯特·库辛·德·格兰维尔(Jean-Baptiste Cousin de Grainville)设想建造巨型地质工程“机器”,生物圈将会崩塌,营养含量也越来越少,人类需要这样的机器来夷平山脉、移动海洋,从而榨取出仅剩的营养;早在18世纪20年代,法国外交官伯努瓦·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就预测过,为了缓解太阳膨胀带来的高热干旱、延缓“人类的彻底灭绝”,人类将会对地球进行全规模的改造和灌溉。
发现自身物种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就是人类在逐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只有当一个人了解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并且想要去规避风险时,他才算得上对自己负责。哲学家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类对自我责任的承担,因此人类灭绝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启蒙史。它所关注的,是现代人类不再像古人那样笃信宇宙本身蕴含着固有价值,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使我们继续捍卫和守护人的价值,它也无法变成自然实在。
不过,如果人类灭绝在18世纪才被提出,那么在此之前是否存在这个概念呢?长久以来,宗教信仰中所描述的末日场景又该作何解释?首先,宗教启示录中的预言向我们揭示的是时间的终极意义,而人类灭绝则是在时间范畴内预测了意义的终结,且不可逆转。启示录强调的是终结的意义,灭绝预测的则是意义的终结。二者的差别在质不在量,因此它们并不来自同一个起源。
那么,为什么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就不去谈论和猜测人类灭绝和存在性灾难的话题呢?

20世纪30年代,美国观念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注意到一种假设,他称之为“充实性原则”,从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茨的西方哲学都对其有所体现。简单来说,这一原则认为,所有合理的可能性最终都必将实现。即使表述略有不同,但某物的存在或是不存在都必定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没有事物的存在不需要理由,没有事物的存在没有理由。因此,像物种灭绝这样不具备充足理由的事情当然是个禁区(这是自然在实现可能性的过程中留下的无法解释的缺口)。这种观念让任何物种(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毁灭都变得毫无意义,且限于一时,因为在该原则下,物种即使在灭绝后也必然终将再次回归。任何物种即使在某地灭绝了,也总有一天会重新出现。受这一原则的影响,从古代到启蒙时代的人们都难以认识到物种灭绝的现象。
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自信地宣称“万物皆非唯一”,因此,万物都不会真正地消亡。几个世纪后的1686年,法国科学家伯纳德·勒·博弈尔·德·丰特奈尔发表了一致的见解,没有任何物种“能够完全消亡”,因为即使我们的星球被摧毁,亦或是我们的太阳衰败了,完全相同的这些物种最终还是会在别的地方繁衍出一个新世界。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也坚定地认为,在浩瀚的宇宙旋涡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地消逝。据报道称,狄德罗被问到过现代智人是否会灭绝,他的回答是“会”,但随后又立即解释说,再经过下一个恒星活动周期,经过“数亿年不知道是什么的过程”,又会重新进化出这种“被称为人类的两足动物”。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名言“而如今,泡沫破灭了,世界也破灭了”常被解读为造物的喜悦与慷慨,很少有人认为这句话是恶的表达。
后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深信充实性原则,1799年,他不顾卷帙浩繁的解剖学证据,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当时新出土的猛犸象和巨爪地懒标本,其活体物种仍然存在,并且数量众多,遍布整个美洲的未开发地区。后来,科学家们已经无法再否认某些生物已经灭绝的事实,但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还是摆脱不了老一套的观念,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还声称禽龙、鱼龙和翼手龙会在不久的将来重返地球,并将重新占领地球。他认为,整个生物属的消失只是一段“沉默的间隙”。根据类似的推测,毛里求斯渡渡鸟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但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灭绝。自更新世以来,人类一直在大规模地毁灭其他物种,但我们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对“充实性原则”的信仰阻碍了我们去理解物种灭绝背后的利害关系,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灭绝现象不值得观察,更不用说预测或减缓了。毕竟,消失的人类或动物只是陷入了沉默的间隙。
****
还有一个问题也阻碍了我们对人类灭绝的思考,那就是笃信宇宙本身蕴含着价值和正义。这种假设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根源,并且与充实性原则密切相关。相信“所有合理的可能性最终都必将实现”就等于相信“现实是尽可能合理的”,简单地说,存在即合理。因此,毁灭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
这一点在莱布尼茨的观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一世界必须是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世界”,但这种主张早在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中就已经出现过了:现实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现实本质上是理性的。

“存在”被认为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理性本身却不能停止“存在”,因此人类理性的终结根本无关痛痒。早在古希腊时期,埃斯库罗斯、赫西俄德和柏拉图就开始讲述宙斯“毁灭凡人种族”的计划,但这样的神话情节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灭绝场景”或“存在性危机”,因为它并不是人类价值的终结。即使宙斯一次又一次地给予人类重创,类似的价值还是会在造物主那里无限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认定宇宙本身具有先定的正义性,那么人类的所思所想带来的风险将变得微不足道。
人类是一种喜欢兜售价值的生物,只有将价值“完全置于”人类的思想之中,人类的灭绝才会变得有意义(这样也能刺激我们探究的欲望和对未来的预期)。我们必须认识到,宇宙并非天生就是正义和道德的摇篮。我们必须将“价值”和“事实”分开,才能真正开始意识到价值的终结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动力真正想要开始预测未来,保证人类正义不受外界自然环境的影响。正是这样一种动力,跨过了现代,将我们的担忧拉拽向了更加深远的未来,并将越拉越远。
理解这一概念的过程开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但是到18世纪时才达到顶峰。这是由于启蒙运动时期,地质学、人口学、概率论等新兴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发展与巩固。
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在17世纪后半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地质学就起源于此。两位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和埃德蒙·哈雷在地球的理论模型上加入了由自然引起的变迁和变化,从而提出了第一个公认的“地史”猜想。他们都明确对先前的物种早已灭绝表示过认同。在此后的整个18世纪,人们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化石证据,直到179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史前动物已经不可逆转地消失了(他对猛犸象臼齿进行了比较解剖学分析)。
人们给居维叶的地球历史理论起了个恰到好处的名字,叫做“灾变论”,因为这一理论依赖于各种爆炸式或地震式的灾难。从第一拨探讨人类灭绝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到灾变论的影子,这些作品全都出自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的圈子:拜伦的诗作《黑暗》(1816)描述了热量散失后的生物圈,一切都变得贫瘠昏暗;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为我们描绘出了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而人类的加入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雪莱接着又创作了《最后一个人》(1826),这是第一部描写全球范围内存在性灾难的长篇小说,但在之前的《弗兰肯斯坦》(1818)中,这种存在性的灾难就已经有所暗示。如果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为怪物制造了一个异性伴侣,那么怪物就可能利用人口统计学上的潜力进行大量繁殖,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物种,从而导致人类的灭绝。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学科背景:“政治算术”——也就是常说的人口统计学。《波斯人信札》(1721)是最早涉及人口统计学的著作之一,也是最早提到人类作为生物物种有可能消失的著作之一,由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著。他在书中写道,自古代以来,全球人口一直在减少,他在经过“尽可能精确的计算”之后,宣称“如果放任这种趋势继续下去,10个世纪以内,地球将会变成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
自那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新兴的人口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多类似的推断。人们发现数据统计可以应用到现实当中,用来预测未来的长期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人口统计学的兴起也成为了一项关键的助力因素,让人们更容易面对和接受存在性危机,因为人口统计学巩固了人类的这一自我认知,即人类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发表于17世纪80年代的著作重新定义了“物种”的概念:物种指的是与其他群体存在生殖隔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固定下来的有机体形态。因此,这种政治算术通过强调人类作为一个生殖群体的存在,向人们灌输着“分类学上的自我意识”。这一观点被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奉为圭臬,1758年,他将人属纳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范畴。也正是在这个世纪当中,我们开始称自己为“人类物种”。既然可以接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存在,那么我们就也可以接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灭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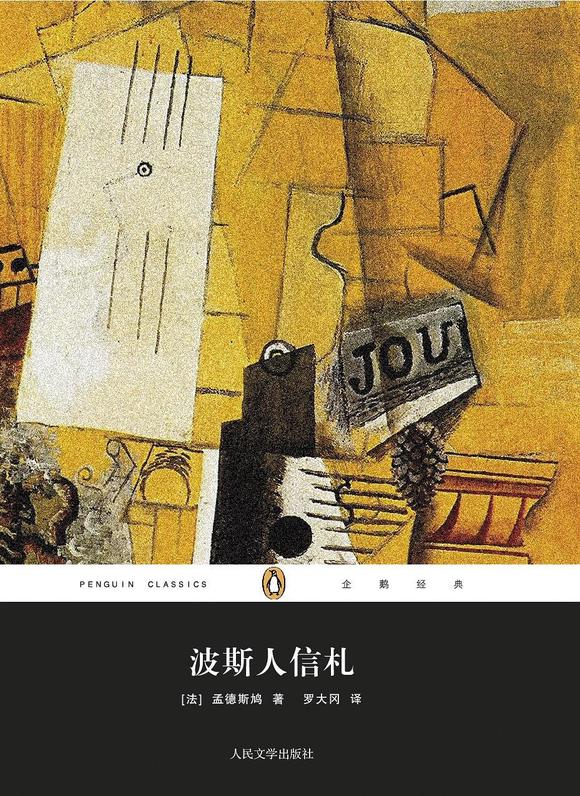
****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还提到,过多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将人类“带入濒临灭绝的境地”。他警告说,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毁灭我们,我们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关键的学科背景——概率论,这是一种严格而现代的概念,格外强调风险与不确定性。
概率论在诞生初期就被应用到了人口普查数据领域,政治算术也应运而生。从法国的帕斯卡尔到瑞士的雅各布·伯努利,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们首次开始处理概率论问题,也首次开始利用数据测量去预估未来。不久之后,概率论就开始被用来计算所谓“全球灾难性风险”的可能性。
1773年,法国天文学家杰罗姆·拉兰德首次应用了概率论来处理存在性威胁的问题,他预测地球与彗星相撞的几率为七万六千分之一。这则消息被大肆宣扬传播,在巴黎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后,法国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也声称,尽管这一概率的绝对数值很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彗星撞地球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到了1810年,德国天文学家威廉·奥尔伯斯已经将拉普拉斯预测到的“一长段连续的时间”具体到了一个精准的时间表,他计算出了每两次碰撞之间的时间间隔为2.2亿年(但是当代计算的结果显示,每隔5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足以使全人类灭绝的碰撞)。
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历史的变迁,认识到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在其中的危险状态,认识到了我们在宇宙背景中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才终于得以接受人类的灭绝。然而,如果“事实”和“价值”不能完全分开,这一切都将不再重要。只有我们完全承认了宇宙本身并不具有先天的价值,“人类灭绝”才有道德价值上的风险,才值得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对人类灭绝的探索,不仅要有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作为依据,还需要反思价值的允当性(及不稳定性)。
因此,最后一块拼图并非来自实证科学,而是来自批判哲学。它起源于18世纪80年代康德发起的哲学革命。
康德认为道德价值是自我立法的问题,是人类自身对自身的约束,它本质上依赖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此,道德价值不应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离不开主体意志的支撑与维护。如果我们不加以悉心的管理,这些道德价值就无法持久地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换句话说,“思想”完全是“思想者”的责任。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从存在的层面来看,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十分重要。正是这种伟大的启蒙思想,让我们意识到了思考的重要性。
随着康德的思想日趋成熟,他自己也越来越关注人类灭绝的前景。他曾经说过,人类世界消亡时,我们“不应该哀叹失去了整个自然”,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宇宙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的道德价值,并且宇宙中存在无数像我们一样的生物。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了人类价值的不稳定性与珍贵性。在他晚期的作品当中,人类灭绝的幽灵反复出现过多次。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未来学——康德称之为“可预测的历史”——的文章,文章指出“自然革命时代的到来将会把人类推到一边”,他对人类完美性的预测被打破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康德自己就将启蒙定义为人类对自我责任的承担:根据人类理性的判断,一个人将要承担的责任应当恰好与他需要面临的风险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预判日益严重的灭绝危机是人类承担自我责任的重要部分。只有阐明了无知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才会更加积极地去思考和推断,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将现代性具体阐述为“我们对未来的需求”的增加,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未来对我们的需求也在增加,只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还不太清楚。本文回顾了灭绝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人类通过关心灭绝问题来应对未来的召唤,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一系列预言和缓解(例如牛津的人类未来研究所,还有剑桥的生存危机研究中心)正是对过去的传承:这个想法早在启蒙时期就已经提出。这么说可能略显严肃,但正是由于我们对物种灭绝的担忧与日俱增,所以我们才更有理由对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抱有希望,也许还可以期待更遥远的未来。
本文作者Thomas Moynihan系哈佛大学博士,观念史学家。新作《脊椎灾变论》(2019)即将问世。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