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材数量充足加上唾手可得,我们对暴食的抵抗力越来越低,地球会有被吃空的一天吗?

图片来源:Barbara Alper/Getty Images
1万只沙漠鼠、1万条鱼、1.4万只绵羊、1000只羊羔、1000头肥牛以及其它许多动物被杀死、做成菜式并端上餐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亚述尼夏巴尔(Ashurnishabal,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859年)在为期10天的大宴里就是用这些来款待7万名来客的。公元1466年,约克郡大主教的就任仪式则耗费了104头公牛、2000只鹅、1000只阉鸡、1000头绵羊、400只天鹅、12只鼠海豚和海豹以及大量其它种类的鸟和哺乳动物。一则不无夸大成分的花边传闻称,治下极尽奢华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某场婚礼上因暴饮暴食而动弹不得。
没有比极端状况更能激发想象力的了——诸如酒池肉林、世纪大战、灭顶之灾以及丰功伟业之类的东西。身为杂食性(omnivorous)动物,我们对大办酒席可谓是又爱又恨,偶尔还会不知所措。
以往我们尚且从事狩猎和采集,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都如此,此时杂食的习性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日常的营养来源较为多元,这令我们免于营养不良和饥饿(我们还经常会好几天乃至好几周都不吃东西)。食物的质量和数量是难以预测的,这种偶然性源自诸如贸易路线之类的人类力量以及天气和自然周期的变动不居。从很早开始,我们就适应了短期性的忍饥挨饿,抓住一切机会积累热量和易于储存的营养——例如,每当我们找到一株浆果已然成熟的灌木丛,或是碰上有众多贝类栖息的潮水潭,我们就会大吃一顿。谁眼疾手快且善于把握觅食机会,且有将多余热量转化为脂肪的生理学途径,谁就更有可能在较长的两餐间隔当中生存下来,以及培育出健康的后代。
这些适应性的习惯在人类第一场重大革命到来之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农业革命令我们可以储存食物了。随着文明的兴起,谁粮草充足、六畜兴旺——一般是法老、国王和其他统治者——谁就能举办宴会来酬谢政治上的支持者,或将其作为一种凸显自己凌驾于大多数穷人之上的权力象征。对精英阶层而言,梦幻般的盛宴几乎成为了传说的一部分。
不巧的是,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欧洲、亚洲和文明世界里的许多其它地方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代,当某些人掌控的食物资源多于他人,食物便造就出社会分化,它是阶级的象征,是衡量地位的尺度。“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食物史家费利普·费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解释道。
第一批与食物相关的乌托邦故事有好些都诞生在中世纪欧洲,这一时期根深蒂固的不仅有宗教信仰和封建制度,还有饥荒和疫病。对生活困窘的农夫而言,幻想可以敞开肚子吃喝的仙境不失为一种常见的解脱之道。
此类理想乡有许多版本,如德国的“懒人之乡”(Schlaraffenland)、荷兰的“悠闲丰盛之乡”(Luilekkerland)以及人们更熟悉的安乐乡(Land of Cockaigne),它首次亮相于1250年的同名法国诗歌。这三个版本的共同点,是取之不尽的食物、用之不竭的闲暇,且都委婉或直接地挑战了阶级体系。
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画作与游手好闲、随意吃喝的理想乡一样具有超现实色彩。其中有挂满了食物的树或用食物建成的屋子。各种家畜不仅已经煮熟,有时还直接被插在方便刀叉上,显得栩栩如生——像是一种相对无害的不死生物。天上下起了鳗鱼和肉饼雨。河里流淌的是葡萄酒或牛奶。到处都是可供食用的动物,有些还会自己跳进食客的嘴里。家畜与家禽的养殖、屠宰、烹饪等诸多繁重工作尽皆消失不见。

阿姆斯特丹大学中世纪荷兰文学荣休教授赫尔曼·普莱(Herman Pleij)在《梦回安乐乡》(Dreaming of Cockaigne)一书里深入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恐惧,即“已然十分悲惨的境况会突然变得更糟”。为缓和焦虑,人们在每天与饥饿作斗争之余便会转向幻想的食物乌托邦,以其“夸张的幽默来创造一个美好的、颠倒了的世界”。安乐乡乃是向伊甸园的回归,是人间天堂,是自然趋于完美的状态,其中不再有痛苦、不适以及一切类型的欲望。在那个奇妙的世界里,人类在食物链上的斗争彻底结束了,我们自由了——既不用当别人的猎物也不用自己找猎物了。此外,里面的人们也不再需要为了领主的利益而背负繁重而悲惨的农活了。
安乐乡里的动物也自愿成为人类的食物,这一点与某些美洲土著故事十分相近,其中诸如鹿和兔子之类的猎物会主动向善待它们的猎人献身。对美洲土著而言,彼此尊重的相待之道可以称作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一个可持续的狩猎世界,应当同时保证动物以及以之为食的猎户都能不断繁衍后代。反过来看,安乐乡里的家养动物的自愿献身则与食客的行为举止毫无关系。在一切幻想当中,自然法则都失效了。
但有一样东西显然始终没有失效:那就是贪吃(gluttony)——无论以之为耻还是为傲——如今它依旧体现为在社交聚会、大胃王比赛上的胡吃海喝,或是在打折俱乐部里疯狂囤货。不管用什么字眼来形容这些行为,这一切都依旧能让我们回想起内在于重农主义(agrarianism)的两极化特权,以及我们曾经朝不保夕的生活。
普莱认为,假如中世纪的人们可以和我们相见,“当今的欧洲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安乐乡的梦想:快餐随时可以买到,天气控制技术、性自由、失业福利以及号称可以永保青春的整容手术也都唾手可得。”如今的商家不需要知道我们历史上有多么艰难,利用好根植于人性的享乐欲即可让消费者乖乖掏钱。事实上,这可能是让消费者买单的最简单途径了:用豪华大餐来让他们心神不宁,并且把它做得易于获取及消费。
这种过量(excess)的能力或许有助于解释人类何以经常将一些珍贵的野生动物逼到灭绝的边缘乃至于使其灭绝。这里有三个北美的物种十分典型:信鸽的数量原本数以十亿计,至1914年彻底灭绝;北美野牛原本遍布北美大陆,到了19世纪中叶其数目从3000万头锐减至不足1000头,如今只能在极少数保护区苟延残喘;而北大西洋鳕鱼的规模和数量在史上一度撑起了最为繁荣的跨国捕鱼业。
在以上所有案例中,猎人们面对千载难逢的利好,从来没有想到过——或者利令智昏——什么可持续发展。减少捕猎几乎就等于荒唐,完全抵不上政府规制当中的成本或政治上的反扑。其实,我认识一个在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工作的人,他就经常抱怨说自己的研究团队在1980年代对大西洋鳕鱼数目锐减的灰暗预测基本没有人听进去。其结果就是纽芬兰大浅滩(GrandBanks,世界最大渔场之一——译注)的鳕鱼存量彻底不保,1992年开始实行的商业捕鱼暂休期亦持续至今。

虽然几千年来还有不少生殖力不算强的鱼群在炸弹、鱼叉和渔网的轮番折腾之下趋于灭绝,但前述的三个种群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就在于其初始的数目极为庞大。加速其灭绝的,或许反而是这一令我们掉以轻心的惊人数目。要指责其它时空下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短视并不难,但不妨想象一下,站在19世纪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里,看到千百万只信鸽从头上掠过,一连好些天都遮天蔽日:此时你会收手并且怀疑每周一两车的狩猎量长期来看是不好的吗?
另一方面,近来北部鳕鱼存量的管理不善表明,不能以眼下短期的充足来否认未来世代的需求。也许没有什么研究或者道德约束可以阻止我们享用那些不请自来的东西。但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相信,滥杀的倾向乃是“人类本性使然”,而不是历史上的某段时间或某个地点所特有的(把所有责任都一股脑地推给欧洲人的竭泽而渔,毕竟是一种很诱人的观点)。“过度榨取(overexploitation)是狩猎过程中的常见祸害,因为狩猎文化必然是高度竞争性的:没有在对抗中率先收手、坐以待毙这一说。”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解释道。
数量充足加上唾手可得,还有别的一些表现。在北美和欧洲,宣传鸡肉、牛肉或猪肉大餐的广告里通常会有一只母鸡或公鸡、阉过的牛或者猪,热情地招徕着那些业已垂涎欲滴的食客们。这可能是一种描绘动物心甘情愿被吃掉的黑色幽默。英国游记作家彼得·梅尔(Peter Mayle)在《愿上帝保佑法兰西厨子》一书里观察到,其目的是尽可能凸显娱乐性和诱惑性:
法国人一般不会对食物动情,但他们确实倾向于让那些即将被自己吃掉的东西显得很快乐……如此,不管是在肉铺还是在超市里,不管是在海报还是在包装纸上,你都能看到……鸡、牛、猪、兔子和鱼都有着一张笑脸。它们看上去都为自己即将为一餐作出重要贡献而无比兴奋。
英国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在《宇宙尽头的餐馆》里就以一个幽默搞笑的场景凸显了这种荒谬:亚瑟·登特和友人正在点菜,一只动物来到桌前,那是一头“又肥又壮的牛,足足有一般牛的四倍大,还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牛对他们说道:
“晚上好,”它弯下身子,一屁股坐下来,“本日的主菜就是我。您对我身体上的哪一部分有兴趣?”
亚瑟一开始有些不解,接着勃然大怒,自己居然可以自由选择吃掉一只活物的任意部分。亚瑟的外星人朋友对他的反应颇为不解,对此亚瑟解释说“这太没良心了”,接着就改点了沙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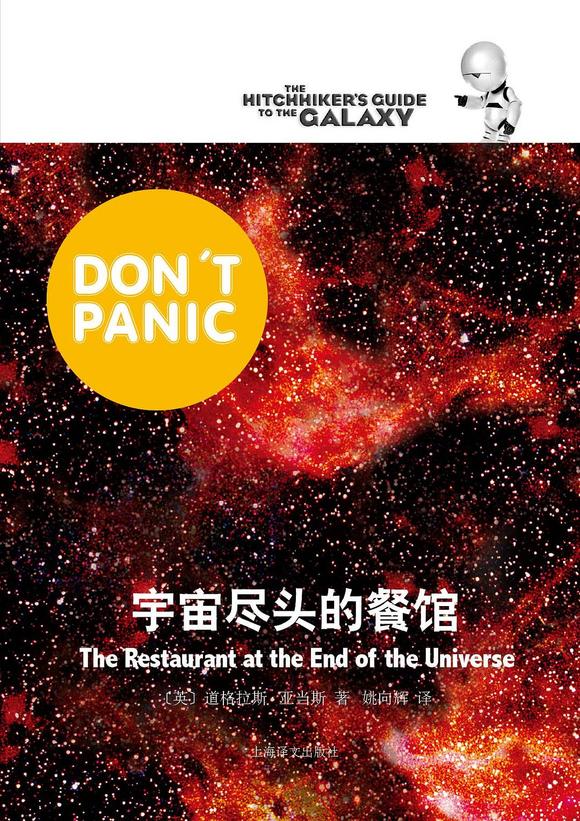
人们想要轻而易举地开杀戒,但又觉得这是错误的。与其它许多人类特质类似,人类的集体意识里有许多这样的成双成对的矛盾面。我们一面对死亡有恶心感,一面又认为任何非素食餐饮都会有一条生命的代价,只不过这条生命可能在解剖学和情感变化上跟我们不甚相似。我们明白代价,但饕餮——这部分源自我们的生物学特征——依旧占据主导。此特征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文化建基于其上也毫不奇怪,它构成了类似于“主题与变奏”的排列组合,但这当中似乎又有相当数量的组合方式确然为人类所特有。
英国科学作家柯林·塔基(Colin Tudge)的《史前时间》(The Time Before History)一书提出,人类与非人类杂食者的饮食习惯都倾向于浪费——短期与长期都是如此:
一个非专食性的(non-specialist)的追猎者——也就是可以食用多种动物或是兼食荤素——并不依赖于猎取某一特定的种群。所偏爱的猎物数量若有减少,它只需换一种吃法即可。但假如它真的特别喜欢吃某一种猎物,那该猎物即便濒临灭绝也不会让它收手……总的来看,虽然有“追猎者与猎物必然同生死共命运“这一生态法则,但诸如人类这样的动物——在饮食上善于随机应变,偏爱的猎物变少后只需略作调整——是有能力打破这一法则的。
来自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学院、专门研究食物链的生态学家珍妮弗·邓妮(Jennifer Dunne)指出,猎物转换(prey-switching)是可以自行发生的——其方式是赋予稀缺商品以更高的价值,这部分是因为它的稀缺本身。蓝鳍金枪鱼在国际寿司市场上有非常高的需求量,因此其商业捕捞也相当繁荣。随着它的日渐稀少,其价值也水涨船高。“于是就形成了这种荒唐的反生态怪圈,”邓妮解释道,“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某种生物一旦变得稀少且难以寻觅,它的生态价值也会随之降低。追猎者改变狩猎对象的原因在于:为得到那种猎物,他们所耗费的能量是其难以承担的,或者狩猎过程太过危险。然而,在奢侈品市场里,人一下子就变得竭泽而渔了,因为这样能赚取更多的钱。”
就这一觅食冲动而言,我们的生物学特征或许给予了我们相应的口味和生理特质,但文化则将其化为法则并加以正当化,且经常会夸大其重要性,这造成了一种古怪的、自我开脱的(exculpatory)反馈循环。要打破这一怪圈,就需要自上而下地实施极端严格的管控,单纯的规制和不痛不痒的罚款只会让市场由地上转入地下,以及呈现出类似于象牙和穿山甲贸易的规模。再一次地,一系列源自想象的产物——无论是盛宴的宏大排场、对理想乡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的幻想,还是一条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枪鱼——抹杀了动物的真实状况。
如今,可以敞开吃喝的自助餐以及无处不在的快餐,可以说就是现实生活里的“安乐乡”:便捷、廉价、简单。诸如一只背上插着刀的烤猪健步如飞之类的形象,乃是在回避杀戮,且借此掩盖了围绕杀戮而产生的诸多紧张。对数量的强调——且不论获取渠道——影响了对我们与现今或曾经生存着的食物的关系。被丰盛冲昏头脑(外加一定的幻想成份)后,我们就不去直面那些不愉快的念头了,特别是动物在狩猎(或圈养)及屠宰期间所经历的疼痛和苦难。金枪鱼的锐减这个例子表明,哪怕我们明知有稀缺性,也难以控制自己攫取地位崇高的梦中美食的冲动。其象征性价值(及其味觉享受)几乎完全抹杀了它作为有生命的、有感觉的存在者的身份,更不要说它在生态系统里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了。
这就是我们的面目:贪得无厌、掠夺成性、好吃懒做且鼠目寸光。要改变这一现状,知识界必须从哲学和科学里提炼出精巧的论证来约束我们千年以来形成的习惯。这是十分困难的。饥荒的记忆深入我们的骨髓;肉类当中的脂肪和蛋白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饥饿的最佳保障,因此我们的生物性告诉我们:放开了吃!而文化性则补充道:肉必须是既容易搜寻又容易获取的。这样,丰盛之地同时也就是懒惰之地。最后,懒惰还令我们对表面上唾手可得的餐食背后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真相矢口否认。
本文作者Louise Fabiani系作家、诗人和独立学者,现居蒙特利尔,曾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稿,主要关注科学与文化。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