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遥远而顽固的形象仍为战争、历史与异域幻想题材作品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空间,但真实的阿富汗历史是否被遮蔽了呢?

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吕利
在近二百年来的文学与流行文化史上,阿富汗从来不是一个缺乏故事的国度。这里是柯南道尔笔下华生来到贝克街之前的噩梦,是鲁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疯狂蒙昧的卡菲尔斯坦,还有《第一滴血3》和《查理·威尔逊的战争》,即便《西姆拉宣言》《甘达马克条约》乃至马苏德的北方联盟已经从大众的记忆中淡去(正如一切追求短平快的国际新闻那样),阿富汗遥远而顽固的形象仍为战争、历史与异域幻想题材作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空间。
随着阿富汗在现实中的残酷与混乱借助摄像机和电视信号史无前例地投射到全世界的视线之下,传统的战争史叙事逐渐失去了戏剧张力:在无限制、非对称的低烈度治安战面前,写作者以阿富汗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方作为主角进行讲述似乎都有失偏颇,而任何追求中立叙述的企图又易于沦为某种国际新闻背景资料乃至对外政策评论。但在《王的归程》中,作者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有意借1839~1842年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对这一困局发起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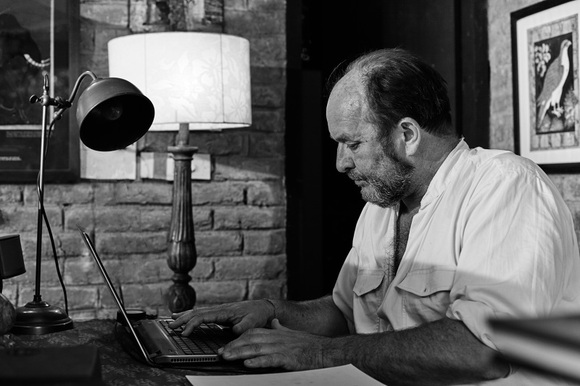
在现代的世界地图上,阿富汗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北限与阿姆河流域的南沿,背靠不可翻越的兴都库什山脉,尴尬地夹在南亚次大陆与中央欧亚之间。这似乎确实构成了一个高度闭塞的地理区域,也为那个著名的头衔“帝国坟场”提供了方便的解释:任何一个前现代定居国家都无法在这样一片缺乏航路的土地上维持后勤补给和有效管治,而现代基础设施的匮乏与无力往往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点。这种政治地理学背景因而让前近代(乃至现代)阿富汗呈现出一种内陆边疆社会的特质,其在很多层面与被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瓜分的巴尔干以及处在哈布斯堡、俄罗斯与波兰夹缝间的加利西亚-鲁塞尼亚的状况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兴都库什山脉留下的无数褶皱比迪纳拉或者喀尔巴阡山区更加难以逾越,将这一地区政治态势的去中心化与开放化推到极端。
然而,考虑到当代通用的阿富汗疆域在1893年由英属印度划定,而彼时的阿富汗已被深度卷入到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当中,这种地理认识对英阿战争之前阿富汗历史地位的理解并没有助益,这也正是《王的归程》在开篇试图提醒读者注意的。
一方面,近代以来的阿富汗地区存在着异常多样化的人口与社会结构,在背靠突厥斯坦的什叶派北方族群、邻近波斯的赫拉特、靠近印度河流域的东南部和为复仇与现实利益所撕裂的所谓“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力学关系,但在另一方面,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近代阿富汗是一个先天等待被人统治的地域。在18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土兵部队进占喀布尔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在阿富汗崛起的杜兰尼王朝曾利用莫卧儿帝国与萨法维波斯留下的权力真空角逐北印度,不但将东南方向的克什米尔与旁遮普(如今都处在印巴两国的实质控制下)纳为臣属,还在1761年堪称前近代亚洲最后一场大决战的第三次帕尼帕特会战中彻底击溃了来自德干高原的马拉地人,在印度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虽然在1772年开国君主艾哈迈德沙阿病死之后,阿富汗陷入间歇性的内乱状态,但杜兰尼的创业者仍为后世的阿富汗君主赋予了在这一地域罕见的独立地位与尊严,直到1808年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团第一次进入阿富汗的冬都白沙瓦时,他们依然能够从艾哈迈德沙阿的直系后裔、来自“正统”萨多扎伊部族的统治者沙·苏贾(尽管他的即位过程远非什么“平稳的权力交接”)的身上见证一种波斯式君主的威光。而随着这位君主在第二年因敌对部族巴拉克扎伊的发难而亡命旁遮普、从统治者沦落为王位觊觎者,英国终于掌握了一笔可用于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政治资本。

而在东印度公司的眼里,沙·苏贾在东旁遮普的流亡政府虽然耗费了巨量的财政资源,且不断与当地驻军发生摩擦,但继续像莫卧儿皇帝那样对这支“帕坦人”(普什图人)加以怀柔起初也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策略。直到名为“大博弈”的地缘战略焦虑迫使加尔各答对阿富汗的现状作出干预,对沙·苏贾乃至阿富汗这个国家估值的天平才在1830年代末彻底倒向了“采取行动”的一边,这一次东印度公司对沙·苏贾的索求不再是财宝抑或常见于中世纪领主间的短暂约定,而是一种长期收益更加稳定的安排。正是这种看似精明的考量促使加尔各答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决策,最终导致了阿富汗灾难的发生。
1838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布《西姆拉宣言》,正式确定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干涉的方针。《宣言》谴责了阿富汗巴拉克扎伊王朝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国内的穆斯林部族对统治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发动圣战以攻占白沙瓦(亦即1808年杜兰尼王朝的沙·苏贾接见东印度公司使团的冬都)的行径,强调了在西北方向拥有一个稳定的亲英盟友对英国在印度利益的重要性;而鉴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表现出对英国利益不利的倾向(其不但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扩张活动,还未能在波斯与俄国的联合攻势面前守住西部重镇赫拉特),英国将诉诸力量扶持沙·苏贾夺取阿富汗统治者之位,直到这一目的达成之前不会撤军。
无论是与1979年的苏联还是与2001年的美国相比,东印度公司介入阿富汗的正式理由都是极为务实的:《宣言》看似用一套简洁的三段论迅速明确了“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哪里”“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何在”,以及“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达成它”,这构成了一套教科书式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三段论,没有为任何“解放”“打击恐怖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福音主义语汇留有余地。英俄之间围绕内陆亚洲的“大博弈”也由此发轫,并成为(自称)现实主义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地缘战略实践。但这种令“大博弈”擦枪走火的理性修辞是否真的意味着决策者的决策过程真的是理性的,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又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博弈”的走向?
这正是《王的归程》在1839年英阿战争爆发前所要澄清的第二个问题:“大博弈”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场伦敦对彼得堡的全球战略对决。诚然,“大博弈”在主观上是一种贯穿整个亚洲大陆的大规模战略竞争,但“大博弈”现场与两大帝国核心部分之间巨大的物理距离意味着实际主持前线工作的冒险家、外交官乃至总督在很多问题上无法唯上级指示是从。换言之,一种从白厅直接传达到伊斯法罕或坎大哈的顶层意志在大多数时候(在电报发明之前的1830年代更是如此)并不存在。恰恰相反,基层人员的自发行动和不同决策层级间信息与话语权的不对称在这场地缘政治竞赛中往往发挥了比全局理性更大的作用。

随着获得俄罗斯支援的波斯军队和直接代表俄罗斯的外交使节维特科维奇在1837年底抵达赫拉特与喀布尔,伯恩斯的外交使命似已注定失败,而《西姆拉宣言》中溢于言表的“大博弈”焦虑也已经坐实。但达尔林普尔却不惮以同情的笔法描述了伯恩斯在俄罗斯的触角正式深入阿富汗境内的时刻曾一度拥有的优势:作为早在1830年代初便已造访阿富汗并赢得多斯特·穆罕默德私人友谊的先来者,伯恩斯在外交场合始终受到巴拉克扎伊王室的优待;阿富汗方面在整个1837年底都维持着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对于俄罗斯的尊重,与只能与阿富汗大臣见面的维特科维奇相比,伯恩斯依旧垄断着直接面见多斯特·穆罕默德埃米尔的特权。但在1838年春天维特科维奇利用偶然的机会赢得阿富汗朝臣青睐、并获准参见多斯特·穆罕默德后,伯恩斯在阿富汗宫廷享受的宠臣式待遇便很快凋谢了,英国失去了最后一种影响巴拉克扎伊王朝的和平手段,武装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
伯恩斯的策略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在全球殖民帝国尚未成熟时的体现,但也带有一种鲜明的前近代色彩,这从阿富汗君主的个人偏好与国家外交政策的紧密关联中可见一斑。但达尔林普尔也指出了伯恩斯私人外交背后东印度公司政治支持的缺失:直接决定对阿政策的总督府在对阿富汗当地形势的判断和情报的收集上全然信赖当时并未深入阿富汗本土的情报系统,这让总督府在发表《西姆拉宣言》前(相对于伯恩斯的观点)低估了巴拉克扎伊王朝的军事力量和统治稳定性。
达尔林普尔并未明确断言1839年战争是一个可以通过更合理的政治手段避免的结果,但他无疑认为这种对巴拉克扎伊王朝和多斯特·穆罕默德本人的持续妖魔化叙事为英阿双方在1839年初走向战争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这种妖魔化叙事的背后并不只有东印度公司情报部门出于客观(尽管并不准确)分析得出的认识,也存在着外交与情报人员之间争夺话语权的因素。在这里,达尔林普尔关于“大博弈”外交的叙述暗示了历史的多种可能的走向,其意旨已不只在于讲述往事,也是在向当代的一种外交政策观提出质疑:仅凭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能否让决策者更好地认清国际关系的“现实”?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已经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给出了答案。
如果说在阿富汗这片“帝国坟场”里每一个挑战者都迎来了类似的结局,那么至少在1842年决定停止对阿富汗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死法”尤为惨烈。1979年的苏军和2001年的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虽然陷入了治安战与恐怖袭击交错的泥潭,但两军正规部队本身并未在任何一场重要战斗中被显著地击败,而在1842年1月的第二周里,撤离喀布尔的东印度公司占领军在兴都库什山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6000名以上的战斗与非战斗人员全军覆没,如此彻底的毁灭即便在英国海外军事史上亦难有出其右者。
鉴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军在火炮以外的军事装备上并无压倒性优势(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后半叶,阿富汗人的长管步枪“杰撒伊”仍令英国人印象深刻)且从未接受过在高寒山区作战的训练,这场灾难在技术层面显然不会缺乏解释,但在达尔林普尔看来,东印度公司的失败首先源自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决定,而正是这些决定让第一次英阿战争的走向与结局充满了寓言意味。
尽管在1838年发表《西姆拉宣言》公开阐明了在阿富汗扶持亲英政权的战略意图,但对1839年夏天进入喀布尔的英国人来说,发动阿富汗战事的时机从一开始就是尴尬的:东印度公司在1837到1838年间刚刚经历了毁灭性的印度斯坦大饥荒,从1840年开始又不得不在远东对清帝国发起一场耗费巨大的海陆两栖军事行动。这让加尔各答方面对阿富汗远征的基本判断从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升级为一种经济上的现实主义,东印度公司的收支平衡考量决定了英国只能在阿富汗维持最低限度的存在,其所寻求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工程也只限于在当地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以节省开支。

然而,在以君主和部族领袖间基于赏金和兵役效忠的交换所结成的主从秩序为底层逻辑的普什图社会,任何军事力量集中化的尝试都等于彻底改变阿富汗政治的基本骨架,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为了在经济上解决军费,必须反过来在政治上加大投入,绕开低效而落后的王朝政体、直接从加尔各答统治阿富汗,而这势将意味着无比激烈的反抗。只有少数真正熟悉阿富汗社会的人(如业已在阿富汗军事占领体制内被边缘化的亚历山大·伯恩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控制欲螺旋”的必然后果,而当英国驻喀布尔的军政机关正式认识到这一两难的灾难性后果时,反英的普什图部族武装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
在《王的归程》结尾,达尔林普尔的历史叙事与阿富汗的现实终于实现了紧密的汇合:在走访1842年英国驻军灾难性撤退的现场时,达尔林普尔偶然发现这条路线途经的大多数区域正好是当时塔利班武装的控制区,而当年曾在兴都库什山区痛击英军的普什图部族依旧居住在原地,且为当地的塔利班武装提供了绝大多数兵员。而在《王的归程》付梓的2013年,主导阿富汗新政府的部族在血统上正好也是沙·苏贾所在的萨都扎伊部族的后裔,随着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再度下降到最低限度,这一“不幸”被西方世界选中并扶持为亲西方政权的部族是否将迎来和祖先类似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