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诞生九十年之际,我们需要以纪念他生日为理由,深入地去把握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我的印象中,纪念哈贝马斯的九十大寿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哈贝马斯有关的活动里)最盛大的一次 。”在日前“新京报·文化客厅”主办的“哈贝马斯,生日快乐”活动现场,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回忆道。德国哲学研究专家薛华也认为,这一段时间对哈贝马斯的纪念活动称得上是一个公共事件。对比二十年前的哈贝马斯访华,薛华认为这次的纪念更有全民参与的特点,“之前是由社科院组织,这次对哈贝马斯的纪念完全是自发的,是出自人的内心。那次前后不过维持了半个月的时间,而这次时间更长,相关的论文质量也更高。”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公共领域研究到交往理性的提出,从对现代性的思考到后民族主义构想,他的理论对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大陆学界同哈贝马斯建立直接联系是在1980年,那时中国社科院和北大学术代表团访问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薛华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2001年,哈贝马斯第一次正式访问大陆,他在各大高校发表了七场演讲,主题涉及后形而上学、民主、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等,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甚至有媒体将这次访问与上个世纪罗素、杜威和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

在中国,哈贝马斯被了解、被研究直至产生深远影响,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任剑涛在上大学时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中的哈贝马斯部分,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看到了“邮政自由主义”这个词,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那是“Post-Liberalism”。几十年过去,从不知所谓到深入研究,中国知识界对哈贝马斯思想接受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对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乃至官方而言,哈贝马斯既是一位德国思想家,又是一位切中中国问题的学者,正如任剑涛所说,“在哈贝马斯诞生九十年之际,我们需要以纪念他生日为理由,深入地去把握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任剑涛认为,哈贝马斯极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深切地关心社会大灾难后人们怎么办的问题,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种反思精神也同他个人的经历相关。哈贝马斯从小有患有唇裂,少年时他敏感内向,不易被纳粹的狂热感染。在上大学后,他接触了政治、哲学、历史,开始关注公共议题,并立志未来从事记者行业在公共领域发声。哈贝马斯早年受海德格尔影响很大,但后来觉察到了其亲纳粹倾向,看到海德格尔在二战结束后未做出任何忏悔,依然作为知识名流出入大小公共场合,他很受震动,立志要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对纳粹主义的反思是德国建立民主宪政的基础,他曾极力反对“光复德国荣光”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一位被右翼视作神话且和纳粹切割不清的总理。他的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理论也同他对德国民族主义复辟的高度警惕有密切关系。

除了对二战时期德国的反思,哈贝马斯还关注着欧洲一体化、海湾战争、911、基因科技、宗教及移民问题等大大小小的国际事件,始终坚守公共知识分子责任感,即便年届九十,他的批判之声依然常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
在近期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篇专访中,哈贝马斯说:“我从没有停止批判过资本主义,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痒的诊断是不够的。我不是那种漫无目标的知识分子。”任剑涛认为,他的社会警惕性之高在在世学者中实属罕见。这种精神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他在科索沃战争后撰写的《兽性和人性》一文曾在中国思想界引发强烈反响,而他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也激起了知识分子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滋养着中国思想界的自我反思精神。
更难得之处在于,哈贝马斯作为一个致力于批判的知识分子,同时保持着“温和派、反思派”的立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并不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极力颠覆者。他的政治立场处于极左和极右之间,提出的程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理论“让他稳稳当当站在了中左位置”,这些理论在当时的左派之中并不受欢迎,却促进了战后德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任剑涛提到,这一点对中国而言颇有参考价值,因为“在今天,中国走到改革深水区,极左极右的主张特别容易搏眼球”, 而“现代社会的稳定就在于中左和中右能团结起来去抗拒极左和极右”,极端立场的许多观点都不诉诸实践理性,他说,“哈贝马斯的指引意义在于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制度上。他的民主理念对转型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
哈贝马斯的许多观点令薛华倍感崇敬,他在活动上着重提到了宪法爱国主义及公民不服从两点。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马斯宪政观的核心思想之一,按薛华的总结便是“要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宪法”。哈贝马斯认为,以传统的血缘和文化构建的民族认同来构建共同体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人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公民认同基础,即以公约、宪法的形式构建共同政治文化,并以此作为共同体的维持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国家的热爱不是因为自身的民族或文化身份,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 因此,对现代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而言,重要的不是去寻找民族文化认同感,而是学会参与共同的政治文化。
在宪法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源自梭罗,他靠拒绝纳税来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美国战争,并写下了《论公民不服从》一文。文中写道,“如果一千个人今年拒绝缴税,跟同意缴税相比,前者不算是暴力与血腥的手段,因为缴税将可能使国家使用暴力且使无辜者流血。事实上,这就是和平革命。”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深受梭罗此文影响,之后的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作者)和哈贝马斯也都论述了公民不服从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法律偏离了轨道,违背了民众的政治意志,那么就可以以公民不服从的形式对法律进行批判。

但是,公民不服从同一般暴动不同,它是理性的、非暴力的。1986年,哈贝马斯在接受《星期》杂志访谈时指出,“公民不服从要和革命性的实践严格区分开来,也与暴乱严格区分开来,公民的不服从明确地拒绝暴力。”宪法爱国主义是公民不服从的根基,不服从也是对宪政民主的尊重。“公民不服从不能根基于一个私人的、武断的世界观,而是在原则上要在宪法所界定的范围内。”哈贝马斯也否定了守法最高原则,在访谈中他说道,“对我来说,霍布斯、卡尔·史密斯或《法兰克福人公报》所强调的守法为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党正统性准则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为了什么目的,保持司法和平与稳定是必须的。”
薛华在活动上以朔尔兄妹为例介绍了公民不服从的历史。朔尔兄妹是反纳粹运动组织“白玫瑰”的成员,1943年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派发反纳粹传单时被管理员注意,遭到举报并被纳粹斩首,人们为纪念他们而创设了朔尔兄妹奖,以表彰那些支持公民自由、道德、智识的人。哈贝马斯在1985年荣获此奖,薛华提到,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一荣誉,始终为此感到惭愧。
由此延伸开来,薛华认为中国文化里的不服从传统也自成脉络,“舜立诽谤之木”之中的谤木“就是让人发表意见的”,普通百姓如果对朝廷有看法,可以在谤木上写谏言,批判政事。到了宋朝,朱熹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道统高于王权的政统,学者应当批评当权者不受约束的权力。魏晋时期,许多名士也勇于于挑战权威,“嵇康临到死还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弹《广陵散》。”在薛华看来,他们都组成了中国传统里不服从的“隐约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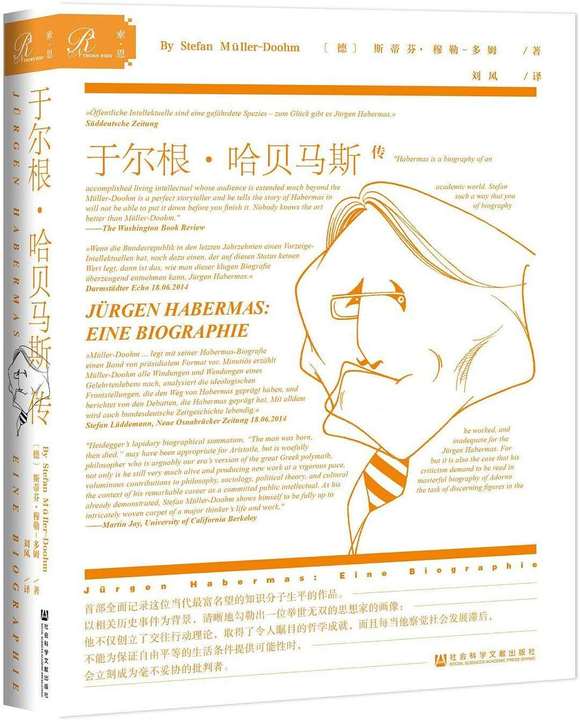
从哈贝马斯所处的德国哲学系统来看,富于公共关怀是其特点之一,任剑涛认为,“德国哲学一直就是政治哲学,沿袭了古希腊传统。那时哲学家必须在公共领域发声才能达至荣耀。” 公共领域也是哈贝马斯研究的重要对象,他在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公民可以在公共领域自由地商谈各类议题,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与之对应的私人领域则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生活领域,在现实社会中,这两个领域的区分并不如理论上那样判然有别,两者之间会有动态的转化或互相入侵。任剑涛指出,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随着报纸和电视等新媒体的介入与泛滥,“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发生重要转型,公私边界划分的重要前提没有了。”人们要么直接将公共问题转化为私人问题,各扫门前雪,要么便是将严肃的公共问题被人们化约为茶余饭后的笑谈,以消解愤怒与无奈。
任剑涛认为“公共”这一概念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在对谈中,他区分了publicity(公共性) 和 the public(公共)两个概念。国内对“公共性”一词的关注最早是由200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汪晖《文化与公共性》一书引发,他认为,谈“公共性”而不谈“公共”实际上是有误导作用的——“公共性”是存在于任何没有公共制度建构的国家的底线的一致性,再专制的政权都有这样的公共性;“公共”背后却有着一套严格的公共哲学,这种哲学是特定现代产物,它来自英国,“理念上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政治上就是民主现代化,文化上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及其重构体。”任剑涛分析认为,“我们捍卫‘公共’的热情,应该要超过我们捍卫‘公共性’的热情,因为‘公共性’背后的假设,可能恰恰在剥夺我们的‘公共’。”
在许多国家,对“公共”的维护往往由公共知识分子来引导,但在任剑涛看来,当下中国对公知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略显激动地谈到了中国社会对于公知的污名化,“大家现在对公共事务避而不谈,反而反对公知,这也是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许多公知对待启蒙的姿态也需要改变,公知不能高高在上地传播真理,而应该为创造和引导公共讨论发挥作用,“启蒙绝不是中国很多人以为的‘你蒙我启’,启蒙是‘有蒙共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