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该学院自1810年创立以来第十位“精挑细选”的荣誉院士,此次也是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学术研究中心。莫言将出任该写作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苏童和余华受邀成为首批驻校作家。

文 | 环球YOLO精英 周元
编辑 | 美龄
6月12日,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荣誉院士称号,以表彰他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贡献。同时,成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院长罗伯特·埃利斯与莫言一起,为“莫言国际写作中心”的牌匾揭幕。
莫言是该学院自1810年创立以来第十位“精挑细选”的荣誉院士,此次也是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学术研究中心。莫言将出任该写作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苏童和余华受邀成为首批驻校作家。

即使距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已经过去了七年多,莫言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作家,从未远离过公共舆论的中心,互联网时代,他的言行被无尽放大:一会儿是中国的“诺贝尔奖英雄”,一会儿是抹黑国家的暗黑书写者;一会儿是鼓与呼的“民族良知”,一会又是圆滑逢世的“话语媚客”……

在众多场合,莫言只能选择尽量沉默,一如他的名字一样。提及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他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第一次发生关系。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只能作为一种习惯来承受它。”
无论莫言说什么,他都在不断被解读、被关注,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读者和文坛对他再推新作的期望一直很高,但莫言并不算高产,他愿意一遍遍打磨修改,因为在他看来,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是任何奖项无法替代的,“这不是因为读者,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追求完美的愿望。”
1955年,原名管谟业的莫言出生在高密县大栏乡平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年幼的他几乎瘦成一根豆芽,“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过,甚至连煤块都敢啃,“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
家里虽然穷,父母还是咬牙送莫言去读书,后来因家庭成分不好,回家务农,主要从事农业,比如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
莫言喜欢看书,没有书的时候他也会看《新华字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后来,莫言靠着《中国通史简编》这套书度过了农村劳作的漫长岁月。他时常自言自语,但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念叨什么,这让家人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莫言萌生写作的念头,原因很简单,就是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1976年,莫言经过4次报名后终于如愿参了军,在部队中,他干过保密员,也当过图书管理员,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1981年,莫言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处女作发表大喜事的鼓励之下,他继续不断地写作,然后连续投稿,然后发表。

1982年,莫言被提为正排级干部,并在第二年被调到北京的部队。这一年,他的作品《民间音乐》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赞其有空灵之感。之后,著名作家徐怀中也看到了这篇《民间音乐》,十分欣赏,破格给了莫言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考试的机会,莫言顺利通过考试,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
1985年,莫言因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汪曾祺、史铁生、李陀等人对此都高度评价,更有人将其称为是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也是这一年,莫言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凡是触及故乡,他似乎都有写不尽的话。
第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横空出世,引发强烈反响。莫言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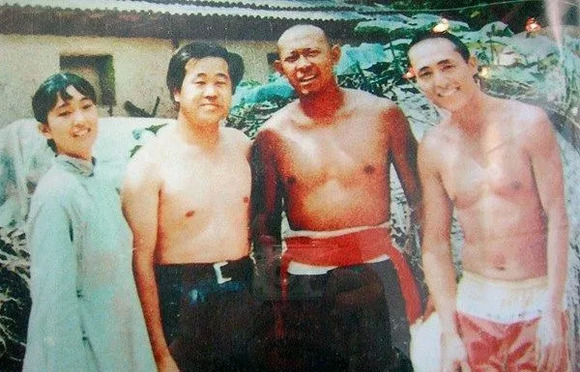
之后,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专门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和莫言商议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在张艺谋看来,纯朴的生命中展现自然的艺术,美轮美奂,令人神往。当时,莫言对张艺谋提出的改编也没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也是这部电影,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2000年,《红高粱》被《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和作品是永恒的主题。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是应该先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事情,跟自己切身最为相关的事情。“你要持续不断地写作,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必须回到自己的记忆当中去、童年当中去、故乡当中去。”
莫言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抵抗式的写作,常引人注目,让很多人咂舌,比如《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等。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量的累积,“我的那种有意识的抵抗越来越少,回忆和温情变多,但还是会有争议,比如《丰乳肥臀》。到1998年以后的写作,我变得更低调,甚至说要大幅度往后退,有意识地压低写作的调门,比如《檀香刑》。2000年以后,我觉得无论刻意地对抗,还是刻意地低调,都是故作姿态。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所谓求放心,跟着我自己的心去写,寻找一种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开合、大怜悯、大慈悲和大解脱,就有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

对于莫言,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予的评价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并不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但他却拒绝成为第二个“马尔克斯”。“高密是我的故乡,童年的经历是我独有的,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想成为某个作家的翻版,既想写普世的价值,又想写出属于中国独有的特色。”他说。
无论是在获诺奖之前,还是载誉归来之后,莫言始终认为,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女儿管笑笑。

管笑笑6岁之前一直跟母亲住在农村。1995年,管笑笑和母亲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氛围的浸染,管笑笑自小也爱读书,大一就创作完成长篇小说《一条反刍的狗》。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后来这部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一对父女作家,给文坛平添了段佳话。
成名之后,莫言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如今陪伴家人的时间愈发少了;自己扎根农村,是个农民,如今在城市中参加各种活动,有时也身不由己;奖项是短暂的荣誉,一个作家还是需要拿出更多的作品……
无论是7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如今当选牛津荣誉院士,并在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命名学术研究中心,莫言始终被关注、被阐释,一直处在舆论漩涡之中,“我非常企盼着,我现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企盼着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一旦出现以后,热点、焦点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