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合作社令人生疑。我们是否还需要另一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实验?如果合作社并非空想,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实践如何能在现实中存续下去呢?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工作场所的民主和平等?又会不会只是另一种让劳动者自我欺骗的企业意识形态?

撰文 | 李丹宁
编辑 | 黄月
今年3月末,一些程序员对过度加班的抗议掀起了一场关于职场过劳、加班文化、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互联网公司生态以及劳动者权益的讨论。然而,除了劳动者、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几轮舆论切磋,似乎没有什么真正被改变:没有哪一家大企业的声明试图改变工作场所的过劳现状,许多劳动者仍旧处在企业文化导致的过劳压力之下,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全无掌控。在一切照旧的现实面前,渴望改变的上班族还能做些什么?在对既有工作框架的被动接受中,我们是否还有想象理想工作场所的权利与能力?
在这场网络大讨论之外,一些青年在线下行动起来,在北京发起了为期四周的“社畜博物馆”活动。“社畜”一词发源于日本,是“会社”与“牲畜”的结合,意指像牲口一样为公司干活、任公司使唤的上班族。除了“社畜博物馆”活动现场的影像、文献等展品,观众也可以带着与自己工作经历有关的物品来参加展出,分享自己作为“社畜”的日常经验。此外,“社畜保健所”工作坊试图为那些在职场疲于奔命的人提供身体与心灵上的保健服务;名为“四季葬礼、宗卷、宝札和亚洲劳动厚生处”的活动则为近十几年因过劳而死去的人举行了集体纪念与追悼仪式。这四周时间里,学者讲座、圆桌讨论、阅读和电影放映等活动也促使参与者共同讨论了就业形式、性骚扰、劳动休息权和城市居住权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时,这些青年在合作社这一形式里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没有老板,没有加班,共同决策,公平分配”——每一个成员共同拥有合作社,对合作社的运营发展拥有投票权和话语权,也因此有机会创造更为理想的工作环境,并在更大程度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它当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社畜博物馆的一位发起人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说,“但它一定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种方式。”
乍看之下,合作社令人生疑:早在两百前年,傅里叶的“法郎吉”(Phalanges)、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New Harmony)以及与之类似的社区实验就幻想过解决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并以失败告终,我们是否还需要另一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实验?如果合作社并非空想,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实践如何能在现实中存续下去?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工作场所的民主和平等?又会不会只是另一种让劳动者自我欺骗的企业意识形态?
1903年,美国游戏设计师里奇·麦琪(Lizzie Magie)设计了一款名为《大地主》(The Landlord's Game)的桌面游戏。游戏里,几个玩家在棋盘上轮流掷骰子前进,买地建房,贷款投资,通过向其他玩家收取过路费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来积累自己的财富,直至所有对手纷纷破产出局,最后的赢家一人垄断所有地产。麦琪创作这款游戏的灵感来源于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亨利·乔治发现,横贯东西岸的铁路建设在给加州带来经济飞跃的同时,也抬高了地价,成就了一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却也让劳动者越来越难以负担地租,加剧了贫富间的差距。作为亨利·乔治反土地垄断与地租税政策的支持者,麦琪希望这款游戏能让玩家直观地认识到土地垄断如何危害着社会公平,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这款游戏便是如今流行全世界的桌游《大富翁》(monopoly)的原型。讽刺的是,在重新设计与广泛流传的过程中,游戏的初衷已然被遗忘;相反,玩家在游戏中体验着垄断经济带来的快感:对手们最终身无分文,而你实际拥有了一切。游戏的流行也隐约反映出了这种破坏性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如何自然地融入我们的日常中,以至于从孩童时代起人们便潜移默化地接受着这种价值观并享受其中。

2011年出现的另一个游戏《Co-opoly》试图打破这一局面。它基于合作与互助并非相互竞争的逻辑:在游戏中,玩家们既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共同组成一个合作社,作为一个整体在棋盘上前进;面对不同的挑战,玩家与其他成员共同决策,并平衡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果任何一个人破产了,所有人都会输;而如果整个合作社破产了,每个人也都会输。游戏的目的不是某个人赚得盆满钵满,而是把合作社运营下去,并用盈余开拓另一个新的合作社。换言之,游戏的核心不是我V.S.他们,而是我们V.S.各式各样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游戏的发行者“教育和社会行动工具箱”组织( The Toolbox for Education and Social Action)本身也是一个工人合作社。

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时代,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使得许多熟练工人陷入贫穷的生活。当时市面上流通着的食品已经让一些穷人无力负担,1844年,英国罗奇代尔的28个工人与工匠在4个月的时间里凑齐了28英镑,决定开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小食品店,来供应他们自己能负担得起且质量优良的燕麦、糖、面粉和黄油。他们吸收了先前合作组织的民主特征,发展出了自己的组织原则,包括入社自愿、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按交易量分配盈余、重视社员教育等。不久,这个小合作社的食品获得了物美价廉的名声,更多的人开始加入合作社,成为了合作社的消费者兼社员。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们扩展了供应食品的种类,并在一年的经营后收获了710英镑的营业额,社员增加到74人。此后,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并陆续开办了面粉厂和纺织厂。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成功掀起了英国及海外的纷纷效仿,也让“罗奇代尔原则”发展为这场国际范围的合作社运动的指导原则。
正是这些原则让合作社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形式。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为了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要,个体们自愿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这意味着合作社旨在服务于每一个社员,而非少数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在投资和股份上做出限制,合作社防止以逐利为目的的投资,并鼓励合作社的使用者投资和自主控制。在这里,打破传统租车公司模式、乃至“共享经济”公司盈利模式的租车平台合作社,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育和社会行动工具箱”组织的David Morgan在《“共享经济”是一个问题》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发现,共享经济平台依靠匹配外部的共享资源,以极低的成本获得极高的利润,以至于在2014年租车平台公司优步已经成为了市值四百亿的公司。然而当平台从司机的每一笔交易中轻松获利时,平台上的司机作为非正式的合同工,却无法享受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不受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在松散的结构中甚至无法联合起来争取权益——共享形式甚至成为了专职司机的噩梦。
面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和共享平台的状况,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二百多名司机选择不再向传统出租车公司缴纳昂贵的租赁费,或是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送给平台大亨,而是共同成立了“联合出租车”(Union Taxi)——一家由出租车司机自己拥有和管理的租车合作社。由于合作社的资产归他们自身所有,司机们无需缴纳租车费,除了日常交易的收入,每年年末还可以获得一笔盈余。事实上,早在1979年,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出租车司机们便因罢工无果,转而成立了自己的 “麦迪逊联合出租车合作社”(The Union Cab of Madison Cooperative),并一直运营至今。在这些例子里,合作社成为了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武器,来获得理想的分配模式与工作条件。

合作社的另一个原则是民主治理与决策。这意味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每个成员都有话语权决定合作社的基本章程、收入分配方式、工作时长和运营方向等,而非被动接受他人定下的决策、工作规则乃至基于权力关系所形成的潜规则。在纽约的皇后区,三名跨性别拉丁裔女性成立了一家美容合作社(Mirror Trans Beauty Coop),希望能为跨性别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2015美国跨性别调查发现,跨性别拉丁族裔比跨性别白人受到更多的就业歧视,27%的跨性别拉丁族裔人士因他们的性别认同在职场受到差别对待。发起人Joselyn Mendoza在接受VICE采访时提到,自己之前在餐馆工作时常常加班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另一名发起者Castillo也曾经为了不丢掉工作,在被诊断出结肠癌与乳腺癌后也不敢请一天假去看病。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职场环境之后,她们决定成立一家由自己做主、没有歧视的合作社,公平分配收入,能够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而不必再错过英语课或医院的挂号,并有权选择自己的客户,拒绝那些粗鲁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者。在没有良好的职场环境与公正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她们为自己开辟了这样一片空间。

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理念中,合作社是由“价值”而非单纯的“利润”所驱动的,它们常常致力于为社员提供福利与教育,并服务于社群的发展。波多黎各的一所监狱里有一个由囚犯组成的合作社(Cooperativa de Servicios ARIGOS)。起初,它只是监狱帮助囚犯创作艺术和工艺品的一个心理治疗项目,1993年,几个囚犯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成立了合作社,出售大家在狱中制作的艺术品。参与者在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渐重建自尊,并学习到更多出狱后回归社会所需的技能。事实上,许多合作社在成立之初便以服务社群本身为目的,因此,合作社有着比在市场中逐利的公司更为丰富的范畴和内涵。
合作社绝不仅仅存在于零星案例中。从工业生产、农业加工、杂货零售到住房、医疗、学校、媒体,合作社可以出现在各种行业的各个环节里,使人们以一种更平等的合作关系满足各种各样的经济需要。全世界至少有12%的人口是世界上300万个大大小小的合作社中的一员。据世界合作监测组织2017年的统计,300强合作社和互助组织的总营业额为2.1万亿美元,合作社为全球2.8亿人口提供了就业,占世界就业人口的10%。作为一种能够带来社会效益、为弱者赋权的经济合作形式,一些地方的市政府(如美国的纽约、罗切斯特、麦迪逊)已经开始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和法律方面的帮助,以帮助这种组织形式获得更多来自社会的了解与支持。
提到合作社便不得不提世界上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系统。它的业务网络覆盖工业、农业、零售业,生产从自行车到工业机器人的各种产品,并拥有自己的银行、提供抚恤金与医保的社会保障合作社、科研中心以及学校。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无论从资本、销售额还是创造的就业数来看,它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截至2014年,它已拥有7万名合作社成员和257个下设的机构及组织,成为西班牙第十大集团。
更惊人的是它的合作社性质:所有的股份均来自合作社的劳动者,从流水线工人到高层管理的每一个成员在社员大会上均有投票权。蒙德拉贡长久以来一直是工业工人阶级转型的典范,它在创造就业、发展地区经济、维护工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等方面的成就被世界各地广泛研究和借鉴。它的民主与高效同时吸引了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支持者、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提供着工作场所改革的最佳范例,这其中的成就是工会与政治党派无法从外部达成的。

当基于蒙德拉贡模型的合作社法规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确立起来,它似乎成为了一个市场可行性与工人民主相结合的神话,可以脱离语境在任何环境中被复制。然而,合作社是一种十全十美的经济合作形式吗?更重要的是,当太多有关这一体系民主、平等特征的言说被广泛传播与接受,人们似乎忘了站在工人的角度去问一句:对他们来说,合作社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日常工作生活?
这便是美国人类学家沙林·卡斯米尔(Sharryn Kasmir)在著作《蒙德拉贡的迷思:巴斯克小镇上的合作社、政治与工人阶级生活》中试图解答的问题。作者于1989-1990年在蒙德拉贡展开了参与观察,希望从工人的视角去理解合作社对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次在蒙德拉贡体系中的合作社之一Fagor Clima参观时,卡斯米尔询问人事部主管这里有多少工人、多少管理者。主管的回答是:“我们都是工人。”言下之意,这里没有社会阶级。在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系统里,社会团体的划分不按照技能、工资或地位,而是以是否直接参与流水线划分为直接和间接劳动者。然而不同于管理层的言说,在卡斯米尔对合作社工人的访谈中,她发现工人们往往将经理、工程师与合作社委员会中的代表称为“老板”,或是不同于“我们”的“他们”。这种对立的划分是否意味着工人将决策委员看作是由管理层控制、而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民主机构?一个工人曾经这样形容外面的私人企业:“至少他们不假装平等。”
这是否意味着合作社平等的理念是一个谎言,而民主的架构则只是个空洞的形式?是什么阻碍了工人参与合作社的民主决策?Antxon是Fagor Clima的流水线工人,同时也是一名合作社的社会委员会代表。他向卡斯米尔说明,实践民主的技能和时间的缺失都限制了成员们参与管理决策。“每个社会委员会代表每月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向大会报告自己部门的情况。如果你想要一定的参与度,这点时间是不够的。……当经理人发展出了新方案,我们理应是对这些方案进行批评,或者提出代替性方案。为此,下班后我们不得不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来阅读和分析这些方案。实际上,我们也没法提供什么代替性的方案。”在讨论中,工人们常常为各种有关财务、商业方案和产品的技术性信息所淹没;他们能接触到信息,可是却没法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这在无形中让工人对于参与委员会不再提得起兴趣。
此外,当合作社的意识形态让一些工人相信所有成员具有同样的权利,相信工作场所并不存在所谓身份的不对等,一些工人们便容易自愿将权利让渡给那些他们认为在决策上更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角色。由此,委员会不再是工人与管理层双向交流的平台,而是越发成为一个促使工人接受管理层命令的机构。当工人试图解决表达自己的不满时,这套“容许异议、鼓励对话”的机制又反过来使得工人只能在现有框架的内部解决问题,消解任何可能产生的冲突。当工人没法像在传统工会中那样与管理层相抗衡,这种“对话”的姿态只是加深了他们在共同决策中的无力感。

于是卡斯米尔发现,这套参与式结构与工作民主的意识形态对于合作社里那些管理层员工来说似乎更有意义,他们更积极地宣扬合作社的价值,相信在这里人人平等。然而这样的言说里却没有包括工人真正的经验。工人对这种意识形态是失望的;这非但不是他们的日常现实,甚至还否定了工人自己言说自己经历的言语。“至少在一般的公司,你能骂老板是个婊子养的,”一个工人对卡斯米尔倾吐自己的不满。当外界对合作社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基于管理层的言说,一个过于正面的合作社形象便产生了——正是这种对合作社经验有所选择的呈现,创造着蒙德拉贡的神话。
作为对比,卡斯米尔也观察了蒙德拉贡附近地区的一个私人公司Mayc。不同于合作社里经理与工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委员会,私人公司里的工人委员会将工人意见反应给管理层,但无权参与公司事务层面的决策。1989年,Mayc公司希望扩大出口洗衣机的生产,因此决定给工人增加一轮生产班次,这轮加班将影响到两百多个工人的工作生活安排。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工人委员会在咨询工程师后,提出了增添流水线、雇佣更多工人的替代性方案,这样既能增加出口,工人也无需加班。虽然工人委员会无权参与经营方案的设计,但其行动旨在维护工人自身的工作安排,这在他们的权利范围之内。当年,工人委员会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工人还是不得不加班生产。然而在几年后,在企业决定再次扩大生产时,他们的方案被采纳了——更多的员工被雇佣来满足生产需要,工人们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作息。虽然工人委员会并没有立即为工人们赢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它能够求助于外部的法律和工程专家,尝试做出本属于管理层特权的决策,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也是对私人公司里工作民主的一个补充。
在一般认知里,在私人公司里大小事宜的决定权仅由少数人掌握,而合作社的工人则是合作社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合作社工人参与决策的能力、精力与积极性——其中有成员的个性差异,也有结构性因素施加的影响——都在限制着这些权利的施行。反过来,私人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也能有效代表工人的权益,给予工人一定的话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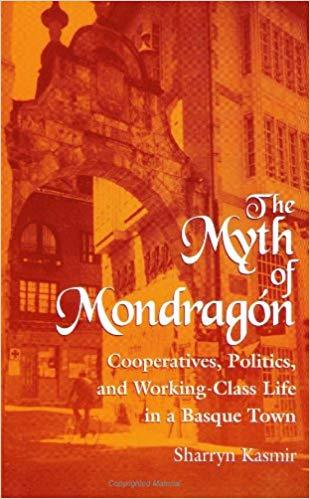
在此,卡斯米尔提醒我们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区别,并重新审视“参与”与“民主”究竟为何:这些美好的词语常常与合作社的意象绑定在一起,可是当工人丧失了参与民主的积极性,合作主义还是参与的、民主的吗?反之,在一般的公司里,尽管工会与管理层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否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呢?
合作社的精神在于使每一个工作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并有足够的话语权为自己做主。它百年来的基本原则旨在扩大工作者在私人公司里有限的参与决策、更充分地享受劳动成果以及自我实现的权利。然而当我们过于迷信它的形式——包括它强调平等参与的意识形态和包容异议、创造对话的机制——并寄希望于这个体系本身能带来民主协商、平等参与的工作方式,我们似乎忽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个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无论是渴望在主流的公司框架内追求更多的工作自由,还是在别的可能性里探索理想的工作模式,不应该忘记的是:只有我们自己才是能够行动起来争取自己权益的主体——去发现我们所身处的体系的弊病,去尝试解决问题,去联合起来创造解决问题的空间。
参考资料:
林徽,《我的“社畜”生活:工作13个月哭过100次,每天都感到慌张和恐惧》 钛媒体影像《在线》 2019年5月7日
https://m.tmtpost.com/3928125.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合作社的七大原则
Brain Van Slyke,《垄断创造问题,合作提供解决》2012年3月7日
https://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2-03-07/monopoly-presents-problem-co-opoly-presents-solution/
David Morgan & Brian Van Slyke, 《“共享经济”是一个问题》,《Truthout》2015年11月19日/art https://truthout.org icles/the-sharing-economy-is-the-problem/
Mary Hansen, 《假如优步是一家工人合作社?这些丹佛出租车司机让它成真了》《Yes! Magazine》2015年4月10日
https://www.yesmagazine.org/new-economy/uber-unionized-worker-owned-co-op-denver-cabbies
Moira Lavelle, 《这些拉丁裔跨性别女人开了一家美容合作社来对抗歧视》,《VICE》2019年1月5日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neppwq/transgender-beauty-coop-queens-new-york
Ajowa Nzinga Ifateyo, 《世界上第一个囚犯工人合作社》2015年9月16日
http://www.geo.coop/story/worlds-first-prisoner-worker-co-op
Sharryn Kasmir, The Myth of Mondragon: Cooperatives, Politics, and Working Class Life in a Basque Town. SUN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