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给人类网络连结增加了复杂度,全球化是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它不仅让世界变得更小、地球变得更平,还让外部冲击更加不可预测,个人建立人际联系的激励与社会的最优选择之间存在更为普遍的矛盾。

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孔笑微
在现代互联网诞生几千年前,人类已经生活在巨大的网络之中,这是一个激动又沮丧的现实:今天的社会图景的基本架构,从网络观点上,或许只是节点数量和复杂程度的差异。移动互联设备与社交媒体,给每一个节点上观测者——你和我——一种微型信息中心的幻觉,而事实上决定我们在社会这张大网中的位置的,仍然是人和人构建的节点和分叉。
在本月全球观众纷纷吐槽《权力的游戏》最终季人设崩坏、剧情奇葩之际,不妨从巨龙与异鬼的奇幻世界中移开眼睛,稍微换一个观察角度。为什么“龙之母”丹妮莉丝在厄索斯大陆无往不胜、所向披靡、备受爱戴;而同样携三条巨龙、兵强马壮、人才济济,作为根正苗红的正统公主杀回维斯特洛老家,秉持一样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愿望,却屡遭背叛和挫败,甚至被逼成屠城暴君功败垂成?固然有编剧乱开金手指的因素,然而丹尼莉丝在两个大陆上政治网络节点的不同位置,不可不说影响了她通往铁王座的权力之路。

让我们先看看一个真实世界权力更迭的故事。象维斯特洛大陆上盘根错节的各大家族一样,寡头家族是把持意大利商业城邦的主要势力,佛罗伦萨在1433年放逐了美第奇家族主要成员,包括后来著名的族长科西莫。这个决定背后站着当时两个最有权势和财富的本地家族:斯特罗齐和阿尔比齐;美第奇尽管是后起之秀,在财富与政治席位上暂时还无法与之相比。
然而反转出现了:美第奇家族的放逐没有持续多久,对手低估了科西莫的能力。他通过盟友将大量资本转移出佛罗伦萨,在之前卢卡战争打击已经造成悲观的预期下,此举立刻刺激产生了金融危机。紧接着,在新的执政团选举中,美第奇家族和盟友一举扭转了局势,极大控制了新的人选——1434年秋天科西莫和美第奇家族在盛大游行中重返佛罗伦萨,几天之后被放逐的就是阿尔比齐家族——这次是永久驱逐。 美第奇家族开始了在佛罗伦萨统治盘踞300年的传奇权力历程。

没有巨龙的美第奇为什么能够成功改组政府、反攻倒算?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在财富、政治权力之外另一个维度上经营的成功:通过商业与联姻,制造了相比其他家族而言更加有中心度的网络位置。美第奇家族围绕着银行的商业模式,让他们不仅与精英家族,还与更多的非精英家族、宗教领袖产生了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同时美第奇家族非常积极地用联姻来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在一幅佛罗伦萨上层社会的网络节点地图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美第奇家族的商业和婚姻联系,不仅数量上远超其他家族(是竞争对手阿尔比齐和斯特罗齐的两倍),而且位置上居于“中央联络人”的节点,也就是不同家族之前通过美第奇家族才联系在一起——这大大增加了美第奇调动“一致行动人”的潜力,即使明面上他们在议会的实力不如对手。
龙女王丹妮莉丝返回维斯特洛大陆之际,也曾积极地联络盟友,然而在这个“旧世界”前朝公主已经成为外来人,首都君临作为中心节点,仍然能迅速组织政治力量。丹妮的盟友高庭、多恩,被迅速各个击破而她未能及时应援,导致属于她的网络节点迅速萎缩,信息与影响力开始指数化坍塌。
而最致命的错误,无过于在决定“夺铁王座”和“抵抗异鬼”这两项任务的优先次序中,丹妮选择了边缘节点而放弃了中枢。联合北境抵抗异类固然深明大义,但是北方的作战在节点上处于信息极为不利的地位,南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人民几乎对此一无所知,牺牲巨大也难以争取民心;同北方贵族联盟更是败笔,网络边缘节点本身对外联络通道少,而且难有动力和物质能力去增加联系。即使没有琼恩作为竞争者出现,一心想独立的北方为龙母提供中原逐鹿的资源亦是有限。
网络节点的“中心度”决定了位置重要性,决定了你是否能被更看到,你的信息是否能被更快接收到,你的中介地位会不会被其他节点优先选择,从而导致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在资源与信息的争夺战场上被充分,甚至不合比例地过度代表。当我们在媒体上第一时间为巴黎圣母院的浩劫喟叹的时候,还要等上很久,才从身边水果蔬菜价格上涨惊觉附近郊县的水旱灾害、异常天气。衡水与毛坦厂的孩子从灯火耿耿的自习室望出去,迷茫的夜雾那一端只有灿烂的超级都市——夜间谷歌地图金色的灯光节点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秘密肖像。
世界在变小,似乎听上去不是什么惊人的秘密——但是事实上,世界一直以来就很小。社会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名的服从性实验的主导者)1963年发起了一项极富想象力的追踪实验,结果惊奇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网络构造的内在简洁和效率。

实验挑选了居住于肯塔基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志愿者,请他们想办法把一些仅知道收件人部分信息(如姓名和职业)而不知道地址的邮件发出去,方法是发给自己的熟人,认为他们更可能认识收件人。这样屡经转折之后,64封邮件最终成功到达,而平均需要的转手次数仅仅稍大于五次,也就是说两个随机选取、看上去毫无联系的社会个人节点,中间仅仅间隔6个人。这就是著名的随机网络“小世界实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来流行的“六度间隔理论”。后来在社交网络Facebook上的重复性验证显示,任何两个活跃用户之间的距离只有4.7个连接,与“小世界”实验结果惊人地吻合。
更让人吃惊的是,即使退回中世纪,世界仍然是大致联通的, “小世界”现象依然存在,只不过从一个人到另一个平均需要的步数,根据当时的人口密度, 大致是10-12而不是现代社会的5-6步, 从对中世纪的数次巨大瘟疫传播事件的研究都揭示了这一点。“小世界”并非是通讯连接技术发达之后才产生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构造的内生拓扑框架。
“小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令人震惊地证明了一个高效联通的世界,特征是“稀疏”而不是稠密的。两个随机网络中任意节点的平均路径,远远短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即使离群索居,也不可能真的与世隔绝——就像你不管怎么闭目塞听、停电断网,想躲过《复仇者联盟4》或者《权力的游戏》的剧透,“阵亡”的时间仍然大大短于想象。 社会网络的“稀疏性”是反直觉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拥有过去想象不到的好友数量,但是比起“可能”拥有的最大数量的连接,仍然微不足道——美国成年脸书用户平均拥有334位好友,但是比起潜在的链接总量(7.4亿),连百万分之一都没有实现。网络用最简洁节能的联通方式,建立了效率最大化的信息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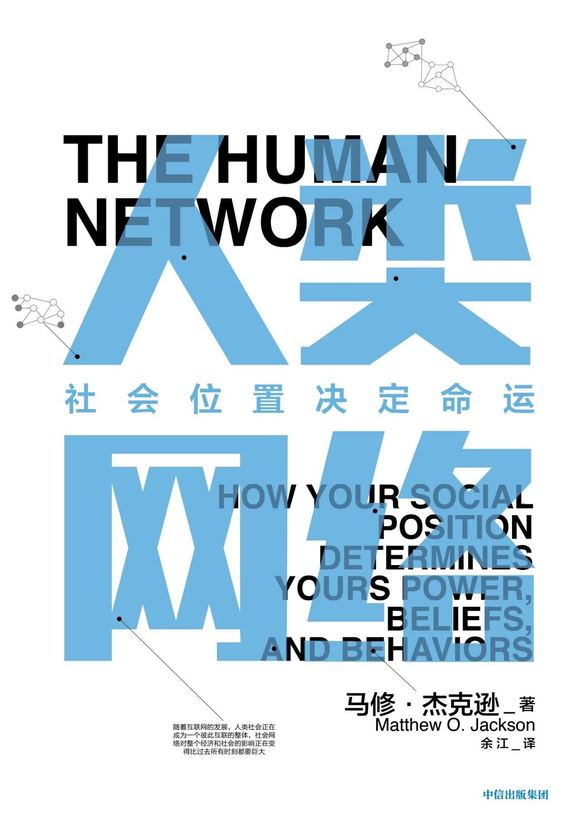
“小世界”让“宅生存”得到了现实基础,一个人或许无法象海德格尔理想中那样诗意地栖居,却可以既紧密又疏离地悬浮在社会的潮水之中,最少地保留外界连结与社会关系,依然拥有完整的社会单位功能,被系统容纳其中。这种反乌托邦小说情节一般的描述,却恰恰是今天无数青年上班族、各种“漂族”的日常。“遍历性”(即游遍网络联通节点)成了一种既麻烦又奢侈的社交负担,被扬弃在旅行时高铁飞速掠过的中间小站,和逢年过节回乡时被迫应付七大姑八大姨的抱怨中。
人类网络在金融危机的传播中却显示出了另一种面目,“小世界”在这里有了变形,因为金融网络的特点,节点之间连接数量(稠密性)与系统风险呈现高度非线性特征。金融市场联系非常稀疏的时候,虽然系统性总风险较小,但是无法分散个别风险,会造成投资直接损失的高概率;而在联系逐渐稠密的阶段,对个体风险分散的好处超过了风险传染的劣势,系统的安全性在上升;但网络连结的稠密度过大,金融节点之间的风险敞口过于重合,又会引发指数爆炸般的系统风险升高。复杂网络的不可预测性,使各阶段之间的临界值——受到即使微小的初始冲击——都会发生巨大波动。
新世代异性恋爱关系中的一句著名的沮丧之辞是:如果没有性吸引,男孩(女孩)更喜欢跟男孩(女孩)一起玩!其实这句描述背后有着坚实的数据支持。人口学家维尔布鲁格对美国和德国的调查结果显示,68%的成年女性的好友是女性,而男性的数字则达到了90%;不只是性别,年龄、肤色、教育水平、职业都在人际关系中强烈地表现出了同质性,甚至体重也是一样。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人与人的体重差异每缩小7.5公斤,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概率就相应提高三倍!
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在对合作与冲突博弈的研究中发现,同质化与隔离现象可以肇始于非常微小的初始变化,也就是即使博弈者对多元化并不反感,仍然会因为外部微不足道的冲击——比如一家熟悉的邻居搬走——被放大与加速之后,最终选择同质化的选项。
但如果你觉得多元化消失就能带来稳定性,那又大错特错了。当多元化消失到一定程度,原本稳定的同质联盟中又会由小冲击而出现新的分裂,产生新的“我们”和“他者”,这个无限可分的游戏不断迭代下去,是促使社会网络连结产生和消失的动力。

极端化是与同质性和“小世界”相伴而来的一种动态结果,如果只要通过寥寥几个中间节点就可以把意见传遍整个网络,那么初始信息节点的位置和权重就非常重要。“集体智慧”被认为是大数据理论的重要实践基础,它是一种简洁的理念形成、学习与传播的模型,基本观点是在传播中上一个节点发出的信息,乃是之前遍历的节点信心的均值——比如估计一件古董的价格,第二个人听到第一个人的估计数字之后,往往会对自己的估计做一个平均化的调整,在信息传播到足够多的节点之后,基本可以认为真实数字是所有人估价的平均值。这种简单而优美的学习路径,被认为比很多复杂的行为模型有更好的预测性。
但是平均化的学习模型也有致命的弱点,可能让“集体智慧”变成“集体愚蠢”。首先平均化计算中会有巨大的“回声效应”,你的观点通过反射回到自己这里,你的朋友传回来的观点中含有你自己平均进去的部分,势必更加靠近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正反馈,加强自己的信念。因而过滤掉自己的回声非常困难,尤其是起始位置中心度高、特征向量权重大的节点,很快就会被自身的大音量回声包围,形成一个意见的“漏斗黑域”,这也是位高权重者很少能够听得进反对意见、往往一意孤行的形成机制。
另一个偏差是“重复计算”,也就是看似独立的网络节点,因为“小世界”效应,很可能很快已经受到同一个初始信息源的“污染”,然后它们再进行平均,上一个节点的信息就被重复计算了。“集体愚蠢”的后果都是某一种意见会被不断加强,不断极端化,最后被几个节点“超级代表”,留下沉默的大多数无能为力。
技术进步给人类网络连结增加了复杂度,全球化是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它不仅让世界变得更小、地球变得更平,还让外部冲击更加不可预测,个人建立人际联系的激励与社会的最优选择之间存在更为普遍的矛盾。2016年之前,很少人想象得到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欧洲的难民政策安排、宗教冲突也和曾经深入人心的多元化与自由主义观念引发了现实冲突。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国际贸易以指数的速度增长,不仅带来了复兴与繁荣,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联系与国家联盟的数量和稳固性,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贸易联系的增加,使条约寿命变长,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变得深刻而稳定,特别是与19世纪的世界——拿破仑战争之后翻云覆雨的各类短命政治同盟和条约——相比,今天的世界因为网络更为稠密,联系更为复杂,而实现了更好的风险分散,即使在极端条件下(比如冷战),节点联系的多样化仍然有效牵制了灾难性后果的发展。
技术将继续进步,而网络的同质性、极端化、聚合性也仍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破坏,但是不断强化的经济和文化连结是需要正视和深刻理解的现实,而不是撕裂与孤立的理由,因为,后者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与观念之网中仅仅是自大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