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小说反映的是极端现实,还是仅仅是一种刺激?且看柳原汉雅、蕾拉·斯利玛尼等作家怎么说。

克里斯蒂安·贝尔为其2000年主演电影《美国精神病人》拍摄的海报。(图片来源:Sportsphoto Ltd./Allstar)
在《美国精神病》出版之前,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就已经收到了13次死亡威胁,那是在1991年。最后他不得不签署一份声明,证明自己已经知悉所有死亡威胁信的内容,如果真的惨遭毒手,埃利斯的父母不得起诉出版社。“我现在再也没有写这本书的冲动了,”近日埃利斯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它属于特定的时空……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我孤立无援,必须独闯火线。”
《美国精神病》原定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临阵退缩,理由是与埃利斯“在评论家所言之暴力和厌女的内容上存在审美差异”。此外,该书还一度遭遇美国全国女性组织抵制,授权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过书籍的所有作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其出版。“这不是艺术。”美国全国女性组织洛杉矶分会会长塔米·布鲁斯直言,“埃利斯是一个充满困惑而又病态的年轻人,他内心对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女性深恶痛疾。”最后,该书由企鹅兰登Vintage出版社接手出版。
当时埃利斯对此处境感到茫然,但并无愧疚之念。他认为,在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电影《美国精神病》(2000)中,暴力情节明显被夸大演绎,故不值得上纲上线,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不足为惧。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埃利斯坦言:“我写小说不是为了得到赞美,也不是为读者而写。我只为自己写作,我心底有感兴趣的物事,我便会通过写作呈现。”也就是说,写作不需要理由。《美国精神病》写的是一个男人将一个个女人折磨致死的故事,对埃利斯来说,他只是凭感觉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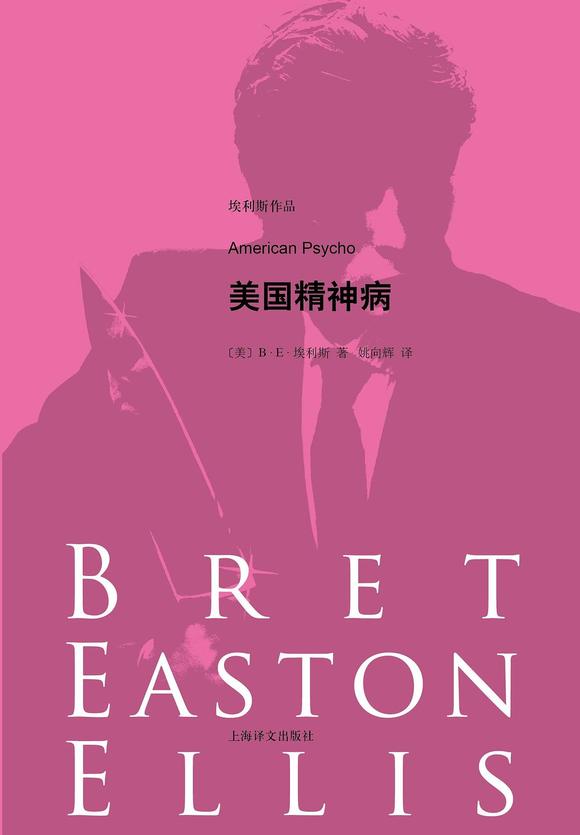
“极端生活无处不在,小说必须如实反映。”——柳原汉雅
回望从前,《美国精神病》似乎是一个小说时代的终结,或许还得加上米歇尔·维勒贝克1998年出版的小说《基本粒子》。过去百余年间,写下伟大小说的作家难说不希望带给早期读者一声惊雷,个中佼佼者包括《简·爱》《包法利夫人》《无名的裘德》《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波特诺伊的怨诉》。就像《美国精神病》一样,这些书很大一部分都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出版过程,但这对销量来说往往又不无裨益。要是一本书因为过于让人惊骇而无法出版,大家自然特别渴望一探究竟。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出版过14部俄文和英文小说,但仍籍籍无名。直到把《洛丽塔》的版权卖给一位巴黎色情作品发行人后,他才开始声名鹊起。但如今,成名之路已经关闭。凯西·阿克、达瑞斯·詹姆斯、丹尼斯·库柏、斯图尔特·霍姆等1990年代最叛逆的小说家现在基本上已经鲜为人知。“我无法想象现在出版《美国精神病》会是什么样子,”埃利斯说,“会有人感兴趣吗?我是不是得在网页的一些奇怪边角位处自行发表试读?”
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些年的小说变得平和了,也不能说令人震惊的小说受到了忽视。在艾米尔·麦克布莱德的《女孩是件半成品》(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萨利·鲁尼的《普通人》(Normal People)、蕾拉·斯利玛尼的《食人魔花园》、克莉丝汀·罗佩尼安的《心知肚明》(You Know You Want This)、希拉·海蒂《何以为人》(How Should a Person Be)、梅利特· 提尔斯的《回心转意》(Love Me Back)等书中,女主常通过暴力或纵情声色自我排解。而在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加布里埃尔·塔伦特的《窒爱》、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女孩是件半成品》、柳原汉雅的《渺小一生》、奥戴莎·莫思斐的《消失的囚徒》、尼尔·穆克吉《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等书中,强暴、虐待甚至谋害儿童的情节均有所体现。要想在过去十年的小说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和畅销书排行榜上应有尽有,没有一部是因为陷入丑闻而出名的。在英国电影领域,许多包含性暴力的场景可能是违法的(相关法律较为复杂,是否违法将取决于电影场景是否“完全或主要为了引起性欲”而拍摄)。
如果说《洛丽塔》是一部描画少女遭摧残的惊骇之作,《渺小一生》和《我的挚爱》的笔触明明更为直白残忍,为何却大失其惊骇之效呢?显然,1955年以来,时代已经不同,而小说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我写作的目的从来不曾,也从来不会是为了震惊世人或者煽动争端,”柳原汉雅告诉我,“我一直认为,各种各样的生命都应该在小说中得到真实的呈现,包括充满暴力和痛苦的极端生活。极端生活无处不在,小说必须如实反映。”

在接受采访时,塔伦特谈起其小说《窒爱》的女主人公特特尔,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记录她的生活,让读者看看我们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就像我看到的那样,”他说,“真实、紧迫、让人难以忍受。”纳博科夫知道《洛丽塔》将震惊世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动笔写下了这个故事,因为他内心深处和埃利斯一样,渴求将故事诉诸笔端。而对于柳原汉雅和塔伦特来说,让读者感到震惊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希望书中故事对公众有警醒作用。不管怎样,读者们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小说,就像他们会被苦难回忆录深深吸引一样。读者们对虐童题材尤为感兴趣,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出版的最大趋势之一。总而言之,具有社会意义是这类书籍成功的一大要义所在。
“我讨厌‘看了会让人感觉良好的书’(feelgood books)这类标签。一本书的意义在于唤醒你,让你感觉自己还活着。”——蕾拉·斯利玛尼
“这类书籍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书里的事都是真的。”斯利玛尼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温柔之歌》讲述了一个保姆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杀害雇主家两个孩子之路的;她的另一部作品《食人魔花园》成书更早,描述了主人公阿黛尔陷入性瘾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人们震惊,”她说,“我只是想‘打扰’他们,让他们心里起点波澜。我认为文学是用来‘打扰’我们的。”对斯利玛尼而言,为了感觉舒坦而阅读一本小说几乎等同于不道德。她坦言:“我讨厌‘看了会让人感觉良好的书’(feelgood books)这类标签。一本书的意义在于唤醒你,让你感觉自己还活着,让你睁开双眼,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类。”
与《渺小一生》《消失的囚徒》一样,穆克吉的《他人的生活》同样入围了布克奖。这本书描画的场景包括虐待、嗜粪癖、强奸和谋杀儿童。在去年与柳原汉雅的一次谈话中,穆克吉发现不同作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包括他自己。“世界上有两类作家,”他说,“一类是认为自我是唯一真实主题的作家,另一类是认为只有自我之外的世界才值得书写的作家。换句话说,小说可以是镜子,也可以是窗户。”因此,本文提及的穆克吉、柳原汉雅和塔伦特或许可以归为窗户小说家(window novelist);埃利斯则是一位镜像小说家(mirror novelist)。在穆克吉看来,镜像小说占据了主流。
即便如此,一部小说的写作目的还是难以界定,毕竟作者笔下所写与读者感受之间存在一定偏差。提尔斯的作品《回心转意》中的女主人公玛丽是一位未成年妈妈,生活辗转于滥交、自残和吸毒之间。提尔斯自己也认同,这小说似乎不会像过去那样被人视为耻辱,但当我问到读者是否提及她的小说会让人精神崩溃时,她承认:“噢,确实会。”提尔斯曾担任德克萨斯州平等机会基金会(TEA Fund)执行董事三年,该基金会为需要堕胎者提供资金援助。提尔斯希望自己的小说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善的曙光,哪怕只有一点点。“但基金会设立的目的并非如此,”提尔斯补充道,“我觉得说清楚这点很重要,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有意识地将小说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听起来既枯燥又霸道。无论如何,提尔斯的真正目的出于自身。当谈及《回心转意》中有多少内容来自她自己的经历时,她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像柳原汉雅,反而更像埃利斯。她认为不需要过多在意读者阅读时是否感受到了痛苦,“作为苦难承受者,我对自己的过去足够忠诚,”她说,“我的苦难带有一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须经过记录才能成形。”
尽管斯利玛尼心中有社会使命感,但她写作的真正主题似乎也是自我。“文学没有禁忌,没有,”她说,“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可能这样表达自我。因为某些观点难以让人接受,大家可能会对我评头论足。事实上,当我写作时,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在自由里翱翔。我让书里的孩子身亡,这事不会让我震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解放,因为我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当我落笔描述孩子死亡这件事时,我有一种真实的感觉,那就是这事现在不可能发生。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已经写过感受过了。写作本身有点像一种宣泄。”

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当作者最初并无影响社会的意图时,小说最终是如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这也是众多小说的命运。读者、出版商和评论家可以从一堆书中挑出符合口味的内容,并分辨出热门写作趋势。如今,具有社会价值的极端素材极具市场,也许是因为读者想成为更好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艺术层面上充满好奇,也许他们想寻一个托辞享受性爱和暴力带来的快感,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做的那样。
如果你对人们为何精于找寻极端题材阅读存疑,想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吧。如今我们知道适度自慰是无害的,但是那些坚信自慰有害健康的人有绝佳的理由禁止色情书籍流通。当然,出于现实需要,有时我们必须在医学文件或法律报告之类的文档中记录“性”。因此,立法者试图在允许明智、博学的人(实际上这群人都极为富有)阅读任何他们想读的书的同时,保护那些自控能力弱的人的健康。这个目的并不容易达成。对于一个人生选择寥寥、前路不明、意志薄弱的人来说,任何物事都很有可能令其纵情声色玩物丧志。这同时催生了一部分隐晦的色情作品,这些作品以高尚目的为借口,暗暗印刷挑逗性内容。1868年,广受欢迎的《忏悔录揭秘》(The Confessional Unmasked)被禁,原因是读者阅读动机更大程度上出于寻求娱乐而非精神救赎。该书记录了女性在告解室向天主教牧师忏悔时牧师的问话,可疑地过分透露了淫秽细节。
随后,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令》允许律师为“无知传播”(innocent dissemination)辩护,并增加了一项新规定,如某部色情小说能为公众带来益处,那么它可以正常出版流通。例如某部色情作品属于艺术作品之列,则可免于被禁命运。一年后,企鹅兰登引述此条例重新争取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权,此书才重见天日。
暴力场景确实很受欢迎,即使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极端的恶——出版商深知这一点。
小说中的惊骇内容在实践、艺术和社会层面上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如何取舍显然仍需进一步斟酌。大部分人不会愿意承认这些内容是正常的、无害的,更羞于承认他们好于此道。企鹅兰登书屋在其为《地下铁道》所写的高中生研读指南中警告教师,他们的学生(16-18岁)将在书中看到“大量的暴力场面(包括性暴力和身体暴力)”。但该指南补充称,教师“不应该将学生和暴力场景隔绝。相反,教师应该指引学生进行讨论和批判性分析,加深他们对许多遭受奴役者的命运的认识”。
这指引确有现实意义,但将其作为警告看待又有些奇怪。描写性暴力和身体暴力的场景确实很受欢迎,即使是——也许是尤其是——当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极端的恶时。如果你不相信,尽可以看看报纸报道、战争片、苦难回忆录、电子游戏、连环杀手纪录片、《权力的游戏》……
这不正是大多数出版商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吗?在我为《消失的囚徒》写的书评中,我不遗余力地使用“肮脏的”“丑陋的”“令人震惊的”“无情的”“令人心神不宁的”和“令人不安的”等词来吸引读者。而在我自己的书《两厢情愿》(Consent)中,我同样力陈这书是“令人心神不宁的”“令人恐慌的”“恶心的”和“令人震惊的”。访问企鹅兰登书屋网站的另一个页面时,你会发现有人评论《地下铁道》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这评价可谓是至高无上的赞美。犯罪小说或情色小说的受众非常清楚,他们花钱阅读是为了得到快感。也许对沉迷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读者群体而言,他们倒愿意花钱自我隔离。
本文作者Leo Benedictus是一位自由撰稿人,著有小说《余兴派对》。
(翻译:刘其瑜)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