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死亡是生命的倒影。

记者 |
清晨八点,当《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声回荡在长沙雨季潮湿的空气中,明阳山殡仪馆二层最常见的一间悼念厅,姜书远(化名)的葬礼正准备开始。二十分钟后,由司仪的带领,人群缓缓向厅内移动,本也不算狭窄的空间勉强能容下这些前来看他最后一眼的同学与老师。如果你此时越过人群瞟上一眼,彩色遗像上,姜书远正穿着学士服微笑,与那些前来悼念他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并无差异。
按照流程,追悼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姜书远的遗体将由升降机从地下运送至悼念厅的玻璃棺内。很难想象,一天前,姜书远还不是这个模样。意外去世的他被送往位于明阳山殡仪馆半地下室的装殓班,因遗体受损较为严重,需要进行特整。用一种遇到液体可以黏贴得更加牢固的塑泥,塌陷的头骨和面部被撑起,随后是如外科手术一样的缝合。再之后,身体和头发被彻底清洗,穿上红色唐装,化妆。数小时后,姜书远看上去已经和这里躺着的其他正常死亡的遗体无异,只是也许更年轻,也因此更令人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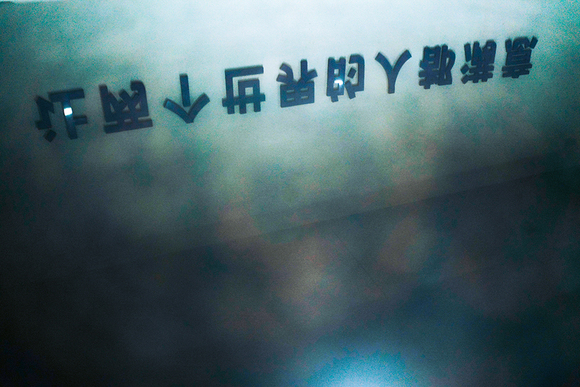
在明阳山殡仪馆,这样受损严重的遗体每一、两天就会送来一具。即便是不需要进行特整的遗体,平均下来,每天也有超过60具。他们有些是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有些被要求直接火化,剩下的一些,则经过一整道“工序”,穿衣、化妆、遗体告别,最终被推向火化车间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
“长沙个变态的天气!”
一间能容纳几十人的教室最后一排,仍可听见王丹丹不用话筒就高达九十分贝的声音。四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正进行一堂有关遗体防腐的专业课程,而王丹丹正皱着眉头,扬着脑袋,“咒骂”着长沙潮湿多雨的气候——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几乎是罗布泊地区的35倍。后者,是著名古尸楼兰女尸的发现地。
关于王丹丹第一次看到遗体的故事,她已经跟人讲了无数次。这一天,王丹丹又一次把当时的照片打在比她高出几头的投影屏幕上,试图回忆当时的情景。
“实习第一天,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一间超大的房间里巡查,房间里停放了我数不清是几百具的遗体,我的工作就是检查他们是否有腐败的迹象,当然打苍蝇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王丹丹所形容的“超大房间”,实际上是上海龙华殡仪馆一个恒温在21℃至22℃的房间。与明阳山殡仪馆不同,龙华殡仪馆采取的多是防腐剂防腐的方式,因此尸体全部停放于室内。“我的胆儿就是从这里练出来的。”实习过后,十九岁的王丹丹得到了明阳山殡仪馆遗体整容师的工作。

时间总是模糊的。中午十二点和午夜十二点,对于王丹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并没有太大分别。本着“人尸分流”的原则,装殓部的工作区域在半地下室。没有阳光直射的整容化妆室,让白天与夜晚只能靠墙上的钟表分辨。虽然同事们觉得她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但在王丹丹的形容里,走出半地下室的那一刻,“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殡仪馆的任务多时,王丹丹需要凌晨四点就从家里出发,开车半小时到殡仪馆开工。大概每一周的时间,她需要值一个通宵的班,和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轮流在员工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但通常“还是能听到‘哐当哐当’运送遗体的车的声音”。她很难闲下来——在与上午相比化妆任务较少的下午和晚上,她要么在地下室入口处的编码室等待遗体,要么在休息区域打扫卫生,偶尔还会接到一些外派任务。这些时候,地下室到处都能听到她洪亮的嗓音。哪怕在夜班的休息时间,她也宁可开着灯睡觉,这让在补充四个小时睡眠之后的起床不会那么吃力,会“警醒自己”。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十四个人的装殓部有五位女性,只有“丹哥”的称呼被叫得最为响亮。在同事眼里,她“不像个女人,就是个男人”,而这并不只因她利落的短发,以及平时不化妆的习惯——酒桌上,一口一杯,王丹丹最爱的是炽烈的白酒;面对熟悉的人,她的急脾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谁都知道那是她的个性,其中包裹着出人意料的细腻心思。
“雷厉风行”,同事舒登高这样形容她的工作风格。也因此大家各取所长,例如王丹丹“缝合做得厉害一些”,而像同班组的舒登高和周哲,更愿意做花费时间的“细活儿”。
有时,对王丹丹来说,性别分界是模糊的。或者说,女性的性别概念在她的身上得以重塑。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遗体整容工作,让她自入行就时不时受到质疑——时光倒回十几年前,那个从落后的内蒙古故乡坐火车来到长沙的十几岁小姑娘,回答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带着长沙口音的问话时,还略显莽撞与生涩,却已颇具胆量。
“你这么瘦,以后能不能抬得动遗体哦?”
“行不行,做了再看。”

打出租车去明阳山殡仪馆时,“到了门口我不进去喔!”这样的话时常从司机口中冒出。甚至,只有少数司机愿意载客到这样的目的地。“这跟小时候村子里死了人,父母不让你进去是一样的道理。”一位不得不拉活儿去殡仪馆的司机一边抱怨一边这样解释。因与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深深联系在一起,殡仪馆是一个许多人忌讳踏入的区域,甚至,人们忌讳谈论它。
很少有人真正没有芥蒂地踏入殡仪馆。连带着,很少有人可以正视殡仪行业的从业者。就像遗体整容师们往往无缘见到逝者家属看到遗体的表情,悲痛中的家属也很难想到和这些隐藏在半地下室中的工作者们打一个照面。殡仪行业所带来的神秘感,多半与从业者幕后工作的性质有关。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死亡被比喻成一道门,入殓师作为“看门人”,目送着逝者穿过它,走向每个人注定的下一程。对于王丹丹与她的同事们来说,这道“门”虽在传统意义上将“阴”“阳”分隔,却剥离了抽象的含义,呈现得十分具体、赤裸和真实。“生前的痕迹,在死后的脸上显露无疑。”不同的死因与死前被对待的方式,造就了每一具遗体的不同容貌。针对这些特质,每一位遗体整容师在化妆时也带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例如针对有些老人的嘴部需不需要填充的问题,有些整容师可能认为她戴着假牙时嘴部是丰满的,还有一些会认为本来老人家的牙口就有一些凹陷。”
对于王丹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与标准操作相比,遗体整容化妆的方法会根据长沙本地的气候和环境等作出调整,例如传统的粉妆被调整为油粉结合的方式。而他们的另一层“标准”,则针对社会上那些与他们有着竞争关系,却有时并不专业,偶尔又缺少职业道德的殡葬服务机构——这些遗体整容师们要试图做得更为专业,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做也许也能打破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流言蜚语。
有时候,也并非只是这些机构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我不认为手工会过时。也许大框架的制作流水线等操作会被机械化所代替,但温情化的服务离不开人。”王丹丹对于手工作业的肯定,几乎是面对新技术的“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国内不少殡仪馆开始尝试3D打印技术,来用更精确的技术手段实现残损遗体的修复。虽然高昂的成本,让这样的方式还未被大面积普及,但手工作业的极限,似乎在新技术的发展中渐渐被提出,被质疑。

而不会变化的是道德的界线。这一点,在王丹丹看来,是十分清晰和坚定的。“为什么要给遗体防腐?人的形体发生了变化....家人的告别就没有了条件。......防腐是一种保存的概念。”在给殡仪学院的学生上课时,她反复强调的自己的工作原则中,就提到防腐行为合理的前提,是它的目的性,例如为了在追悼会上让生者见上最后一面,或是长途运输的需要,以及医学院对于教学样本的需求。
“无论化妆还是防腐,接触遗体必须坚守的是良心。”接着,“必须”又被她强调了一遍。
这样的信念,在十年前,甚至足够支撑王丹丹在工作中不小心被针扎到,都不在乎是否去医院打破伤风针。像她自己骄傲地说的,“十年前的丹哥不怕死”。同样,也是这样的信念使她做了七年公务员后又甘愿回到现在的岗位。对于现在新一代殡仪专业的学生,王丹丹更愿意形容他们拥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心态”——工作与自我的界线变得更为清晰,“更别提为了工作奉献生命了”。












只需在明阳山殡仪馆呆上几天,便可目睹无数场生离死别。发生的地点,对于装殓部来说,大多是编码室的玻璃门外。所有遗体都运送至此进行编码和登记,再经由一条弯曲的走廊,被运送至特定的工作区域。因各种原因死亡的遗体在此聚集——病故、意外、坠楼……在这些也许不愿却不得不死去的人们之外,也包括自杀和互相残杀。脱下送来时穿的衣服,你很难识别他们生前的身份与社会地位,而这些,在这里,也不再重要。
对于许多家属来说,那条绘制着蓝天与山景的走廊入口,就是他们与亲人或朋友最后分别的地方。生者只好被挡在这条看不见出口的通道之外。另一些亲属,则不得不更进一步,也更残忍地,来到专门冷藏腐尸的冰柜区域认领无名遗体。


殡仪馆是许多人的一堂课。在巨大的悲痛中,包括一小部分为了不知什么原因所“表演”出来的悲痛中,他人的死亡逼近,也似乎暗示着每个人都必将面临的结局。这结局并不只是死亡带来的沉默,它像一面镜子,总是能映射出关于“生”的影子。
王丹丹曾拒绝过一个任务。那是一单“价值不菲”的活儿,家属希望她用她能达到的最精湛的防腐技术,将一位死者的遗体保存至他的子孙后代都可以瞻仰的时间长度。家人抗拒自然力量的愿望,似乎超出了王丹丹所做工作的范围。而她拒绝的最直接理由,则是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职业原则。另外,这样的防腐项目需要她不停回去维护遗体,换句话说,她“不会成为他们的‘守陵人’”。
另一次,装殓部收到一具遗体,是一个还未结婚的四十三岁女人。家属为了实现她的愿望,让她穿上了玫瑰红色的纱状衣服,又化上了新娘妆。追悼厅被布置成婚礼现场,布满紫色的气球与红色的玫瑰花。这场十分个性化的葬礼,让工作人员们都记忆深刻。
由死看向生,对于平常人来说,除了悲痛,恐惧有时带来警示的作用。对于王丹丹与她的同事们来说,上班时一天经手数十位逝者是常事,他们选择用专业来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当然还有胆量,以及不断自我说服、自我修复的能力”。在他们的双手触摸之下,无论逝者生前经历过什么,都最终以体面而有尊严的样貌重新示人,告别世界。就像王丹丹所说,“尤其是见到意外过世的人,我会印象极其深刻。会感到活着很好,活着是幸运,好好珍惜生命和当下很重要”。
没有人能够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样子。但若你问王丹丹她是否想过自己死后的样子,她会用混杂着长沙话与东北话的口音,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没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和这些躺着的人一样吧”。但如果让她想象自己葬礼的样子,她会说,“希望少点悲痛,温情、淡然的气氛就好”。










※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乙未光画志”(ID:JMmoment)和界面影像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