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与大男子主义根植在爱荷华作家工坊的文化与历史中。

20世纪50年代,诗人保罗·恩格尔和一群学生在一起,他后来接任爱荷华作家工坊的管理工作。图片来源:The New Republic/Frederick W. Kent Collection/The U
2016年3月,文学组织VIDA公布了十几名女性的匿名声明,指控美国诗人托马斯·塞耶斯·埃利斯(Thomas Sayers Ellis)的不正当性行为。这些声明称,在过去数年中,埃利斯强迫性的挑逗、嘲弄、身体暴力和威胁几乎毁掉了她们的职业生涯。当时52岁的托马斯·埃利斯在文学领域广受尊敬,同年1月被聘请为爱荷华创意写作工坊(Iowa Writers’ Workshop,即爱荷华大学文学创作专业)的客座教授。在VIDA公布这些声明不久后,埃利斯的课程就被取消了,一名大学职员证实他们正在“调查情况”。如今这起案件已经广为人知,既有多重指控,也有网络声援,还有对于权力结构导致的权力滥用和禁止明确表达同情的批评——这一活动被称为“反性骚扰运动”。
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在关于埃利斯一案的报道中写道,“在创意写作领域里,掌权男性的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是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爱荷华创意写作工坊,那是美国最负盛名的MFA(艺术创作硕士)项目。作为美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该工坊只接受一小部分申请者(2016年约3.7%),并承诺给予高额奖学金。工坊的教师帮助学生与编辑建立联系,著名的客座作家介绍学生进入文学圈子,使得该项目培育了许多优秀作家。18名工坊的毕业生获得了普利策奖,还有数千名毕业生出版了著作,他们常常受到评论界的称赞,工坊的教师同样也很出色。
但是,这些出色的教师中,也不乏一些人骚扰、恐吓和戏弄他人。托伦蒂诺的报道表示,爱荷华的学生对于埃利斯被指控的这些行为同样感到颇为苦恼,这件事让人想起多年以来工坊里其他的老师和诗人。在工坊83年的历史中就有这样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工坊教师、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就曾告诫新来的老师不要引诱本科生,但是他暗示研究生可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承认“作弄过学生的衣服”。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曾在参加派对的路上,在汽车后座上摸了一个学生,当她试图拒绝的时候贝里曼便退缩了(“什么?你的意思是不上床?”)。他们常常为了一个女人不惜百般引诱、情色交易,乃至醉酒斗殴。“那些老师整天乱搞,” 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谈到她上世纪70年代末在那里的经历时说,“他们似乎觉得免费的马子是应得的报酬。”
大卫·道林(David O. Dowling)在他的新书《微妙的侵犯:爱荷华作家工坊的野蛮和生存》(A Delicate Aggression: Savagery and Survival in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中明确表示,揭露性别歧视并不是这本书的目的,用序言里的话来说,该书通过讲述当代重要作家的职业生涯(从爱荷华工坊成立之初到如今,这些作家在众多杰出的导师的指导下学习或授课),从而考察“爱荷华作家工坊对文学和出版业的影响”。毋庸置疑,其影响相当深远:道林通过书中15篇简短的传记,记述了这些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作家是如何制造了这一制度环境,并且是如何为这种制度环境所影响的。他也描绘了自1940年以来,工坊和出版业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纽约时报》上如此多的书评获得了爱荷华的认可绝非偶然。1941年,诗人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接任工坊的管理工作,他相当强调发展专业素养。在掌舵的二十多年里,他孜孜不倦地为学生和整个项目争取奖学金和企业赞助。爱荷华作家工坊的学生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出版书籍。道林对恩格尔领导下产生的矛盾很感兴趣,并以此追溯工坊后来的几十年:创作是如何能既具开创性又受人欢迎呢?严苛的制度会扼杀创新吗?怎样才能像恩格尔所希望的那样,既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一个“商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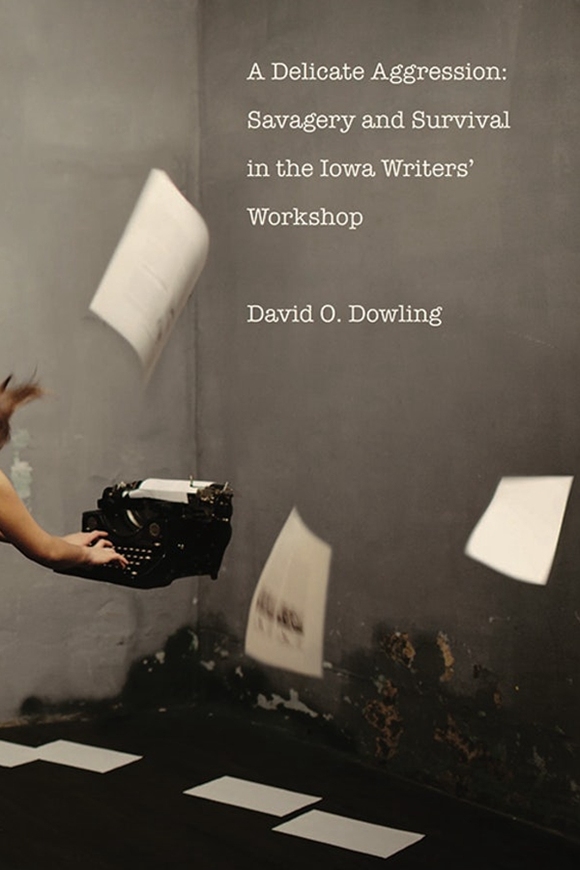
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戴维·迈尔斯(D.G. Myers)、马克·麦古尔(Mark McGurl)和埃里克·本尼特(Eric Bennett)等学者巧妙地解决了。但道林的书有其重要性和创新性,书中详细记述了性别歧视给爱荷华作家工坊带来的影响。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发现了一些描述不当性行为的信件、采访和回忆录,因此书里有很多脚注(大卫·道林是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从事引文研究的学术实践)。他的书充分展示了存在于制度环境中的性别歧视,而不是聚焦在零星的性骚扰事件上:性别歧视根植在爱荷华作家工坊的文化与历史中。书中讲述了诸如拳击比赛的趣闻轶事、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暴跳如雷,以及参加研讨会的同时还要养育两个孩子的艰辛母亲。他还讲述了女性作家之间互帮互助,蔑视男性权威,以及她们后来成立的与爱荷华截然不同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似乎有很多野蛮的地方,但与之相对应地产生了崭新的抵抗形式和生存之道。
书里有很多令人唏嘘的年长男性作家,但书的第一章聚焦于一个女人: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她是工坊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奥康纳当时是乔治亚州米利奇维尔的一名大学毕业生,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1945年被录取,成为工坊的一名学生。在满是退役士兵的教室里,她是一个“聪明的不合群者”。一位同学回忆,他们是“一群生活艰难,却相当放荡的人”。奥康纳一开始不敢在课堂上朗读她的作品,经常让男同学代她朗读,后来当她大声朗读她的第一部小说《智血》时,恩格尔被她对性诱惑的描述震惊了。为了纠正他认为的不合理之处——他称之为“可爱的无知”,恩格尔把她叫到办公室,然后建议到他的车里去,在那里她可能会更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性经验。奥康纳和他一起去了,但她对自己的性生活只字未提,也没有修改自己的小说。后来,她三次赢得欧·亨利文学奖,并在197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矛盾的是,爱荷华作家工坊作为一个旨在激发创造力的文学机构,早年间却充满了尚武的精神。当时的教室设立在军营中,恩格尔在打字机旁放了一根鞭子,扮演军士教练员。他鼓励学生互相严厉地批评,希望他们能变得有韧性,变得坚强,好似工坊的课程就是军队里的基训。道林解释道:“恩格尔通过建立共同的敌人,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出版业大批潜在的敌对评论家和编辑,这一举动源于冷战思维。” 文化是冷战时期的一种武器,恩格尔也在为冷战做准备。奥康纳并不反对她“前导师”的教学方法。“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大学是否扼杀了作家,”她曾说,“我觉得,他们扼杀的反而不够多。”
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其他地区一样,爱荷华作家工坊进入了道林所说的“水瓶宫时代”,一个社会革命运动伴随着性解放和毒品泛滥的时代。更多的有色人种作家来到爱荷华,包括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乔伊·哈霍(Joy Harjo)、丽达·多维(Rita Dove)等女性学生。这个曾经禁止学生留长发的地方——恩格尔说长发太过浪漫,他要求学生“剃发明志以保持专业素养”——现在却录取了诸如T.C·博伊尔(T.C. Boyle)这样的学生。博伊尔自称“嬉皮士中的嬉皮士,道德败坏之极”。虽然仍有老兵书写他们的战争经历(这次是越战),但同时还有其他学生写下了搭便车旅行和吸食海洛因的故事。

未曾改变的是爱荷华工坊的教室、餐馆和酒吧里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简·斯迈利(Jane Smiley)回忆道:
老师们往往是有一定年纪的男性,他们认为竞争很关键,也就是所谓的诺曼·梅勒时期。据说如果你不同意诺曼的意见,或者给了他差评,他会气得朝你鼻子来一拳,你们也许就会因此在餐馆打起来了。
这种事可没少发生。道林在书的开篇讲述了1954年贝里曼和他的学生、未来的桂冠诗人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酒后斗殴的轶事。显然,“莱文用重拳与他的导师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后来,他讲述了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在访问爱荷华市时,如何与一名女子发生争执,并写出一名老师所谓的“最优雅地串联在一起的猥亵片段”。道林称之为“最好的亵渎诗歌,最糟糕的是充满酒臭味和对于女性的厌恶”(托马斯写的第一句就是“你这他妈该死的婊子!” )。约翰·艾文(John Irving)开始是工坊的学生,后来成为了老师,他曾经试图用摔跤解决在爱荷华台球场的学生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工坊颇为盛行:究竟是拳击强,还是摔跤强?有一段时间,拳击占了上风,以至于有学生觉得每周都应该办场拳击比赛——“至少对男人来说应该如此”。后来,一位准作家用“海明威式” 来形容一位的同学的拳头(诸如“这是一记不错的重拳,一记坦直的重拳,一记讲述你自己故事的纯粹重拳”等等)。正如道林所说,“梅勒、拳击和豪饮都是工坊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气背后隐藏着高人一等和不断的挑战、嘲弄与自我扩张的精神。”
这种“大男子主义”感染了整个教室的氛围。严厉的批评一直是工坊教学的核心。恩格尔认为“年轻作家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创作能力,只有严厉的批评才能让他们清醒地认识自己”。 希斯内罗丝对此说得比较简单:“没有爱。”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描述了学生撕毁正在创作的作品时是如何“互相攻击”的。赞美从来都不公正,而是处处充满偏颇的。当像博伊尔这样的男学生和他们的导师在校外喝酒的时候,“为了测试女学生的意志,她们反而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这一过程被合理化成为一种教学法。”她们面临着一项很多女性都相当熟悉的测试:证明自己足够坚强,能够成为男人中的一员。
当然,女学生还有第二个选择:引起老师的性趣。据道林写道,一些女学生会有意识地讨好别人,利用自己的年轻美貌来得到学业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的天真烂漫吸引了年长男性作家,让他们觉得另有弦外之音。希斯内罗丝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受到了一个教授的特别关照,不久之后她就意识到“教授对我感兴趣是觉得我是个不错的作家”的想法太过天真了。她现在警告年轻女性,不要理睬任何来自有权势男人的主动示好。
就男性作家而言,他们把这种暧昧看作是一种恢复活力的邂逅,或者仅仅是应得的回报。冯内古特在一封信中写道:“女人能够让漂泊在外的男人重拾雄心和智慧,而我已经两次有此幸事……这两次,在和这些天使睡过之后,我又重新开始写作和作画。”他还写道,“贝洛(Bellow)和梅勒一次又一次以这种方式重拾自我,就像买新车一样。”(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学生比作消费品。)有传言说,女性申请者是看照片录取的。一位70年代参加过工坊的女学生把工坊的女性形容为“没有必要的装饰性花瓶,没什么用处”。
希斯内罗丝和哈霍对于工坊的文化氛围颇为失望,于是她们互帮互助,在情感上、物质上和创作上互相支持。希斯内罗丝帮哈霍照顾孩子,让她腾出时间写作。她还鼓励哈霍写诗,将作为一名艺术家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窘迫融入诗中。两个人开始在课前喝酒。有一次,她们向一位老师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让她们参加每周轮流的阅读会。“当他看到我们俩的时候,”哈霍说,“他开始后退,仿佛我们要拔出刀来,或者把他头皮剥下来一样。”在下一周的阅读会上,她们的诗就被拿来品评了。
还有其他一些女权的抵抗行为。比如,当斯迈利已经厌倦了再听一位“年长男性”的品头论足,便把一则正在创作的作品交给一位女性朋友。这位朋友在研讨会上读了这则作品,并给了斯迈利应该继续写下去的鼓励。希斯内罗丝不顾顾问唐纳德·贾斯蒂斯(Donald Justice)的反对,继而写出了《芒果街上的小屋》。20世纪70年代,作家工坊的女性们建立了一个名为“优雅与红宝石(Grace and Rubies)”的女性专属餐厅兼图书馆和聚会场所。博伊尔就此事写了一个讽刺故事,这则故事发表在《阁楼》(美国著名色情杂志)杂志上。到了1978年,当女性承受着让男性进入她们专属场所的压力时,该场所便关闭了。慢慢地,经过不懈地努力,作家工坊变成了一个更加多样化、更加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地方。

几年之后,希斯内罗丝回想起她在作家工坊的经历时说:“在爱荷华作家工坊的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不同。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能够把自己从一起学习的人和阅读的诗歌里抽离出来,发现真正的自我。不过这种体验并不愉快。” 现在她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她想创造一种协力合作的工坊体验,就像她的朋友哈霍曾经描绘的“餐桌社区”。 1995年,她创办了马孔多作家工坊(马孔多是《百年孤独》中描述的一座虚构城镇),她在餐桌旁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后来,成员起草了一份“富有同情心的行为准则”。希斯内罗丝认为,教师不应该是施虐狂,而应该关爱和支持自己的学生,作家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马孔多作家工坊是一个汇集了富有同情心、有雅量的作家的讲习班,这里的成员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带来更加美好的非暴力社会变革。换句话说,这与爱荷华作家工坊恰恰相反。”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同样有许多作家在爱荷华作家工坊的熏陶下转变了写作风格,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道林的书中有很多作家对爱荷华作家工坊对于职业生涯的影响做出了积极回应,这些作家包括工坊的老师和学生,比如W·D·斯诺德格拉斯(W.D. Snodgrass)、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和艾纳·马席斯(Ayana Mathis)等。他还指出,女性作家张岚(Lan Samantha Chang)从掌管工坊14年之久、严苛到从不妥协的弗兰克·康罗伊(Frank Conroy)手中接任工坊,意味着一场“进步的文化接替”。道林认为,她的任命标志着“工坊里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表示了从1987年到2005年主持工作的康罗伊只是简单地延续了“恩格尔时代的父权统治”。 道林将张岚描述为一位“富有同情心”和“包容心”的领导者,在她的领导下,工坊招收了更多的有色人种学生。与早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爱荷华作家工坊和其他美国大学一样,已经明确实施了禁止性骚扰的政策,那里的老师也接受了相关培训。
爱荷华作家创意写作工坊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创意写作项目,也不是唯一一个深受性别歧视困扰的美国文学机构——正如近期的一些反性骚扰事件所展示的那样。《微妙的侵犯》一书汇集的经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爱荷华作家工坊的历史,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广泛地认识这一段文学史。在这段历史中,女性的声音被奚落、被忽视、被打压。像希斯内罗丝这样的故事只是那段历史的沧海一粟,有太多的性侵犯、大男子主义和对女性的歧视不为人所知。道林还表示,官方记录中仍有很多空白,因为弗兰克·康罗伊把他的档案封存到2024年。尽管道林拥有特殊权限,但是工坊的管理部门还是“决定从档案中删除一定数量的材料”。道林的书让你有机会了解那些90%的默默无闻没有成为作家的工坊学生,他们挫败的原因和他们本可以写的书。
作家兼评论家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那段沉默的文学史致哀:“致那些默默无闻、不甚光彩的米尔顿(Milton)们:那些醒着的时候都在为生存而挣扎的人;那些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些女人。”她的思绪触及的是那些从未有机会去过爱荷华作家工坊这种地方的人,更别说大学了。但当我读道林这本书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她为“未完成的作品”以及未曾有的创作而著的哀歌。《微妙的侵犯》是一段历史,也是纪念,它证明了女性的创作常常会被男性的成功所扼杀和牺牲。
本文作者玛吉·多尔蒂(Maggie Doherty)是哈佛大学的讲师,她即将出版的新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诞生之初时,一群女性艺术家之间智慧和友谊。
(翻译:张海宁)
……………………
|ᐕ)⁾⁾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