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物身体不只是暴力承受者创伤书写的方式,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共同现实。毒物不只存在于被资本与权力所抛弃和排斥的废弃之地、边缘之地,它可能弥散于任何地方。

撰文 | 卢浩菊
编辑 | 黄月
3月下旬,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在事故搜救基本结束后,搜救工作人员和媒体撤离现场,响水似乎回归了寂静。环境灾难事故往往在基本工作结束之后就消失于大众的视野,很快被抛诸脑后。然而,无论是化工爆炸、石油废弃物泄露、洪水还是火灾,环境事件或许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奇观式的突发事故,事故释放的毒物或造成的灾难将生存其中的人们与其他生命卷入一场缓慢的浩劫之中,暴力以更为隐蔽、延缓的方式施展。生态批评学者罗伯·尼克森(Rob Nixon)在论著《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中提出了“慢暴力”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弥散于空间内部的、需要长时间累积才释放的伤害,而在崇尚壮观、追求瞬时的媒介文化和注意力稍纵即逝的时代,这样非即时非突然的伤害往往不被看见。在本文中,我们选取了几位不同国家的作家以不同方式书写的被毒物影响的身体与生命,试图揭开隐藏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毒物承受者的伤痛,从而指认毒物弥散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暴力。
在印度作家因德拉·辛哈创作的长篇小说《人们都叫我动物》里,叙述者是一位名叫“动物”的19岁男孩。印度考夫波尔城的美国企业康帕尼工厂发生毒气泄漏的那个晚上,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灾难事件让他成为了孤儿,也改变了他的身体形态:“六岁时,身体就开始疼了”,“剧痛扯着我的脖子,我只能低着头”,“我的背驼了,疼得我只能向前弓着身子”,“我的骨头已经扭曲得像个头发夹子一样,屁股成了全身最高的地方”。他只能依靠双手支撑拖着绵软无力的双腿匍匐前行,如同一只残疾的动物,终日生活于毒气发生后废弃的工厂里,与流浪狗嘉拉为伴,穿梭于街头小巷乞食或以垃圾为食。小说以“动物”的视角出发,讲述了遭受毒气泄漏的考夫波尔市民的悲惨境遇:在灾难事件发生的19年后,他们依旧无法脱离毒气带来的身体病痛与精神梦魇。
小说源自一起发生在印度的真实的工业污染事件: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杀虫剂原料厂发生氰化物毒气泄漏,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去,近20万人流离失所,至今依旧有数十万居民遭受毒气的后遗残害。时隔20年,辛哈以此为背景撰写了小说《人们都叫我动物》,获得了2007年曼布克奖决选提名及2008年英联邦作家奖。《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这部小说“以滑稽、粗鄙的叙述语言描绘了一座中毒、‘废弃’的城市”——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他描绘了无数被毒物渗透的残败的身体:修女玛·弗兰西丧失印地语能力,整日疯言疯语;阿丽亚的妈妈因为肺部糜烂多年后死去;吸进太多毒气的沙姆布老头浑身疼痛、呼吸困难;年轻母亲挤出的奶汁是带着红色、苦涩的有毒液体。小卖部老板细数街头邻里的病痛:街对面的子宫出血,癌症;路这边的脖子肿胀,胳膊抬不起;再过两家患了妇科病,疼得像死了孩子。伤痛与死亡成为考夫波尔城的街头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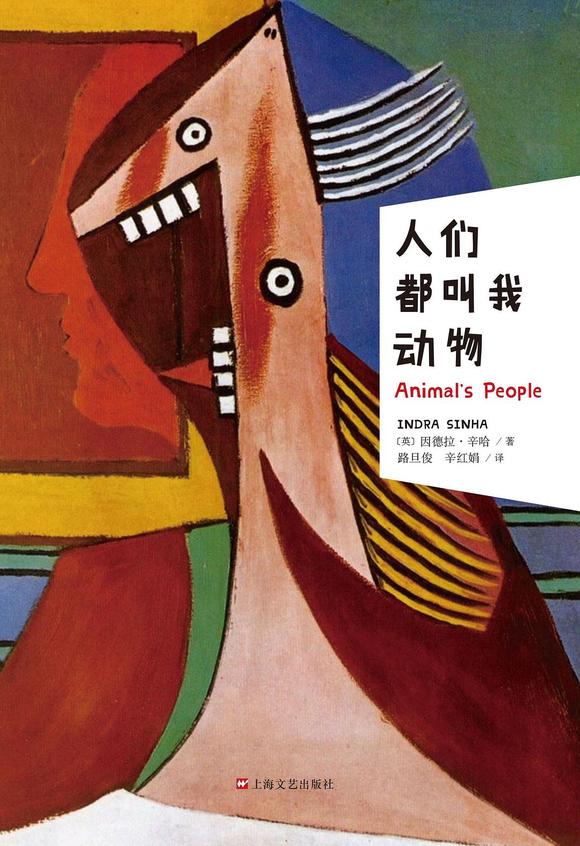
“动物”在医院目睹了被装在医学溶液瓶里的“毒气婴儿”,它们是事故发生的那个夜晚活下来的孕妇流产的婴儿,形态乖张丑陋,“小小的拳曲人瞪眼看着”,“双手向外伸张,一脸歹相”。小说的英文名字意为“动物的族群”(Animal's people)暗示着主人公“动物”被毒物侵害而扭曲变形的非人形态——如狗一般四肢爬行、忍受不堪与屈辱的生命经验并非其独有,而是考夫波尔城市民共同的生存处境。
事实上,毒物身体的描写在有关毒气、辐射、污染等环境灾难事件的作品中并不少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重访了核泄漏灾难的幸存者,尽管已过去10年,他们的身体依旧烙印着辐射导致的伤痛与病变。一位军人在身赴清理现场的三年之后病倒了,没能逃脱潜藏的辐射;他当年的同伴有人死了,还有人发疯自杀了。毒物渗透所带来的缓慢伤害不同于热兵器的战争——“我从阿富汗回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之后才把你杀死。”
暴露于辐射的身体同样会将这种生理的扭曲延续至后代,母亲生下死胎,刚出生的孩子形似“布袋”,甚至生成了“后切尔诺贝利的身体”:孩子无法排队等待十五分钟,他们会头晕流鼻血,他们总是疲惫又困倦,脸色灰白,他们不会玩耍嬉闹;年轻的生命突然死去,孩子上吊;切尔诺贝利人生下来的孩子身上流下的不是血,而是不知名的黄色液体。
以上两部虚构与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毒物身体”,向我们展示了工业毒物对生命漫长的腐蚀与浸透,可能蔓延至几代人。化工厂爆炸、核泄漏这类事件在媒体报道中往往被视为意外的、瞬时的重大事故,在事件平息后迅速消失于世人的视线之外,非即时性的、延缓的暴力则被忽视了。正如《慢暴力与穷人环境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内部,生态危机往往被指认为惊心动魄的“灾难片景象”与奇观式的突发事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态暴力是一种慢暴力:发生缓慢、被排斥于主流的视线之外,弥散于时间与空间内部的暴力,其破坏性后果是经过长时间累积而生成。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体系内部,可能有生命与环境威胁的化工污染行业往往从欧美转移至第三世界,从城市中心转移至偏远地区,位居边缘地带的穷人身体成为这一慢暴力的直接承受者,成为“可弃置的生命”而不被看见,这也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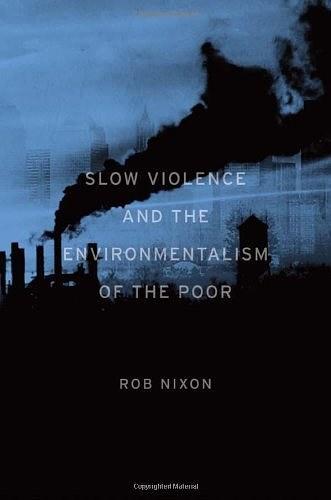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生存其中的人们来说,毒物带来的不仅仅身体的“变异”,毒物渗透进土地、河水、空气,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整片家园的覆灭,他们顷夜之间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成为被驱逐者。尼克森也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驱逐”的概念:驱逐不仅仅指强制性的移除,从故土搬迁,流落异地;同时也指居住在毒物土地之上却已经失去脚下的土地与资源,他们被遗弃、被剥夺了居住权。遭受核辐射的表层地皮需要被清理,牛奶、豆子、蘑菇不能吃了,肉要泡三个小时,马铃薯要煮两次,水也不能喝了,“毒进入土里、水里、血液里、奶水里。这儿一切都有毒。”由世世代代编织的在地景观被破坏、摧毁成异化的、抽象的景观,随之而来的是时间感的改变,由过去和未来构成的历史感被摧毁成为静止的现在,如同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篇自述文中所言,切尔诺贝利改变了我们和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下子被剥夺了不朽。时间停顿在死寂的土地上,变成它一直是的东西——永恒。”
“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信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而事实上,核泄漏现场的信息被封锁,被派往前线清理核辐射的工作人员签署秘密协议,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能告知任何人事实发生了什么,就连他们身上负载的核辐射量都是军事机密。
这是身赴切尔诺贝利现场的幸存者的讲述。毒物对身体的渗透,当然不仅仅是物质在躯体内部发生的化学反应,这种渗透也包含施加于承受者身上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位煤矿工人在切尔诺贝利清理工作结束的一个月后被诊断患有肺部、脑部、心脏疾病,在访谈中,他将身体内部的辐射负载描述为“异化的、不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力量——除了身体内部的病理上的客观不适,这种“异化的力量”同时也指向毒物背后的权力机制: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已然身处后苏联时代,他们的身体依旧被苏联时代的灾难所控制,依旧被幽灵般的过去所笼罩,带着已逝政权的残酷烙印。
谎言与信息的政治管控是切尔诺贝利处理现场的日常:当地居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造成居民恐慌是政治指令;军人、志愿者被欺骗利用,长官说不会有危险,只要记得饭前洗手,原本两个月的任务期限被无限拉长;防护措施简陋粗暴,士兵身体下方没有防护,穿廉价的迷彩靴子,睡在反应炉附近的麦秆上。知识与科学此时成为了权力的工具,医生得到指令,将切尔诺贝利爆炸后生下的异常婴儿定性为“先天性残疾”,而非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切尔诺贝利的另一番景象,是冷战格局美苏对峙背景下的政治话语宣传:广播连续播了三个月的“状况日趋稳定”,电视画面是当地居民摆拍的“祥和”生活,恐慌被指认为西方制造恐慌散布的谣言,市民被不断地提醒“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在海的另一端”,那才是“社会主义的大敌”。

相较于切尔诺贝利幸存者身体内部的政治伤害,对小说《人人都说我是动物》中化工厂爆炸的幸存者来说,他们的毒物身体所印刻的是全球跨国资本作为施暴者的角色和记忆。
在小说中,爆炸事故发生后,美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推卸责任:工厂拔腿就跑,关厂遣散员工;患者得病被归因于当地的贫穷与卫生保健的不健全,与那场灾难无关;法律诉讼被无限地延迟、被告躲得远远的,从未露面,“他们坐在美国,声称这个法庭无权审判他们”,“就这样,十八年来,这官司一直遥遥无期地拖着,对这个城里的人们而言,正义不断地被悬搁、被否定”。这也是历史上印度博帕尔事件的真实写照:爆炸事件被认为责任在于当地而非企业本身,美国联合碳化总公司在事件发生后撤离了安全程序员与监督员以减少利润损失。甚至,这家公司以合并的方式消失了。1999年,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收购了联合碳化,一家臭名昭著的企业消失了,对博帕尔应负的责任和赔偿也被搁置了。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在2000年回应环保人士称:“我无权对十五年前一个我们从未运作过的地方和从没生产过的产品负责”。
全球资本轻便快捷的“流动性”使得责任的推卸、风险的外化转移成为可能,而与之相对,毒物在承受者躯体内部“不可抹除”、“难以剥离”,这一对比的根源正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台湾华梵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张雅兰在《毒乡生存》一文中提到了“毒物殖民主义”的概念,认为跨国企业对在地生命的摧毁与殖民时期殖民主掠夺资源、压榨当地人民、土地等做法并无差别,毒物工厂征用贫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征用他们的生命与在地的生态资源。在全球资本体系内部,第三世界贫穷地区的生命成为“可丢弃的身体”。
罗伯·尼克森认为,我们应该将第三世界跨国企业的“无赖”行为放置于新自由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来阐释,正是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培育了企业的责任健忘症,“自由”名义之下的市场,实质上是并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欧美企业能够轻易地为自己对于第三世界施加的暴力行为推卸责任、逃脱责罚。资本的流动性与改头换面的便捷使得本应该承担责任的面孔更难以被辨认。于是,毒物伤害在某种程度上被合理化了,伤害的承受者成为了不可见的匿名他者。
无论是切尔诺贝利人还是考夫波尔城的居民,他们的伤痛都因“失去”了加害者而无法被指认——跨国企业撤离了,苏联垮台了,但其所留下的毒物依旧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内部,废弃、污物和毒物留给了他们,也借由他们的身体和环境留给了他们的后代,正如辛哈在小说结尾所言:“一切都会过去,留下的只有穷人。我们历经过世界末日。我们这样的人明天会更多”。
产生毒物的不仅有核辐射、化工厂爆炸这类灾难事件,事实上,毒物已作为一种“看不见的风险”渗透进入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危险蛰伏于每个人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弥散于水、空气、食物等生存元素里。化工元素、毒物颗粒以裸眼不可见的形态包围了我们, 包裹穿透生理意义上的躯体,危机随时恭候;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地为自身塑造一个远离污物、舒适安乐的后工业社会图景——化工厂撤离出城市中心,污物被迅速清理,潜伏着爆炸危机的电路设施、化工燃料被包裹在钢筋水泥之中,或被遮蔽在高墙之后。生态批评学者Simon Estok以“毒物健忘症”来描述现代人对日常毒素的习以为常与健忘,并自以为保持了安全的距离。
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长篇小说《白噪音》中就试图处理后工业时代蛰伏于日常生活内部的毒物危机。小说反讽地描述了一位中产知识分子从最开始傲慢地坚信毒物事件与他无关,到全家加入逃荒队伍,最后得知身体被毒物侵入的荒诞经历。小说主人公“我”杰克是一名大学教授,回到家里看到孩子们拿着望远镜时刻关注远处罐车出轨导致的毒气泄漏,当孩子和妻子表达对毒物弥散的忧虑时,“我”一再地向他们强调:毒物不会向这里飘过来,它就是不会到达这里的。只有居住在暴露地区的穷人才是灾难的受害者,“我是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系主任,我们住在一座整洁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城里,”逃难的事情不会落在我们身上。因此,当窗外警车、救火车和救护车警笛齐鸣,甚至在空袭警报声响起时,“我”却在满怀情欲地挑逗妻子。直到撤离命令发布,全家人才仓皇出逃,躲避到军营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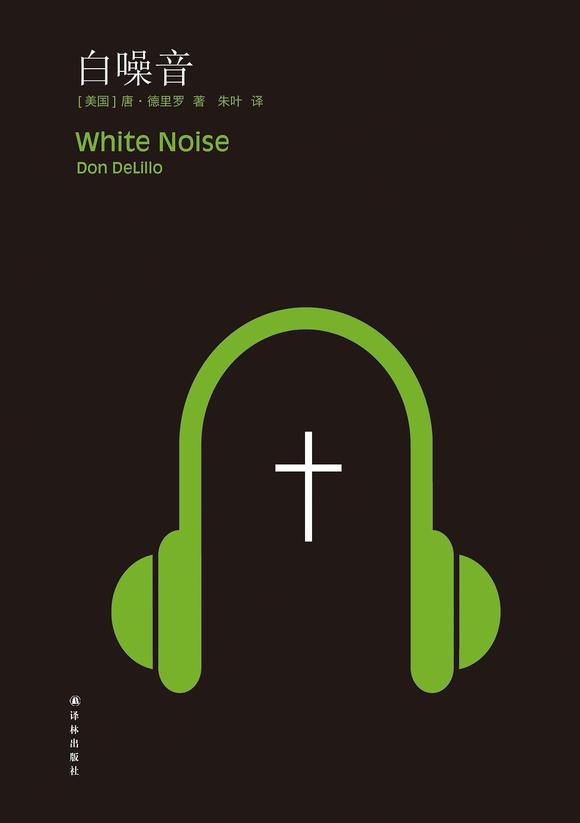
讽刺的是,由于在逃亡途中下车加油,暴露在毒雾中两分半钟,“我”被诊断为尼奥丁衍生物有毒废气的携带者,毒物将在“我”的躯体内寄居三十年——未来三十年里,死亡随时可能发生。正当“我”陷入死亡逼近的恍惚中,营房中的妻子朗读着小报上的报道和广告。小说大量地引述了这些媒体语言,这里充斥着关于“死后重生”、“返回前生”以及大灾难转危为安的启示性事件,人们陷入了对科技伟大的赞美与危机必将战胜的无限希望之中。在这里,唐·德里罗巧妙地将死亡的逼近与死亡在媒介语言和想象中消失这两个反差强烈的事实并置,不无讽刺地再现了毒物弥散于日常生活、而我们又热衷于塑造一个没有污染和死亡的后工业社会景观。
如同很多生态批评学者所论述的,如今我们已很难将环境与污物剥离开来,一个纯粹绿色天然的自然已是一个逝去的“乌托邦”想象。毒物身体不只是暴力承受者创伤书写的方式,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共同现实。毒物不只存在于被资本与权力所抛弃和排斥的废弃之地、边缘之地,它可能弥散于任何地方。然而,在政治与资本的阴影之下,无论是作为现代日常的毒物,还是作为暴力指认的毒物,其累积并潜伏的危险性与背后的复杂意涵往往被遮蔽,转而成为了轻描淡写的一则消息、一个过往、一次胜利。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