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鬼精怪的怒气是对人世间偏见的抗争,仿佛是人间家庭中饱受侮辱的女性的对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蒲松龄一生历经科场困顿,集腋成裘著成《聊斋》,以“异史氏”之名抒发孤愤,仅仅是为了讲述人妖之恋吗?鬼狐花妖又都是千篇一律地美丽又痴情吗?在由《聊斋》精读课程改写而成的小书《 <聊斋志异>二十讲》中,读者可以了解到更为丰富的故事类型与人物个性,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左江尤其注重女性主体的分析,将许多故事颇具新意地解读为“寡妇的命运”“妻子的哀愁”“女子当自强”“精怪的尊严”。 “精怪的尊严”这一节格外有趣,讲的是嫁与人类的精怪一旦受到了夫家的怀疑,宁愿从苦心经营的家中离去,也要保全自己的尊严,在履行人间礼法和妻子职责之外,她执着地保全最后的尊严底线,这样的妖精仿佛是人间家庭中饱受侮辱的女性的对面。
精怪也有尊严,鬼狐花妖纵使神通广大也受不了人间冷言冷语——正逢清明时节,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特别从《 <聊斋志异>二十讲》一书中节选了“精怪的尊严”这一章节,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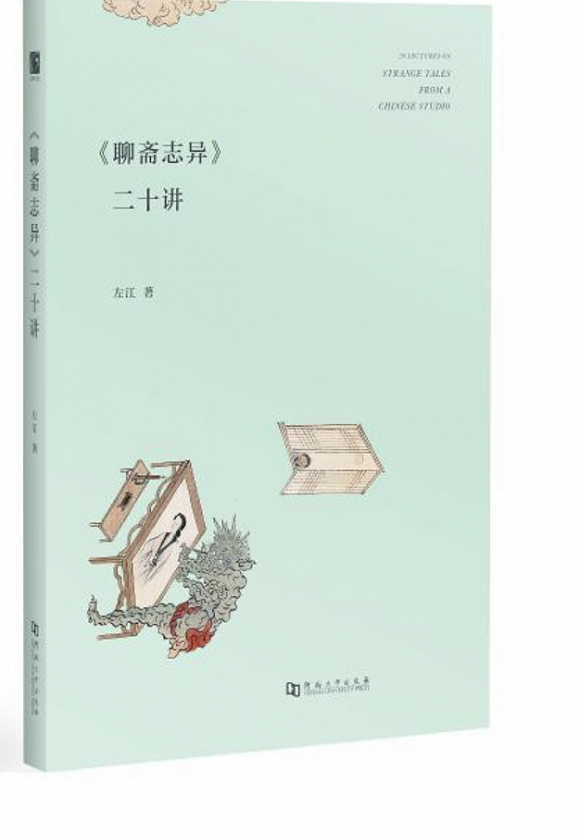
无论是阴界的黑暗阴冷还是山林的寂寞萧瑟,都让女性的鬼狐精怪纷纷步入了人世间, 我们以为她们都应该如《双灯》中的狐女一样,她们是积极主动的,她们也是强势的。魏运旺虽曾是世家子,但因家道式微,只能跟在岳父后面卖酒。不想姻缘天定,竟得到狐女的垂青。女子如此美丽,“楚楚若仙”(卷四《双灯》),魏运旺虽然满心欢喜,但自惭形秽,竟说不出一句调笑的话。女子嘲笑他:“君非抱本头者,何作措大气?”你又不是死读书的呆子,怎么也冒穷酸气呢?并且走到床前,将手放在魏运旺的怀里取暖。女子的主动,让魏氏也放下了紧张羞惭。第二天,女子又来了,调笑道:“痴郎何福?不费一钱,得如此佳妇,夜夜自投到也。”自称“佳妇”,对于自己的自荐枕席不隐晦不害羞,这种大气坦荡实属罕见。半年后,当缘分已尽,她来跟魏运旺告别:“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义。”仍是坦坦荡荡。在与魏运旺的关系中,狐女一直是主导者,她为人大气磊落,语言生动有趣,这样优秀的女子怎么会看上魏运旺呢?让读者也忍不住要问一声:“痴郎何福?”
《双灯》中的狐女潇洒地来也潇洒地走了,因为她只是魏运旺生命中的插曲,她不是他的妻,她并非真正步入了人世间的生活。如果她嫁给了魏运旺呢?也许如此洒脱的狐女就不复存在了吧。因为人类世界对女性从来没有那么友善,她们受到各种伦理道德、规矩礼仪的束缚,她们要学会忍耐学会听话。所以当鬼狐精怪要与人一起生活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她们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贤淑的女子,聂小倩“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卷二《聂小倩》),辛十四娘则“为人勤俭洒脱,日以纴织为事”(卷四《辛十四娘》),她们不再是“肌映流霞”“振袖倾鬟”的艳丽女子,即使如此,这个世界真的欢迎她们的到来吗?
红玉是狐女,与冯相如私下交往半年,此事被冯父发现,做父亲的大发雷霆,先骂儿子学轻浮放荡之事,不但败德而且折寿。接着又骂红玉:“女子不守闺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发,当不仅贻寒舍羞!”(卷二《红玉》)一个女子不守闺训,既玷污自己,也玷污别人。倘若事情败露,绝不是仅仅给我家带来耻辱。言下之意,这更会让红玉自己的家人蒙羞。遭此辱骂,红玉流下了眼泪,说:“亲庭罪责,良足愧辱!我二人缘分尽矣。”对此,冯相如并不是想着如何获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竟然说出这样的方法:“父在不得自专。卿如有情,尚当含垢为好。”父亲在,我不敢自作主张。如果你有情义,还请含垢忍辱,继续这地下的情缘。红玉“言辞决绝”,一定要离去。看起来她这是对社会规范的妥协,不愿在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继续做“逾墙钻隙”的苟且之事,实际上,这更是她对自己尊严的维护,被长辈当面训斥,如何还能心无芥蒂地两情和悦呢?
刘仲堪娶得艳妻司香,司香自称是“铜雀故妓”(卷七《甄后》),本已隶仙籍,因偶有过失被贬人间。二人结婚两年,大家都惊讶于她的美艳,“而审所从来,殊恍惚,于是共疑为妖”。只要一家人彼此信任,外人的猜疑本无关紧要,但刘仲堪的母亲也起了疑心,追问儿子司香的来历,刘仲堪稍微透露了一点,刘母非常害怕,要儿子与司香断绝关系。刘仲堪不肯,刘母竟然暗中找来术士作法。司香目睹了这一切,说:“本期白首,今老母见疑,分义绝矣。”惩处术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怀疑是对尊严的无情践踏,从来都是人与人相处时的致命伤。奚山初见阿纤,只见她“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卷十《阿纤》),他第一反应就是要为自己的弟弟三郎说亲,让这个美丽的少女成为自己的弟媳。阿纤姓古,她的父母也很赞成这门婚事。因为古父意外去世,阿纤就跟着奚山回去,与三郎结了婚。阿纤“寡言少怒,或与语,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这样一位美丽、勤劳、温和、谦抑几近完美的女子,大家都很喜欢,于是“上下悉怜悦之”。后来奚山偶然听说古家的一些异事,怀疑他们一家是老鼠精。虽然阿纤还是那个勤快的阿纤,但已不再是他心中理想的弟媳。奚山“归家私语,窃疑新妇非人,阴为三郎虑”,阿纤觉察到了别人的猜疑议论,对三郎说:“妾从君数年,未尝少失妇德,今置之不以人齿。请赐离婚书,听君自择良偶。”我嫁给你已经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做过有失妇德的事情,现在你们竟然不把我当人看。请你给我一纸休书,你自己另找好妻子。三郎深爱阿纤,一再表白:我的一片心意,你应该早就知道了。自从你进门以来,我家日益富足,大家都认为是你带来了福气,怎么会有人说你坏话呢?阿纤说:“君无二心,妾岂不知?但众口纷纭,恐不免秋扇之捐。”你没有二心,我自然明白。但现在众说纷纭,恐怕我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抛弃。三郎再三安慰,阿纤才平静下来。但奚山却放不下这件事,他甚至找来一只猫试探阿纤,“女虽不惧,然蹙蹙不快”,终于还是与母亲一起消失了。
作者在文中虽未明写阿纤一家是老鼠精,又无处不写他们一家有着老鼠的属性。她家的位置是“庑下”,家中陈设是“堂上迄无几榻”,吃的食物是“品味杂陈,似所宿具”。家里经营的生意是倒卖粮食,贩卖对象是“硕腹男子”。阿纤秀弱的外形、寡言少怒的个性、昼夜纺织的勤劳,以及善于储积粮食的能力,都有着老鼠的特性。阿纤作为一个能幻化成人的精怪进入了人类社会,她遵循着世间的一切道德礼法,履行着一个妻子的职责,她觉得自己无愧于人,她不能忍受别人的猜疑,尊严是最后的底线,所以这个自尊自重的女子跟着母亲决绝而去。

三郎是难得的多情种,当别人都在议论阿纤时,他是“笃爱如常”;当阿纤离开后,他“骇极,使人于四途踪迹之”;在没有阿纤的消息后,他“中心营营,寝食都废”,等待年余,仍“思阿纤不衰”。阿纤能遇到如此痴情人,也不枉她入世间一回。在叔弟奚岚的帮助下,数年后,这对苦命鸳鸯终于又相聚了。“不以人齿” 的遭遇深深刺痛了阿纤,是她内心沉重的阴影,这次她不再妥协,提出了回归奚家的条件:“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这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与奚山分家。从此三郎家日渐富裕,奚山家日渐贫困,阿纤不念旧恶,不但将公公婆婆接到自己家中赡养,还不时拿钱拿粮接济奚山家。此后三郎家也没发生什么奇特的事情。
真心喜欢阿纤,喜欢她对事情的清醒认识,知道人言之可畏,知道猜疑的杀伤力,它会毁掉亲情,也会毁掉爱情,所以主动提出要离去,决不在当下的温柔中迷失自我。当尊严被侵犯时,她决绝而去,不自怜自艾,不辩解,不乞怜。她也有自己的坚守,提出分家的要求,即使这看上去与礼法相悖,与孝悌不符。这样一位聪慧清醒又自尊自重的女子如何让人不喜?
因为身为精怪,她们有一定的法力,也就多了一份保护自己的能力。她们可以远离是非,远离背后的指指点点,躲开一切阴冷的目光。这一点点空间,也就使她们可以守住自己的底线,有了维护自己尊严的可能。
王御史小时候曾无意中保护过遭雷劫的狐狸,此后果然大贵,但人生难得圆满,富贵如他有一子名元丰,“绝痴”,非常傻,十六岁还不分男女。这一天,有一妇人,自称虞氏,带着女儿小翠上门来,自愿将女儿嫁与元丰为妻。小翠不但美貌,“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卷七《小翠》),而且很聪明,“能窥翁姑喜怒”,王公夫妇对小翠也很宠爱。
小翠并不嫌弃元丰呆傻,每天带着元丰在家中嬉戏玩耍,一天,元丰蹴踘正好打中了王公的脸:
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责女,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见之,怒甚,呼女诟骂。女倚几弄带,不惧,亦不言。夫人无奈之,因杖其子。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顿解,释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忻。
这一段写一家四口的关系以及彼此的个性都很生动细致。王公是一家之主,自有一家之主的威严,见儿子媳妇在家中胡闹,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就捡起石块向儿子扔了过去。但这属于内室的事,得交由夫人处置。对于夫人的训斥,小翠只是低头微笑,用手指抠床,看起来都听进去了,实际上全当作了耳边风,仍然我行我素,又将元丰涂成了大花脸。夫人也真动了怒,将小翠喊来大骂。小翠仍是油盐不进的样子,靠着几案玩衣带。夫人没办法,只好找元丰出气,拿起棍子打儿子,小翠这才变了脸色,跪在地上求饶。夫人一见小翠如此护着自己的儿子,所有的怒气也烟消云散了。等夫人一走,小翠开始哄元丰,又是拍灰尘,又是擦眼泪,又是按揉伤痕,又是喂零食,直到元丰破涕为笑。
日子就在小翠与元丰的胡闹中流逝,本来寂静的屋子忽然有了生机,“喧笑一室,日以为常”。小翠看似胡闹的行为却暗藏玄机,不但扳倒了王御史的政敌,还治好了元丰的痴病。至此,元丰的“痴”、小翠的“癫”都未再发作,两人“琴瑟静好,如形影焉”。如此“一生一世一双人”该多好,如此岁月静好一起慢慢变老该多好,但天不遂人意,过了一年多,王御史因弹劾被免官,他想将一价值千金的玉瓶送给上司行贿。小翠很喜爱玉瓶,捧在手中欣赏时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了。小翠很愧疚,赶紧告诉公婆。不想公婆并不体谅,二人交口大骂。小翠生气地跑出来,对元丰说:“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我在你家,保全的可不止一个玉瓶,为什么就不给我留点面子?原来小翠并非人,她的母亲就是曾为王御史庇护躲过雷劫的狐狸,又因为小翠与元丰有五年的缘分,所以让小翠过来“报曩恩,了夙愿耳”。现在受此羞辱,实在太伤自尊,虽然五年未满,小翠再也无法忍受,“盛气而出,追之已杳”。
元丰相思成疾,骨销形立,就这样近两年时间过去了。一天偶然路过自家在村外的亭园,不想小翠竟然在里面。元丰请小翠跟自己回去,小翠不肯,只答应在园中住下来。夫人来请,小翠“峻辞不可”,坚决不答应。小翠与元丰又在一起了,他们还能琴瑟静好吗?不能。小翠常劝元丰另娶新人,元丰一直不同意。过了一年多,“女眉目音声,渐与曩异”。小翠又劝元丰为了子嗣,赶紧结亲,这次元丰答应了,与钟太史的女儿定了亲。等新人入门,“则言貌举止,与小翠无毫发之异”。原来小翠早已预知元丰会娶钟氏之女,“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元丰大婚之日,也是小翠离去之时,她留下玉玦一枚,飘然而逝。
阿纤被兄长怀疑,小翠被公婆责骂,都很伤自尊,为了自己的尊严,她们都选择了逃离,但她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她们的丈夫深爱着她们。阿纤离去后,虽然父兄都很庆幸,三郎却是相思不衰,坚决不肯再婚,因为父兄一直讥诮责骂,才无奈纳了一妾。小翠离去后,元丰“恸哭欲死,寝食不甘,日就羸悴”,他也同样拒绝再婚,“惟求良工画翠小像,日夜浇祷其下,几二年”。枕边人的一往情深,坚信不疑,让阿纤、小翠这样的精怪虽然在人世间受尽了委屈,内心满是伤痛,也足以感到慰藉吧。柔情融化了尊严前立起的寒冰,她们又回到了丈夫身边,阿纤再未离去,小翠也为元丰做足了工作后才因五年缘尽从容而去。这样的故事也算圆满了吧。
如果猜疑来自枕边人,又该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呢?常大用是洛阳人,癖好牡丹。他听说曹州的牡丹名冠齐鲁,去曹州时,就借住在一个缙绅的花园中。虽是二月,牡丹未开,他每天徘徊在花园中,注视着花枝上的嫩芽,期待着花蕊的绽放,还作了《怀牡丹》绝句一百首。不久,花儿渐渐含苞待放,他的盘缠也快用完了,便典当了春衣,流连忘返。一天凌晨,常大用又前往花园,看到一女郎与一老妪;傍晚再去,又见到她们。他慢慢躲到一旁,只见女子“宫妆艳绝”(卷十《葛巾》),如神仙中人。他忍不住冒失现身,长跪说:“娘子必是神仙!”老妪出言训斥他,女郎倒不生气,微笑着说:“去之。”让他走吧。常大用返回书斋,既悔恨自己的冒失,又担心女郎的父兄来辱骂自己,又悔又怕一夜下来竟然病倒了。天亮后,见无人来兴师问罪,心才渐渐安定下来,“而回忆声容,转惧为想”,想起女子的声音容貌,恐惧转化为思念。这样过了三天,几乎憔悴而死。
女郎就是葛巾,她被常大用的痴情感动,几经曲折,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过了些时日,葛巾说:“近日微有浮言,势不可长,此不可不预谋也。”常大用大惊失色,说:“且为奈何!小生素迂谨,今为卿故,如寡妇之失守,不复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锯斧钺,亦所不遑顾耳!”我一切听你的安排,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于是两人计划一起逃亡,葛巾跟着常大用回家。等二人到家,常大用还有些害怕,葛巾却很坦然,说:“无论千里外非逻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不必说千里之外他们查不到这儿,就是被人知道了,我是官宦大家的女儿,就像当初卓王孙对司马相如也不能怎么样,你大可放心。
常大用的弟弟大器,十七岁,葛巾觉得他颇有慧根,就将自己的妹妹玉版嫁给了他。姐妹二人嫁兄弟二人,自是美事一桩,“兄弟皆得美妇,而家又日以富”,日子可谓蒸蒸日上,越来越红火。又过了两年,姐妹二人各生一子,才稍稍透露她们的身世,说:“姓魏,母封曹国夫人。”常大用心中存疑:一来曹州没有姓魏的世家大族,二来大族人家丢了两个女儿,怎么会置之不问呢?心中种下的怀疑的种子,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反而会越长越大,直到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所以常大用又借故去了曹州,“入境咨访,世族并无魏姓”。他仍旧借住在原来那个花园,忽然看到墙壁上有《赠曹国夫人》诗,内容颇有些怪异,便询问主人。主人就请他去观赏曹国夫人,原来是一株牡丹,此花为曹州第一,所以朋友戏封它为曹国夫人。常大用问这是什么品种,主人说是葛巾紫。常大用心中越发惊骇,疑心葛巾姐妹是花妖,猜疑的种子果然变成了大树。他回到洛阳后,不敢当面质问,只是叙述那首《赠曹国夫人》诗来一探究竟:
女蹙然变色,遽出,呼玉版抱儿至,谓生曰:“三年前,感君见思,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生方惊顾,则二女俱渺矣。
常大用自从心中有了疑惑以后就想给自己找一个答案,答案不外乎两个,一葛巾姐妹是花妖,二她们的确是世家之女。他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答案呢?知道了答案他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是世家女,当然是皆大欢喜。那如果是花妖呢?是立刻请巫师来驱逐她们?还是心存芥蒂带着畏惧继续生活在一起?常大用肯定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他只想“觇之”,他并不知道“觇之”的结果是什么。但葛巾是如此决绝,她让他立刻面对一个残酷的结果。三年前,她因为被他的深情感动,所以显出人形,以身相报。现在既然被猜疑,就不能再生活在一起了。不但自己不能跟你在一起,连孩子也不能留给你,因为他们是花妖之子,不能再让他们在人世间的冷漠与猜疑中长大。但明伦评曰:“金可求,盗可退,而浮言终不可灭,猜疑究不可消。遂使玉碎香消,谁能解语?”是的,流言蜚语与猜测怀疑都是男女关系中的致命伤,有了裂痕就再难愈合。

常大用悔恨不已,但葛巾还是给了他一点安慰,在孩子堕地的地方,长出了一紫一白两株牡丹,比普通的葛巾、玉版花瓣更繁更密。你从此就老老实实做个爱花人,守着牡丹好好过日子吧。常大用当得起“花痴”二字吗?马子才酷爱菊花,当他知道黄英姐弟是菊花精时,“益敬爱之”(卷十一《黄英》)。黄生爱着香玉,当他知道她是花妖时,“怅惋不已”(卷十一《香玉》),“日日临穴涕洟”,期盼着她的重新归来。临终时,他对儿子说:“此我生期,非我死期,何哀为!”因为他的魂将化去与香玉、绛雪为伴。这样的情谊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已超越了人妖的界限,超越了生死的界限,所以作者大为赞叹:“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感情的极致,可以沟通鬼神。花死了可以化成鬼来陪伴,人死了可以将魂寄托在花的旁边,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吗?跟马子才、黄生相比,常大用实在是卑微怯懦的小人,作者也对他进行了嘲讽:“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何必力穷其原哉?惜常生之未达也。”心怀专一的人,也就是“情之至者”,才能沟通鬼神,如此也就不能说葛巾无情了。怎么能说葛巾无情呢?她是因为被常大用的深情感动才来到人间,没想到常大用是叶公好龙之徒,胆小多疑,这是对用情专一的背叛,这样的人如何能在一起生活呢?
狐鬼精怪因为缘分因为贪恋人间的温暖走入了人的生活,她们努力向人世间的礼仪规范靠拢,成为孝顺的媳妇、贤淑的妻子,但她们从来没有丧失自我,她们坚守着尊严的底线,当被猜疑被非议时,她们选择决绝而去,她们的怒气是对人世间偏见的抗争,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唯愿世间一切物都能被公平对待。幸运的是她们是精怪,她们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葛巾明确指出“今见猜疑,何可复聚”,她可以翩然而去,但如果只是人世间的普通女子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大概只能要么成为被无情休弃的妇人,要么在流言蜚语中抑郁吧,而这都是比死还艰难的境遇。
霍生与严生从小十分亲昵,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这一次,霍生又设计取笑严生,跟别人说自己跟严生的妻子很亲密,证据是严生妻子的私处有两个赘疣。霍生知道此事,其实是从自己的妻子那里听来的,但严生听说后,信以为真,“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卷三《霍生》)。严生听信馋言,立刻怀疑起妻子的贞洁,根本不听妻子的辩解,妻子不堪其辱,只能以死相争。姚安为了娶美丽的绿娥为妻,不惜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但娶得艳妻后,“以其美也,故疑之。闭户相守,步辄缀焉;女欲归宁,则以两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舆封志,而后驰随其后。越宿,促与俱归。……姚以故他往,则扃女室中”(卷八《姚安》)。因为妻子美丽,就开始产生各种怀疑:怀疑她不贞洁,怀疑别人会惦记自己的妻子。所以什么事也不做了,整天关门闭户守着妻子。妻子回娘家,他要用两手支着袍子盖在绿娥身上出去,等她上了轿要立刻拉上帘子还要做好记号,然后跟在轿子后面。在娘家住一晚,就催促绿娥一起回去;有事外出,就把绿娥锁在屋内。……最终,姚安还是因为怀疑将绿娥给杀了。姚安的疑神疑鬼让他变成了一个疯子,也让绿娥变成了冤死鬼。
《霍生》与《姚安》的事例很极端,更能看到猜疑带来的伤害。具有法力的精怪还可抽身而去,普通的世间女子根本无处可逃,都成了一缕冤魂。过去的女性无力保护自己,当下的女性总可以吧。希望世间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能被真诚以待,没有怀疑,没有非议,没有冷漠……也许可以这样想想吧。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 <聊斋志异 >二十讲》一书,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