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亨利·哈迪,就没有后来的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你现在想必不会因为我通篇的严重扭曲的引用而感到惊讶了。” 图片来源:GEMMALEVINE/GETTY IMAGE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战后英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顶尖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上过BBC的广播节目,也是个高产的散文家,得过不计其数的奖项。但事有玄机。那位刻薄的牛津大学教授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曾有名言称,“与我们的上帝和苏格拉底类似,他述而不作。”临近65岁,伯林只出版过三本书,另有一本他主编的文集。
这解释了为何当他的文学编辑亨利·哈迪(Henry Hardy)首次在伯林家的地下室里搜寻未刊手稿时会感到大吃一惊。与进入图坦卡蒙墓的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类似,哈迪发现了一笔远远超出自己想象力极限的宝藏:书架上“杂乱的论文堆得老高,满是各种书本、文件夹和收纳箱。材料的数量是惊人的、可怕的,也是喜人的”。根据他的回忆:“我第一次浏览时态度相当草率,但很快就发现了被搁置数十年之久的未刊文本,除了伯林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读到过它们。”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哈迪对这批浩如烟海的材料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书并付梓出版,其总数约有十来本。他一手造就了伯林的美名。如果没有亨利·哈迪,伯林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种地位。这是非同寻常的伙伴关系。“天才和书呆子。”是哈迪对此的描述。某些时候,两人看起来更像拉脱维亚犹太人版的伯提·伍斯特和谨慎周到的全才吉夫斯(典出美国作家伍德豪斯的小说《吉夫斯》,主要讲述了迷迷糊糊的英国绅士伍斯特和才华横溢的仆人吉夫斯之间的故事——译注)。每当哈迪挖出一条极不起眼的索引,伯林就会回应说,“太漂亮了!简直像福尔摩斯一样!(Bravissimo! Marvellous Scherlockismus!)”
《找寻以赛亚·伯林》(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实际上把两本书合并成了一本。在上册当中,哈迪回忆了自己如何结识伯林以及怎样整理他未发表的广播谈话、演讲、文章和手稿。下册仅有100来页,主要与二人在哲学上的对话有关,尤其聚焦于伯林在人性、多元主义和宗教等问题上的见解。
上册是最有趣的部分。二人在1972年首次会面时,伯林是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的院长。哈迪当时在该院修读哲学本科课程。他当时只有23岁,曾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教授过一年的古典学。
那时伯林已经年届六旬,名声如日中天。伯林1909年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后前往英国求学,在牛津从事研究和教学,奉英国政府命赴美承担战时服务时有上佳表现,1946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1957年被授予爵位,1971年又荣立一等功(Order of Merit)。1957年至1967年间,他曾担任牛津大学奇切利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在这些荣典和身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国际名声之外,伯林对自己的工作颇为谦虚,对批评意见多有积极回应,如哈迪所言,“其犹豫不决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
二人就哈迪担任伯林的编辑一事达成了共识,伯林散乱的论文因之而得以脱离“混乱至极”的状况,被整理得井然有序。这项工作大约花费了哈迪40多年的时间。其难度比表面看上去要大许多。哈迪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二。其一,收集大量的演讲稿、广播稿和文章并将之编纂成《俄国思想家》《反潮流》《现实感》和《自由及其背叛》等论文集。这一工作要求遍访各大图书馆以寻找索引,改正不准确的脚注以及哈迪所谓伯林的“不可靠的引用”,破译被墨迹和潦草的修改弄得一团糟的手稿、古旧的录音带(伯林经常口授其文章和讲座)和广播录音。有一次,哈迪向伯林询问某处索引。伯林答道,“你现在想必不会因为我通篇的不准确、语焉不详和严重扭曲的引用而感到惊讶了……我当然没有索引可言。你居然还相信我会有这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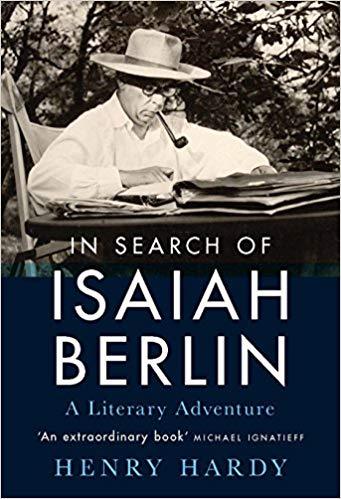
每当哈迪整理好手稿并使之通顺后,他就得料理伯林深入骨髓的自我怀疑倾向并说服他同意出版。这是哈迪工作当中最困难的环节,他也经常吃闭门羹。例如,他始终没法说服伯林将其曾获得197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演说整理成书出版,为出版《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The Three Strands in my Life),他不得不等待将近二十年之久,至伯林去世之后才处理停当。
该书所刻画的伯林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书中涵括了他生命里的最后25年。此时距离他1950至1970年代那段不同凡响的黄金时期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最出色的政治理论、哲学史和观念史论著都是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当时的伯林是否要自信一点?已发表的书信显示,即便在全盛时期,伯林也依旧缺乏安全感且极端敏于批评,不情愿出版他最优秀的作品。
以上简单回顾了一些迷人的幕后经历,只有哈迪知晓而读者浑然不觉。对那些曾经听过伯林的讲座或领略过他雄辩文风的人来说,一切都显得徒劳无功。我在1990年代中期曾与伯林面见过好几次,当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和我与伯林一同在BBC二台上做了三期节目。伯林看起来充满自信且胸有成竹。
如哈迪所言,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大量散文依旧蒙尘且无人问津。伯林一向对复原被湮没的断章残篇抱有抵触情绪。他怎么说也是个一生荣华、名闻遐迩的人了,为什么还如此缺乏安全感?他为什么偏爱演讲、广播谈话和散文而非长篇大论?他生前从来不愿出版完成于1965年的最后一部大作《浪漫主义的根源》。由亨利·哈迪及其同事合编的四卷本书信集《找寻以赛亚·伯林》将深远地改变我们对伯林的观感,围绕我们这位顶尖思想家展露出一幅更为晦暗、更加复杂的图景。
《剑桥伯林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Isaiah Berlin)更少个人性,更加学术化。不过,开头由去年12月刚刚去世的阿莫斯·奥兹(Amos Oz)以及哈迪与乔舒亚·车尼斯(Joshua Cherniss)撰写的两篇有关伯林其人的短文是非常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有关伯林的短文。奥兹的文章仅两页长,但其对伯林的犹太和俄罗斯根源有相当精到的把握,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诸如奥兹、所罗莫·阿维内利(Shlomo Avineri)和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等以色列学人对我们理解伯林所做出的诸多贡献。
书中余下的论文来自2017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一场会议,包括几个板块:伯林论哲学、人文科学与政治理论、伯林与观念史、伯林与政治。全书以伯林1960年代中期的论文“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 of History)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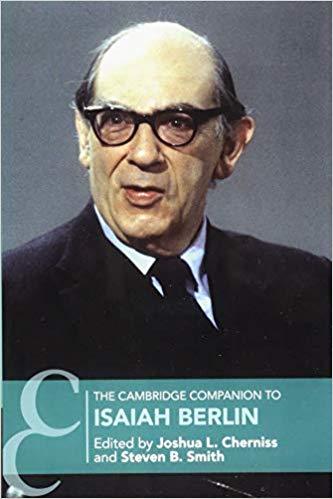
该书涉及到的伯林作品相当广泛,其中包括他身为分析哲学家的早期著作、1930年代对马克思的评论以及论俄国思想家、启蒙运动、反启蒙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论著。一些论文将伯林论自由主义的著作放到冷战这一关键语境下来加以考察,完成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伯林曾在1949年形容冷战为“信条之间的战争……宗教改革及其余波以来最大的一场”。
书中还突出了一大转变,即思考伯林的视角从自由主义向多元主义的转变。1950年代探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作品令伯林以自由主义思想家而闻名。近年来,学界开始较多地强调他有关多元主义与价值冲突的论述,这让他与如今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关切更加具有相关性。
书中各篇论文作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有一部分人对伯林所处的世界——无论里加还是牛津——之重要性有真切的感受,另一些人则没有。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牛津,对一些来自美国的年轻学者而言就好比是另一个世界。其中有人写道,“英国的哲学活动在两次大战期间陷入了严重停滞。”她显然没考虑到RG·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没有留意崛起于1930年代的少壮派学者如AJ·艾耶尔(AJ Ayer)、斯图亚特·汉普谢尔(Stuart Hampshire)和伯林自己。
部分论文的批判性严重不足。不过其中最有趣的一篇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解读伯林的论著。他对启蒙运动的解读是否太片面化?斯蒂芬·史密斯(Steven Smith)如此发问。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真像伯林所暗示的一般吗?为什么他略过了这些思想家之间的重大差别?车尼斯和哈迪接受了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批评:为什么伯林在解读赫尔岑或是维柯之类的思想家时,总给人一种他其实在谈论自己的感觉?他因博闻强识而受人景仰,在音乐、文学与哲学领域均是行家里手。但也有一处巨大的鸿沟:伯林在科学与经济学上建树平平,他情有独钟的俄国经典作家里甚至没有包括诸如艾萨克·巴贝尔(Isaac Babel)以及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这样的巨擘。
话说回来,年轻一代观念史家对伯林的评价才是房间里的大象。伯林涉猎极广:启蒙运动、反启蒙与浪漫主义。晚近的学者已经重绘了知识图景,为18世纪与19世纪的思想提供了一幅更加精巧的画卷,他们更强调历史和文化语境,而非个人的天才。这些批评很少有人注意到。剑桥学派——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GA Pocock)和邓恩(John Dunn)——还勉强有人提及过几次。被忽视的还有乔纳森·伊斯瑞尔(JonathanIsrael)的启蒙运动三部曲,该书对伯林颇为不屑。有两个段落提到了莫米里亚诺(Monigliano)对伯林1976年的“维柯与赫尔德”(Vico and Herder)一文的严厉批评。
这本剑桥指南的最有趣之处,是其恰好反映了伯林所研究的那个变化多端的世界。其中心从牛津转到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年轻一代论文作者都来自美国的大学。在伯林80岁生日及1997年逝世后对相关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基本被无视了——只有哈迪、阿兰·瑞恩(Alan Ryan)和乔治·克劳德(George Crowder)亮了一下相。伊格纳季耶夫、约翰·格雷(John Gray)、玛格丽特、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则都不在其中。这不免给人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
正是这一点让哈迪和阿莫斯·奥兹的论述显得特别珍贵。他们使伯林栩栩如生。他那不同凡响的声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电视观众,兼具犹太、俄国和英国三重特色。归根结底,为子孙后代保藏伯林的卓绝学识的,正是亨利·哈迪的学术工作。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