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敢于挑战的亚洲女性声音正在重塑美国移民群体的故事,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真实的样貌。

图片来源:Slate
小时候,父亲总会读书给我听。后来我慢慢长大,逐渐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缕光,明白在压迫面前如何站起来反抗。我们一家是危地马拉裔美国人,而拥有拉丁美洲血统,就意味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Márquez)和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一定在你的必读书单上。这些作家终其一生改写了那些殖民大国写下的政治社会历史,捕捉了我们的集体想象。然而有一天,我的姨姥姥问我,这两位盛誉加身的作家的文字中,女性怎么都被过度性化(over-sexualize)了呢?他们对女性本身的观点视而不见。把男性凝视放到这些作品的语境中,审视它们如何表现女性(或者压根就把女性给忽略了),我对这些作品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了。我感到一股驱动力,开始寻找更加多元的文学作品,于是我发现了玛丽亚·露易莎·邦巴尔(María Luisa Bombal)、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ristina García)、英格丽德·罗哈斯·康特斯(Ingrid Rojas Contreras)和珊蒂·塞卡让(Shanthi Sekaran)。
我们现在所读的传统西方文学存在这一大块空白,叫人不安——这些空白可以用女性书写的重要当代文学来填满。我最近就遇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在一次朗读会上,我听到了菲律宾裔美国女作家伊莱恩·卡斯蒂略(Elaine Castillo)的作品。她文字的直接和紧迫把所有人都迷住了,整个房间陷入一片寂静。她为我们揭开伤疤,讲述了两个菲律宾裔女性的故事,她们一位是一代移民,另一位是二代移民,一个直一个弯。她用文字与历史对话,讲述一个更清晰的过去。不久后,我就参加了其他的一些读书会,遇到了华裔美国作家瓦妮莎·华(Vanessa Hua)、韩国裔美国女作家R.O.权(R. O. Kwon)和新加坡裔美国女作家克里斯汀·陈(Kirstin Chen)。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敢于挑战的亚洲女性声音正在重塑自己移民群体的故事,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真实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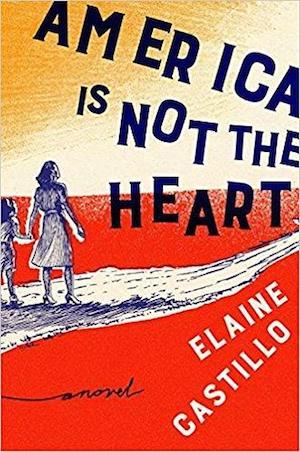
卡斯蒂略2018年的作品《美国不在心中》(America Is Not the Heart)也是对同为菲律宾裔美国作家的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1946年的《美国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致敬——那是一本半自传式小说,讲述了美国西部乡村一位移民的故事,它也为后来的文学作品铺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卡斯蒂略的小说牵着读者来到今天位于城郊的菲律宾移民社区,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似乎扭转了人们对性别分工的印象,在她的笔下,寡言少语的女人每天没完没了地工作以补贴家用,同时也在与自己往昔在游击队度过的黑暗回忆纠缠。小说的主人公海罗(Hero)来到美国时什么证件都没有,对她的姨妈帕兹(Paz)和叔叔来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她还只能在一个菲律宾理发店里当收银员——她端不了盘子,也拿不起刀。有时同事看到她扭曲的手指会忍不住发问,海罗便会回答说:“我曾经是新人民军的一员,差不多有十年吧。然后我被捕了。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两年。就是在那儿弄成这样的。”
“在那儿弄成这样的。”这时候的海罗还没法说出自己遭受的暴力和创伤,将痛苦藏在闪烁其词的言语背后,对她来说,代词就是一面保护盾,也让她把记忆锁在心里。然而另一边,一次次的往日重现成了她的新战场,把她带回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统治下的七十年代,重温那些准军事斗争的经历。作为读者,我们尊重她的沉默,她可以一直安全地保管着自己的秘密,直到什么时候她自己愿意解开这些谜团。
海罗内心的斗争将她和帕兹姨妈联系在一起,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帕兹的内心独白,这也是我们能听到帕兹说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时刻之一。这部分以第二人称的角度书写,邀请读者参与到角色的生活中,在她最私密的时刻陪伴两旁:“你也知道,让你在一个地方成为异类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身贫寒……你这辈子都会是个外国人。”
在菲律宾,帕兹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到了加利福尼亚,她依然没有摆脱贫穷。帕兹是个护士,她会承担额外的轮班,好补贴丈夫微薄的工资。丈夫有一份保安的工作,值晚班。他虽有菲律宾的医疗执照,却因在美国无法转换而如同一张废纸。帕兹看着丈夫,每当他踏过机场的安检门,朝着家乡的方向走去,他的肩头就抬高了一英寸。召唤他回家的不仅是思乡之情,还有一个医生的职位。终于他永远地离开了,还带走了女儿。帕兹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在卡斯蒂略的故事中,男人最终回到了传统的性别角色里——在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养家糊口,做个称职的父亲,而女人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继续战斗,继续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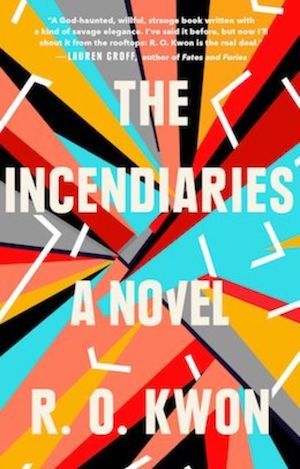
卡斯蒂略讲述了女性的适应能力,韩裔美国作家R.O.权则在同年出版了《火药》(The Incendiaries),告诉你她们如何消失。在小说的开篇,韩裔美国女大学生菲比(Phoebe)正在哀悼母亲的去世,而她也跟一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有关。小说的后续部分以倒叙重现的形式展开,抽丝剥茧讲述了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男人制造的暴力在菲比身边筑起围墙,而且每一项都对她不利。作者把诉说菲比观点的章节放在两个男人——威尔(Will)和约翰·利尔(John Leal)的章节之间。这样的结构让小说有了一种密室般的幽闭感——男性的观点不断侵袭着女性的看法。卡斯蒂略的女性人物在书页间自由游走,权笔下的菲比这个角色则时时被推搡、拖动,被威尔孩子气的回忆重构,被利尔狂热的邪教崇拜改写。前者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友谊与爱,后者则是女主人公哀悼的一种方式。
这不是一场三角恋——尽管威尔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一场两个自私男人之间的拉锯战,争相剥削利用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份认同、话语和身体。举个例子,书中菲比鞭打自己,只为了顺利进入利尔的邪教,将其奉为“Jejah”——这个词在韩语中意思是“先知”。利尔鼓励她,通过对身体的自我鞭笞来消解自己的罪恶和悲伤。在这之后威尔畏缩了——“针织连衣裙打开的口子里,她后背十字形的伤痕显露出来,已经成了一块块淤青,有些地方的皮肤已经破裂了”——但他却还是无法忍受自己“丢了”她的身体,拱手让给约翰,结果强奸了菲比。
当菲比永远逃离威尔的时候,讲述她的想法的那一章就变得更精简、更清晰了。这些文字带读者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她回忆起母亲的死,触碰信仰。她升华了,到了一个威尔、利尔和紧随爆炸而来的FBI调查员都触碰不到的阈限空间,这在文中也成为她消失于人间的一个隐喻。权推着读者们,思考对女性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暴力之间的一致性,就像菲比必须与生活中这两个暴力的男人相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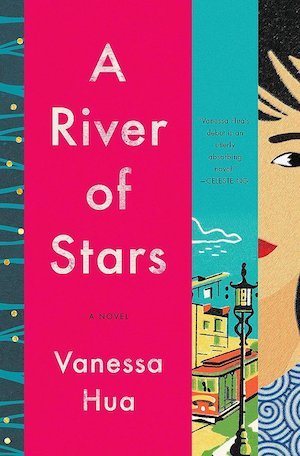
瓦妮莎·华2018年的《星光之河》(A River of Stars)可以说是一本公路小说,她自己称之为“怀孕版的《末路狂花》”。两个未婚先孕的女子被她们的中国移民家庭藏在洛杉矶一家非法月子中心,她们双双逃离,跑到洛杉矶的唐人街。斯嘉丽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无证移民,有一位已婚的情人,而黛西则是一个未成年的华裔美国女孩,正在找自己的男朋友,也就是肚中孩子的爸爸。她们的旅程开始得战战兢兢,充满不确定性,原本生活中的男人也没有给予什么支持,但随着孩子的出生,她们逐渐变强大了。她们合租了一套公寓,初次为人母的经验锻炼着她们的韧性:两人用从街上找到的东西以物换物,推着小车贩卖斯嘉丽做的食物,她们活下来了。
权探索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瓦妮莎·华则为独立单身妈妈唱赞歌,颂扬她们昂首站起。两人所写的都是当下急需、必不可少的故事。尤其是斯嘉丽这个角色,她可以代表中国移民女性的经历——经历了孤独和绝望,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情人杨老板不仅把她藏在洛杉矶,在中国也对两人的关系秘而不宣——他一边为了保护自己家人的声誉,把斯嘉丽藏起来,一边又追踪着自己男性继承人的下落。
在洛杉矶的唐人街,斯嘉丽想办法在移民社区中找到了互相支持的网络,而这正是那个男人给不了的。瓦内莎·华描绘了这里的食物水产市场、学校、公共麻将比赛和电信餐厅,这些都是唐人街的“文化中心”,为的是重塑、记忆并找回过去在中国的社区生活元素。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移民大本营都庇佑着斯嘉丽和黛西,直到她们建立起勇气,离开舒适区,学习如何做一个新妈妈,如何做出勇敢的决定,最终走向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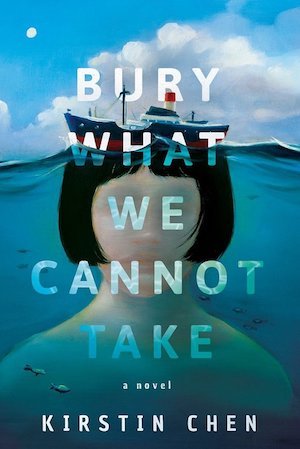
新加坡裔作家克里斯汀·陈的《带不走的就将其埋葬》(Bury What We Cannot Take)讲述了翁氏一家离开毛时代中国大陆的故事。母亲谎称自己丈夫生病,需要拿到赴港临时签证。然而这时她面前摆着一个不可能的抉择,她只能拿到三个签证名额,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必须留下,以证明他们还会回家。她最终选择带上了阿良,把九岁的姗姗留在国内。
当书中的母亲和女儿正期待重逢时,香港家中的爸爸和儿子依然无法放弃那让他们获得特权的政治影响——儿子阿良被学校里的民族主义讯息鼓动,老师也鼓励他加入共青团。一到香港,阿良就和新朋友计划着回到毛时代的大陆。与此同时,父亲明目张胆地“藏”了一个情妇,家人也对此全盘接受,认为这是常见现象,是他男性特权的表现。
在谈到这本小说的时候,克里斯汀·陈承认,自己在写作时也有所顾虑,毕竟她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她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二维的平面展现:阿良想要成为父亲这样的人,而父亲担心男权制度的颠覆——正是这种制度保护着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婚外情事。
读完这四本书后,我拿起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55年关于越南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把格林的男性、西方视角的书与其他四位亚裔美国女作家浸没式的观点相比似乎是件很有趣的事。虽然格林这本书建立在对冷战期间美国干预主义的政治讽刺上,但他笔下的越南角色——从好心给客人准备鸦片大烟的妓女,到为了填补空缺的毫无个性的士兵和平民百姓——都是克里斯汀所担心的过度简化的受害者。
现在看来,格林的作品首先是政治评论,其次才是研究人物性格的文本。另一方面,从他那个年代以来,我们对文学的要求也产生了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本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内在性首先都是走向政治的推动力。当她们书写生活面临崩溃的女性时,父权制和带来这种破坏的政治制度也一并显现。
(本文作者Michael Adam Carroll出生、成长于危地马拉,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取得博士学位。)
(翻译:马昕)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