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人们流离失所,家园易主,但身份认同却没有改变。

《抛开火箭弹》封面局部。断壁残垣前,一个巴勒斯坦小女孩在跳绳。图片来源:亚马逊
特朗普上台以来,巴勒斯坦人心心念念的追求屡屡受挫。美国相继宣布停止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提供资金、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还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了耶路撒冷。白宫走的每一步都巩固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让美国的众多选民看到,巴勒斯坦剩下的不过是一块危险的土地,充斥着建到一半的房子,哪里都能成为火箭炮的发射地点,到处都有可能滋生愤怒的恐怖分子。
赛斯·安兹斯卡(SethAnziska)和马塞洛·迪钦蒂奥(Marcello Di Cintio)都是在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西方叙事中长大的,现在,他们写的书却迥异于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息,转而探索巴勒斯坦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在《遏制巴勒斯坦:从戴维营到奥斯陆》(Preventing Palestine: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Camp David to Oslo)中,美国作家安兹斯卡上溯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讲述了这一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展开的斗争如何渐渐将巴勒斯坦的建国诉求挤到边缘。加拿大作家迪钦蒂奥则在自己的作品《抛开火箭炮:当代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Pay No Heed to the Rockets: Life in Contemporary Palestin)中穿越到1948年,审视“灾难日”如何塑造巴勒斯坦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一年的5月15日,阿以战争爆发,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以上两位作者都展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这么多年来,企图压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各种尝试,最终都只是在为这片土地上的暴力续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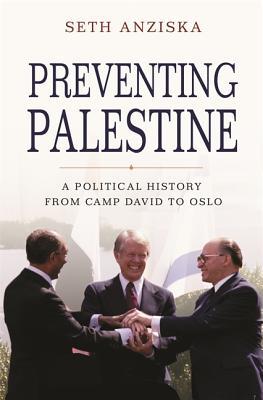
在安兹斯卡看来,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可以算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自治权进行压迫的促成者之一。他在书中再现了当年会面的情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曾试图邀请巴勒斯坦参与协商,但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毫不妥协,认为单单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有所往来都该受千夫所指。贝京原以为美国“希望避免任何与这个‘恐怖组织’的接触,毕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谋杀无辜的平民百姓,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而其目标就是毁灭以色列国”。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在1975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只要巴解组织一天不承认以色列国的地位,美国就不会与之开启协商。到了1978年,参与协商的各国也确实将巴勒斯坦的主要代表巴解组织拒之门外,并签订了戴维营协议。
这次会议中,巴勒斯坦的独立自治问题虽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巴解组织、叙利亚和约旦(二者都拒绝与以色列协商)都被排除在外,会议讨论的重要性也就削弱了,主要由卡特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斡旋,决定巴勒斯坦地区的地位问题。当时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将收复西奈半岛放在第一位,其他任何依附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巴勒斯坦主权与自治的议题,都不是其首要任务。巴勒斯坦政治权利的组织是非地域性的,以色列定居点也找到了可乘之机,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关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传统怀疑论声音越来越大。在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巴勒斯坦战士称为苏联的代理人。1981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与以色列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促进美以战略合作,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以色列借机将在黎巴嫩对抗巴解组织袭击的行动进一步扩大,转为摧毁巴解组织本身。其暴力行动包括:地毯式轰炸,导致5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在以色列控制下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里展开一场大屠杀,导致至少800人遇难。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辩称死在枪弹下的都是恐怖分子,然而当时巴解组织已经从这些难民营中撤出,也就是说被杀死的只有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以色列政府拒绝将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平民区分开来,类似的例子在安兹斯卡的书中数不胜数,毕竟要是能把二者混为一谈,那么以色列就能对任何打击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辩护了。
在安兹斯卡的叙事里,以色列和美国是这场乱局的主导力量,两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往往笼罩在其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影响之上。安兹斯卡用一个章节讨论了巴解组织的各种政治选择,不过在这里他对巴勒斯坦政治代表所面临的困难还可以阐释得再详尽些。关于巴解组织的章节讲述了这个组织是如何经过一步步演化,逐渐摆脱激进主义,成为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PNA或PA)主要的代表政党(representative party)的。1988年,身为巴解组织一员的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应阿拉法特之邀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公开表示巴勒斯坦独立和以色列国是可以并存的。这一和平共存的信号也被捎到了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上,随后协商延续到了华盛顿,这一次,巴勒斯坦代表首次受邀发声。安兹斯卡相信,这些交谈商议对未来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有十足的潜力。

然而这个希望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哈马斯激进分子引发暴力冲突,巴勒斯坦再一次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的圆桌之外。1992年底开始,在巴勒斯坦代表和美国调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屡屡受挫的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直接转向了以色列,经过挪威外交部部长约翰·霍尔斯特、公民泰耶·拉森和以色列学者的促成,在挪威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这些讨论的结果便是1993-1995年的“奥斯陆协议”。最终的结果和当年的戴维营协议一样,都远远偏离了曾经在华盛顿会谈中巴勒斯坦代表所争取的国家主权。
《遏制巴勒斯坦》主要聚焦在巴勒斯坦危机的外交史上,而《抛开火箭炮》就更接地气了,讲述了这段历史在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里留下的烙印。在书中,作者马塞洛·迪钦蒂奥没有置身事外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个社会,而是化身成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与他采访到的巴勒斯坦人产生情感共振。在一张照片里,加沙地带一个微笑的小女孩正从破碎的混凝土堆里把书本撤出来,这张图片是迪钦蒂奥报道中的一个隐喻。这位作家不再将关注点放在丑陋的剥削和压迫上,而是开始找寻巴勒斯坦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他写道,对这些个体来说,没什么东西能比故事本身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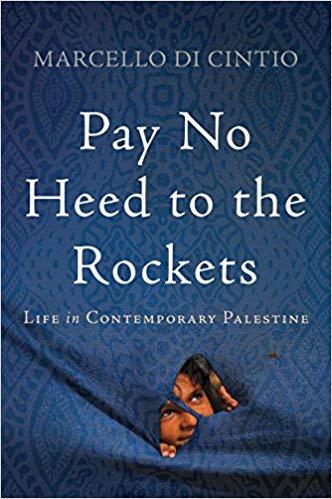
把迪钦蒂奥带到巴勒斯坦的,是他对已故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研究,这本书的标题也来自达尔维什回忆录中的一句话。1982年,以色列封锁围攻贝鲁特,这位诗人讲述了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仪式——煮咖啡,在炮火的重击下找回一点点得以喘息的安全感:“关掉火,抛开火箭炮。”达尔维什给充满争议的巴解组织戴上了人性的面孔。当这个组织还在支持暴力抵抗的时候,他是其中一员;在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夕,他辞去了职务。达尔维什的影响非常深远,当他书写诗句,批评奥斯陆协议的时候,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甚至要求他修改自己的言语。作为巴勒斯坦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在很多方面,达尔维什也受到了最多的拘束。总的来说,他的作品大多都超越了政治,在他的笔下,巴勒斯坦人民不仅仅是压迫和战争的产物。这样一来,批评的声音也就随之产生,人们有时会指责他不该在迫切的时局里把笔墨浪费在爱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迪钦蒂奥还研究了一些年轻的作家,比如玛雅·阿布·海亚特(Maya Abu-Alhayyat),他在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咖啡厅遇见了这位女作家。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玛雅的男朋友被射杀。但在她的故事中却鲜有以色列人出现,玛雅承认,这是因为她一个以色列人都不认识。事实上,迪钦蒂奥采访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遗漏。在这本书里,迪钦蒂奥还展现了另一个现象,即隔离墙不仅存在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在巴勒斯坦人民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当他跨越边界,进入“48前领土”(1948年以前属于巴勒斯坦托管地,今天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区域)时,迪钦蒂奥发现,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被自己在西岸的同胞称作“软奶酪”(Shamenet,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这部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控制下生活安逸,一出生就被宠坏了。
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正如迪钦蒂奥在书中展现的那样,和西岸相比,一些生活在“48前领土”地区的巴勒斯坦艺术家确实享有更大的自由。比如说像拉吉·巴西什(Raji Bathish)这样的同性恋作家,就能在这里发表讲述同性恋故事的作品,而不用担心遭到迫害。尽管以色列与LGBTQ群体能够泰然相处,巴西什还是拒绝将其作为以色列讲人道主义的证明。“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一边保留着隔离和占领,一边为自己对同性恋友好而沾沾自喜,这怎么说得通?”拉吉对迪钦蒂奥说。
末了,《抛开火箭炮》又回到了起点,将焦点转向了生活在加沙的人。尽管到处都是贫穷与战乱,加沙仍然是唯一一块能让巴勒斯坦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与同胞生活在一起的土地。在这里,迪钦蒂奥见到了穆娜·阿布·莎拉赫(Mona Abu Sharakh)。当年阿拉法特信誓旦旦,保证加沙会成为下一个新加坡的时候,穆娜买了他的帐。然而,2000年,以色列关闭了加沙北部的埃雷兹(Erez)边界,停止物资供应,让这个地区陷入极度的物资短缺。虽然阿布·莎拉赫就在这个地方长大,但她痛恨这里。她亲眼看着自己的人民挣扎着生活,而且这么多年来情况只是在不断恶化——2012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一份报告表示,加沙地带很快将成为一块人类无法居住的土地。但穆娜无法逃离——以色列认为加沙是一整个“敌对实体”(hostile entity),要求所有想要通过埃雷兹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先拿到许可证,而这个“恩惠”只能落在贸易商人或是希望来到以色列寻求治疗的病人头上。
在《抛开火箭炮》中,每一个场景里都能看到本地政治冲突的阴影。虽然迪钦蒂奥笔下的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并不热衷于政治,但他们带刺的用词已流露出他们所处境况对个人无可避免的影响。这种痛苦的矛盾和这片土地壮丽的景观并存。书中有一幕,作者在哈希米耶山区(Hashmiyet Mountains)徒步:“我们穿过石榴树林,树冠上点缀着猩红色的鲜花,古老的橄榄树刚结出新果,小小的,绿绿的,和胡椒差不多……幼嫩的鹰嘴豆和扁豆并肩长在广阔的田地里,周围还有烟草和埃及黄瓜。”迪钦蒂奥来到加沙地带的一个小村胡萨阿(Khuza'a),看到“混凝土屋顶支撑在破碎的房屋墙体上,歪斜着垮下来,甚至有些滑稽”。通过书中丰富的描绘文字,作者将巴勒斯坦塑造成一个充满生命和希望的地方。
《抛开火箭炮》在展现巴勒斯坦作家的时候,没有对其过度阐释,也没有将其太过浪漫化。无可否认,其中有些人确实曾经参与到恐怖主义暴力组织中,而今他们都在努力远离,与这些组织划清界限。到了最后,迪钦蒂奥回到了达尔维什身边,用他的一句话总结:“1948年的灾难不只是一段记忆,而是一场无休止的背井离乡,巴勒斯坦人在这段长路上,对生存的担忧日渐增长。”迪钦蒂奥遇到的许多作家都讲述了在一个压倒性权力不把他们当人看的情况下,生而为人是怎样的体验。巴勒斯坦人无一例外,都经受着这种冲突的影响,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被它定义的。
《遏制巴勒斯坦》和《抛开火箭炮》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更加生动的巴勒斯坦,超越了西方媒体展现的那些零碎片段——在他们的镜头下,这整个地区就只剩下贫穷和战乱。安兹斯卡给我们补习了历史背景,而迪钦蒂奥则探索了人们的真实生活经验——这里的人们流离失所,家园易主,但身份认同却没有改变。
(翻译:马昕)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