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制度官僚化、社会碎片化、政治极端化的时代,斯多葛主义的疗愈承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然而这一学派也有着阴暗的内核。

拄着拐杖写作的爱比克泰德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想长大后成为摇滚明星或火箭科学家,其他一些人想当演员或是运动员。但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却想做一个斯多葛主义者(Stoic)。起码这是玛格丽特·尤塞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的小说《哈德良回忆录》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该书发挥巧妙的想象力,以信件来往的形式回顾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写信者是晚年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收信人则是被哈德良选为继承人的青年奥勒留。哈德良虽然很欣赏他“亲爱的马可”,但也对他多有责骂。据哈德良的回忆,马可是个“简朴律己得有些过分的小男孩”,他在长大成人的历程中一直狂热地坚持实践着“斯多葛派的禁欲生活”。
哈德良——或者至少是尤塞纳尔笔下的哈德良——对我们当今的斯多葛主义热潮有怎样的意义?对许多人而言,“以斯多葛主义始”可谓为时已晚,但希望“以斯多葛主义终”的人却不在少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新版的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手册》(Encheiridion,与英文的“handbook”含义相近)和《语录》(Discourses)选编本,冠之以《如何自由:一份过斯多葛式生活的古代指南》(How to Be Free: An Ancient Guide to the Stoic Life)之名,为近来一系列的斯多葛主义的著作——包括畅销书和学术书——再添新丁。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的《如何做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用古代哲学过现代生活》(How to Be a Stoic: Using Ancient Philosophy to Live a Modern Life)和唐纳德·罗伯森(Donald Robertson)的《斯多葛主义与幸福的艺术》(Stoicism and the Art of Happiness)是畅销书一派的新晋代表作,而朗(A.A. Long)的经典之作《斯多葛研究》(Stoic Studies)和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内心的壁垒: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导读》(La citadelle intérieure: Introduction aux Pensées de Marc Aurèle)则为学术著作中的一时之选。
《如何自由》希望能在两类读者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该书由朗翻译并作序,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古典学,为知名的斯多葛主义研究专家,书中文本为希腊语和英语对照。尽管我看不懂原文(“Greek to me”为固定搭配,英语俚语,指晦涩难解的文字——译注),但朗的译文简洁明了——爱比克泰德在其教诲中便多有提倡这一品质。与苏格拉底类似,爱比克泰德一生也不立文字;幸亏其门徒阿利安(Arrian)的整理——此人后来成为哈德良的亲信之一——我们今天才能读到《手册》和《语录》。比较起来,柏拉图在其著作中经常让老师苏格拉底做自己哲学观点的传声筒,阿利安在编纂这位重获自由身的奴隶(爱比克泰德出生于奴隶家庭,幼时曾被卖到罗马为奴,赎身后才开设了斯多葛学园——译注)的学说时则基本没有借题发挥。
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和爱比克泰德——尽管两人生活的时代差了四个世纪——有一高度相似之处:二者皆为知行合一的典范。据我们所知(还不算完全证实),爱比克泰德生活中的一大知名桥段,就发生在他还是奴隶的时候。他的主人在盛怒之下想要掰断他的腿。爱比克泰德以异常平静的口吻警告主人说腿快要断了。主人对警告充耳不闻,爱比克泰德的腿应声而断,已成残疾的他仍然平静地发问:“我不是告诉你腿要断了吗?”
爱比克泰德的瘸腿究竟是因为主人的非人之举,还是源自更为稀松平常的关节炎,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爱比克泰德的奴隶生活塑造了他的哲学。如今一提起哲学,人们一般会想起高度学究气的科班操练,其参与者在同行评审的各大期刊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致力于探讨知识论、本体论、语言学或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研究这一事业的历史。稍微熟悉这一世界的人则会说,它的语言和关切通常是难解且要求颇高的。就其本身来讲,这算不上是问题:乔伊斯、伍尔夫、狄金森和福克纳的著作同样晦涩难懂,但读者们却高度珍视其中灵光一闪的真理和洞见。
阿多在与美国哲学家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的一系列访谈中提到:“哲学史家必须把位置留给哲学家——哲学家必须在哲学史家的笔下保持鲜活。这一终极任务要求他带着无畏的真诚向自己问出那个决定性的问题:‘何谓从事哲学?’(What is it to philosophize)”
阿多论古希腊与罗马哲学学校的著作颇有启发性,他指出,古代人的哲学学校迥然不同于眼下某些对何谓从事哲学的含混见解。现今的哲学院系多以各个子学科为界开设一大堆课程,而古代的哲学学校则提供阿多所称的“精神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换言之也就是提供一种门径,令你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传递改变自我的力量。
尽管学校的种类繁多——无论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论、柏拉图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均不惮于打出自己的金字招牌——但它们都承诺:学生不仅能在此学习某一套哲学,更能以这套哲学来让自己发生彻底的改变。就此而言,新生在选择学校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曾告诫我们说“从来没有人会为本体论论证而死“,然而罗马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塞涅卡(Seneca)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类似的见解。面对当时醉心于各种理论问题、彼此战得不可开交的哲学家们,他如同当头棒喝地痛斥道:“没有任何时间打口水仗……你们曾经承诺要帮助船只失事的人、坐牢的人、病人、穷人,帮助那些利斧悬在头上的人……你们如今又在做些什么?”
我们在《手册》中读到,爱比克泰德便不是那种沉迷论战的人。他告诫自己的学生:
“你们是否认为,自己在入了哲学门之后,还可以像如今这般照常吃喝,或者像原来那样发怒和恼恨?你们将要彻夜不眠,奋力工作,远离朋友和家庭,遭受年轻奴隶的蔑视,在街头被人嘲弄,在阶层、职场乃至于法庭上碰壁,总之将诸事不顺。”
对爱比克泰德来说,斯多葛主义不是消遣,而是成体系的严格操练。以令人重获新生为目标,其要求之严酷——至少从实践角度看——远超后来那些讲求玄奥道理的哲学学校。假如有人负责斯多葛学派的招生事宜,他想必会警告我们说哲学在我们深爱的职业中乃是最为困难的。
在其希腊化时代的源头及随后罗马时期的重述中,斯多葛主义始终强调理性(reason)在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的各项理性能力的指引下,女性和男性——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不会把女性贬为次等人,这是当时少有的——可以遨游世界,其间广大而不可移易的力量将我们带上高处。我们无法掌控这些环境因素,但可以掌控我们对它们的态度。对斯多葛主义而言,这些事件大多被视为“无关紧要的”(indifferent)——换言之,这些事件和事实就其自身而言无所谓内在的好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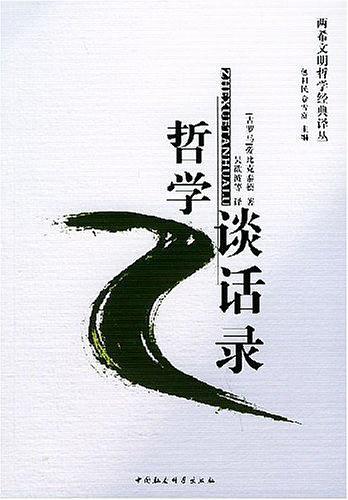
无关紧要之事也包括了一些我们平常会在意的事情,但深入反思表明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如我的车的颜色或者我的肤色等。但更具挑衅意味的是,无关紧要之事的范围也涵括了我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如果我因为肤色而过上了奴隶的生活怎么办?作为曾经做过奴隶的人,爱比克泰德的答案很淡然:深谙斯多葛派智慧的人明白,物理性的奴役乃是无关紧要之事。斯多葛主义者知道自己必须“在不取决于我们的事情上去除好坏,只将其归诸于(ascribe)我们可以决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物都是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的本质(原文为warp and woof,直译为编织物中的经纬,引申为基本原则、架构等——译注)就是如此——亦即不取决于我们,而是由自然来定夺。
关键在于,我们能决定的是自己的眼光(outlook)。借助我们的理性,我们便能把握和赞同世界之道(the way of the world)。虽然需要毕生的精力来达到这一哲学高度,但一旦我攀上了顶峰,我便会发现单纯的物质性和物理性(mere material and physical)的事物无法击破马可·奥勒留所称的自我的“内在壁垒”(inner fortress)。居于这座壁垒中,无论是元老院成员还是奴隶,无论我的贫富,也无论我是百夫长还是妓女,都可以养成斯多葛学派所称的平和之心(ataraxia,英译为serenity,汉译亦作宁静、不动心、冷静等)。
斯多葛主义对罗马人当中的特定阶层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并不出人意料。它不仅反映和强化了罗马人的传统价值观(mos maiorum)——这套价值观定义了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罗马人的生活之道——还在帝制时期为人们提供了些许的能动性和自由。如今斯多葛主义在特定阶层的美国人当中复兴,也是同样不奇怪的。在我们这个制度官僚化、社会碎片化、政治极端化的时代,斯多葛主义的疗愈承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这一角度看,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和亚伦·贝克(Aaron Beck)等认知行为疗法的创始人也受到了古代斯多葛学派的深度影响。
然而斯多葛主义也有着阴暗的内核——尤塞纳尔笔下的哈德良便窥见了它。他虽然很欣赏爱比克泰德的榜样作用——哈德良说,这位残废的老人似乎“享受着一种堪称神圣的自由”——但皇帝也告诉马可·奥勒留说,他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人及其哲学。哈德良若有所思地表示,爱比克泰德“放弃了太多东西,我很快就发现一味克己(renunciation)对我是万分危险的”。皇帝意识到了某些东西。对许多人而言,爱比克泰德全心全意认同的那种斯多葛式克己生活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范围。他平实地将斯多葛式生活比喻为乘坐一艘由自然指挥的船远航。现实生活中的航海者可能会在某个港口停泊一阵,以获取“一点贝类和蔬菜”,但他也必须做好抛下这些东西并立即返回船上的准备。与此类似,在生活的航船中,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也可能在某次停靠时邂逅“娇妻与爱子”。嗐,可别迷恋这些小玩意儿,“一旦船长呼叫你,要冲回船上并且头也不回地抛下这一切。”
在《手册》中,爱比克泰德——提醒读者一下,他是个没有小孩的单身汉——列出了一大堆类似的例子。要是我期望妻儿能正常生活——且不论舒坦与否——爱比克泰德会说我太“愚蠢”,因为我希望把那些不取决于自己的东西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要是我的妻儿里有人过世了,我决不能说“我失去了”她们。她们首先就不归我所有,因此我应该说她们被返还了(have been returned)。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理查德·索拉布吉(Richard Sorabji)等古典学家对斯多葛式克己的后果和代价提出了恰当的疑问。与我们所爱的人或事物建立依系(attachment)不仅有好处,而且是必要的;若没有这些依系,我们也许能享有更大的安全感和更持久的内心宁静,但也会体验到较少的人性(less humanity)。简言之,就是我们会活得有点不成人样。
这本小小的手册还引发了不少大问题。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无关紧要之事,这是否会鼓励一种政治上的听天由命态度(resignation)?斯多葛主义一棍子把一大堆事情打成是无关紧要的,是否有意无意地与某些我们有能力且应当予以抵制的奴役形式形成了共谋?期盼自己的孩子能够正常生活且能活出灿烂人生,真的是愚蠢的吗?当你放下爱比克泰德的书,你也许会想要扪心自问一番:自己究竟是想要与哈德良为伍,接纳自身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并哀悼挚爱的安提诺乌斯(Antinous,哈德良的男宠,20岁时不慎溺水身亡——译注),还是追随“亲爱的马可”,试图以热爱纯粹的人性(mere humanity)来凸显自己的脆弱性?
本文作者罗伯特·扎勒茨基任教于休斯敦大学荣誉学院,学术特长为法国思想史。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