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人的生命”到“我们的生命”,一方面让声讨枪支暴力的运动具有了跨种族的意义,同时却也揭示了美国种族问题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根源。

按:从“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珍贵”),到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校园枪击案引发的反对持枪运动,人们讨论的关键点总是不离“种族”。然而本文作者认为,看待种族问题,不能仅仅将眼光停留在黑人的种族身份上,而应该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广阔的历史时空脉络中理解其多重身份的处境。文章也结合了美国研究种族问题的最新成果,为超越单一肤色问题、综合理解美国种族政治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参照。
文 | 陈映芳
(《读书》2018年11期新刊)
作为一个并非研究美国历史或种族问题的学者,要想理解美国的种族矛盾,不是容易的事。但种族问题,尤其是黑人问题在美国是如此突出,书店、图书馆中,到处有整架整架的书进入浏览者的视野,有关民权问题的各种宣传招贴以及各类艺术作品更是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各种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重要主题,不由得人不关注。

“黑人生命珍贵”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十七岁的黑人少年崔文·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罗里达州桑福德被社区的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认为形迹可疑,经尾随和争执,最终协警开枪将马丁打死。次年七月十三日,佛罗里达州法院做出判决,协警被宣判无罪。枪击事件及这一判决引发了佛州的暴乱和全国范围的抗议运动。在随后几年中,伴随着一系列的导致黑人丧命的警务事件的发生,“Black Lives Matter”在网络上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黑人平权运动。
“圣路易斯历史中的种族”
黑人民权运动的组织者除了致力于揭示、控诉黑人遭白人歧视的现实,还通过对美国种族问题历史的持续重构,来积聚社会运动的道义资源。在左岸网站(left-bank.com)的一份“黑人生命珍贵阅读目录”中,笔者看到,所列的八十来本书中,这样的种族压迫、种族平权历史,大致被分为“民权历史”“当代民权议题”“探索种族的小说和故事”“警察和监禁”“圣路易斯历史中的种族”这几大类。“圣路易斯历史”一词,让不谙美国地方史的笔者心生好奇。之后初步了解到,这个地处美国内陆中心地带的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因在国内战争后和上世纪初有大量黑人迁入,是一个重要的黑人聚居城市(黑人占总人口比例一九一〇年是6.0%,六十年代为26.8%、二〇〇〇年达到51.2%)。在这个城市,包括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种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还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外流(从一九五〇年的八十六万人下降到二〇一五年的三十二万人),以及城市的迅速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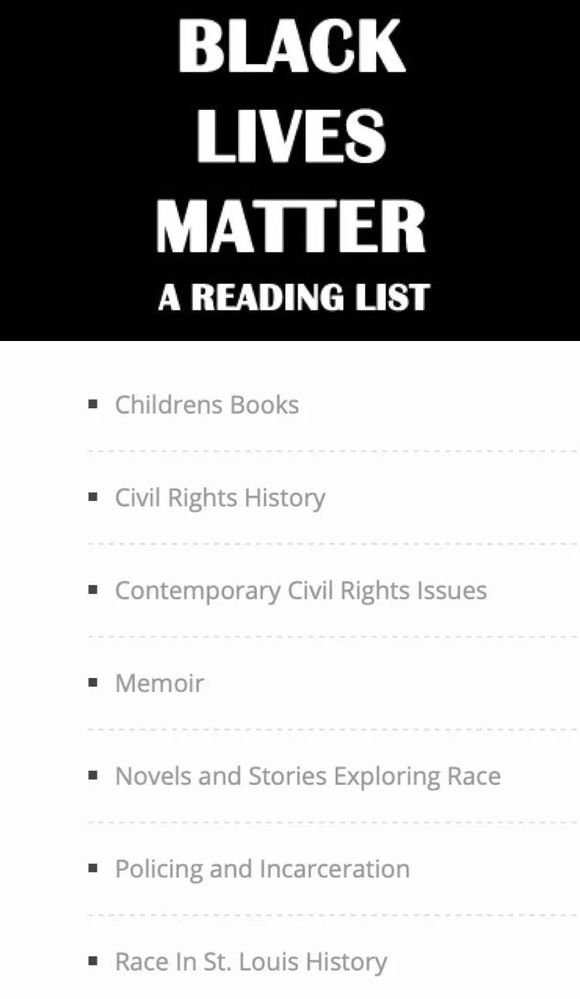
显然,这份参考目录的设计者,意图通过对圣路易斯这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的解剖,让人们了解美国种族关系的演变脉络。事实上,“圣路易斯历史”在美国完全不是一个孤例,甚至也算不上种族歧视的极端个案。在二〇一一年一份由密歇根大学公布的美国十个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的排名中,圣路易斯仅位列第七。
“为了我们的生命!”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美国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发生枪击案,一批学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在网络上、公共媒体上、集会上发出了强烈的声音——“够了!”“再也不!”他们要求国家立法控枪,以此扼制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为此他们与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发言人和一些政界人士面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公开辩论,最后他们还发起了全国规模的中学生大游行,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并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首府华盛顿——“为了我们的生命而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举行了由上百万民众参与的大型集会。
这一次,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代表们还自觉地将种族问题带入了生命安全议题——他们指出,这一次枪击案之所以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是因为这所中学地处富裕社区,而遇害学生主要是白人,而他们希望能利用自己拥有的这一种“白人的特权”,让世人关注到那些被社会长期忽略的遭枪击的黑人学生,以及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由于这些学生领袖的努力,最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的华盛顿集会上,十一岁的非裔女学生、在弗吉尼亚州就读五年级的考特琳·阿林顿(Courtlin Arrington)代表受枪支暴力侵害,但被媒体忽略的非裔学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此外,活动组织者还请来了马丁·路德·金的孙女尤兰达·芮妮·金(Yolanda Renee King)发表了公开演讲,这位九岁的小姑娘说,她梦想有“一个没有枪支的世界和时期”。

从“黑人的生命”到“我们的生命”,学生们将枪支暴力问题从种族问题扩展到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问题,这一方面让声讨枪支暴力的运动具有了跨种族的意义,同时却也揭示了美国种族问题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根源。
如何从跨种族的角度,来讨论黑人的问题?这不是能够轻松驾驭的政治议题。在佛州事件的风口浪尖上,身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的奥巴马被记者问及对事件的看法时曾表示:“如果我有个儿子,他可能就像崔文·马丁一样。”他直接将事件症结指向了肤色问题。总统的发言招致了警界的不满和舆论的各种质疑。一些批评者认为,存在于美国黑人居住区的种种问题和警务事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总统避开社会结构的因素而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为白人警察的种族歧视,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激化种族矛盾。也有一些分析家认为,相比较于当初马丁·路德·金对黑人状况背后的社会不公、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今天“黑人生命珍贵”组织的领导成员们过度聚焦于种族关系,体现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迷茫甚至倒退。
到底是应将板子打在白人的种族歧视上,还是应该将问题归结到阶级结构上去?换句话说,一个以种族身份为基本特征的群体的社会状况,归根到底是因为其种族属性导致了阶级地位的低下,还是因为其阶级地位导致了人们对其肤色的偏见?事实上,在认知层面,人们即使对种族主义抱持警觉,或有意识地与教条式的政治正确保持距离,也很可能掉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无解的因果论中去。

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是跨族群的阶级论方法。白人中不乏贫困者,而黑人中产阶级的兴起,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在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后,已经有美国进入了“后种族主义时代”的说法。但是,就如同制度上的政治平权并不能消灭有色人种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受歧视状况一样,黑人内部的阶级分化,也不能掩盖总体上黑人处于社会下层的严峻事实。如何解释种族类别与阶层结构之间如此突出的相关性?这构成了研究者的挑战性议题。
种族是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群体属性,这虽然可说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人类学知识,但是,具体到那些具有鲜明的社会差异,特别是显著的阶级落差的族群以及族群间矛盾,研究者如何能对其社会性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释?在这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为我们贡献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
值得推崇的文本之一,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阿尔文·本特(Nell Irvin Painter)出版于二〇一〇年的著作《白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人类有关“白色”的概念史以及白人的社会建构历史,从古希腊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这项全景式的研究,以二十八章的篇幅,梳理了自希腊时代以来,欧洲及美国的“白人”种族是如何形成、如何被确定的。这其中不仅有对经济发展历史、奴隶制历史、移民史等等的重新梳理,还有对社会的白人观以及人种科学、人类社会学等等在白人种族被建构的曲折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检视。作者以生动的历史事实和充满建构性的分析,说明了在最早的欧洲社会,包括希腊人和罗马人,原本并没有种族(race)的概念,也不存在按族群和阶级将人分类的情况。那时处于底层的是奴隶,而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奴隶通常来自被征服的欧洲国家——亦即白人社会的内部。奴隶制与种族联系到一起,是相对现代的事。另一方面,在欧洲内部以及美国,对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白人”的科学认定,以及社会的白种人观念,是随着一次次移民潮以及各国的法律与社会的演变,同时在种种“人种科学”的介入下,在十九世纪渐渐形成的。

《白人的历史》因其对传统种族观的冲击力,曾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在知识界、文化界也收获了很高的评价。而在美国史学界,类似于这样的探讨种族与阶层间关系的复杂历史的研究,还有不少。像《基督徒奴隶与穆斯林宗主》(Robert Davis,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一书,揭示了历史上大量白人曾沦为非洲奴隶的历史: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曾有百万欧洲基督徒遭北非穆斯林奴役。另外像《白种垃圾:美国四百年阶级黑历史》(Nancy Isenberg,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一书则让读者了解到,在英国历史上,曾有各种污辱性的名词被用来形容底层的白人,如“人民渣滓”等等,十九世纪更出现有小册子《南方穷等白人》。底层白人曾被视为无用的“白色垃圾”。事实上,那些最早来到美洲的开荒者,有不少正是被英国政府和社会当作“不正常的新人种”而驱逐出来的底层白人,包括流浪汉、小偷、叛军、妓女等等。
黑人群体在美国,何以会整体上成为“下层社会”“高犯罪率”等的同义词?尽管在历次民权运动中,他们已经一步步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甚至因为一些社会权的平权政策,他们还获得了比其他种族更优惠的政策照顾。
要理解这一问题,如“圣路易斯历史”(以及“芝加哥历史”等等)这样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不同于一般社会进化论或文明论以及传统阶级论的认识路径。将一个族群或阶级置于具体的社会时空之中,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影响了他们命运的多重因素。
作为下层移民的黑人群体。美国本是移民社会,但与其他族群的移民史有所不同,由奴隶贩卖市场被输送到美洲大陆的黑人,从一开始,其族群的整体身份就被定位于底层移民。而在废奴运动后,他们虽然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并开始大量迁入北方和各地工业化城市,但始终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卷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之中。在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过程中,黑人曾有数次较大规模的迁移潮——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作为美国社会中人数庞大、曾长期动荡不安的下层城市新移民,黑人所遭受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城移民、城市下层新移民、国际移民群体那里,同样可以看到的社会困境。

作为产业工人的黑人。由南方的奴隶主庄园,到北方的新兴工业城市,美国的黑人群体曾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种种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量白人奔赴战场而黑人不被允许参战,他们因此在工厂,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获得了劳动机会,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战后,随着白人士兵回归社会,并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优待(包括教育、就业、住房资源分配等),加上军工产业的萎缩以及之后的产业转型,制造业工厂向海外转移等等,作为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黑人,开始遭遇失去工作机会的命运。
城市贫民区中的黑人。战后以来,郊区化、城市/道路规划、都市更新(士绅化)运动等等,一波又一波的土地/城市开发运动中,政府与土地开发商联手,不断将地价、房价推高,这让陷于失业的黑人贫困层因无力购房而只能聚居于旧城贫民区,或者被安置于远远隔离于中产社区的公共住宅之中。显而易见的是,空间区隔已经成为今天种族隔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不是黑人造成了贫民区,而是高度分异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住房排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市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让黑人困顿于问题社区,并因此成为永久的问题种族。

黑人青少年。青少年成为权利弱势群体,同时又被视为潜在的问题群体,这是现代社会中普遍的世代现象。在美国,曾有社会学家的实证调查说明:不同阶层之间,青少年的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差异,明显不同的是不同阶层的越轨青少年所受到的法律惩罚的比例。其原因之一,是下层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更多暴露于世,也更可能受到司法的惩戒。此外,在现实中,黑人青少年不仅多属于经济社会的下层,而且大多身处公共服务资源匮乏而犯罪率高发的贫民区,且有很多人成长于问题家庭。这样的青少年不只是警察眼中的高危群体,也是一般民众(经由大众媒体和影视作品的影响)眼中的潜在犯罪者,而肤色和社区,通常是人们识别他们的主要标识。
除上述这些之外,应该还能列出其他种种社会因素变动与美国黑人社会状况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习惯于强调黑人种族的单一身份,而忽略了他们的其他身份。他们的多重身份深嵌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时空结构之中,持续地建构并强化了他们的种族属性和阶层地位。
虽然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种族歧视、阶层分化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非常严重,枪支暴力也成为社会的一个顽疾,但不可否认,社会公正、种族平等、公民平权等等,这些作为社会的共享价值,很少会遭到公开的否定,民权运动的历史成果也有目共睹。只是一旦涉及公民的持枪权问题,社会的分裂清晰可见。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尽管有关校园枪击案及警民间、平民间各种枪击案的伤亡统计数触目惊心(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每年约有两万人丧命于枪支暴力。另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仅二〇一六年就有三万八千六百五十八人死于枪支),可无论是黑人的城市暴动、“黑人生命珍贵”的社会运动,还是跨种族的一次次全国性抗议运动 ——如二〇〇〇年爆发的“百万妈妈大游行”运动中,曾有七十五万母亲走上街头,呼吁枪械管制,但所有这些似乎都难以推动相关法律的改变。

公民的持枪权,在美国受到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显然,它与国民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和国家的最高准则有关。从全国步枪协会发言人以及支持公民持枪权的人们的各种表达中多少可以了解到,观点的分歧涉及了现代国家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国家是否可以垄断暴力?如果国家不能确保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免受他人侵害,公民个人能否拥有暴力自卫权?还有,一旦国家侵害个人生命权或财产权,公民是否可以暴力抵抗?
与这些问题相关联,除了公民的持枪权,美国许多州还立法保护公民以致命武力保护自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类自卫法著名的如公民可以在家中自卫的“城堡法”,还有在家以外地方自卫的“不退让法”。这些年来,一系列平民以武力自卫而致人死亡事件的发生,曾引发人们对法律的质疑,但基本人权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相关的法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接受,从二〇〇五年仅有的佛罗里达州扩展到目前的二十五个州。甚至,当公众面对一些地方民兵为保护私有财产或地方利益而以武力正面对抗国家武装的事件时,也不乏理解和同情。
无论是社会基本的人权观、社会公正价值,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及相关法律,它们内部往往充斥着种种张力和矛盾。正因如此,各种社会团体的禁枪/控枪主张一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是在奥巴马时期。虽然在实际的枪支暴力事件中,身处社会困境中的黑人往往是最容易受侵害的群体,但显然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个种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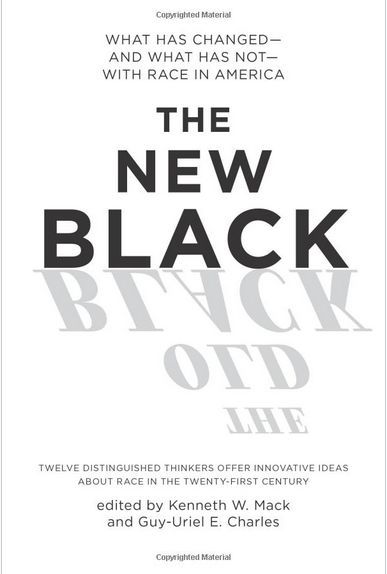
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及其黑人的处境到底处于怎样的复杂局面?在由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斯·麦克(Kenneth W. Mack)和杜克大学法学教授盖-艾里·查尔斯(Guy-Uriel Charles)共同主编,由十二位思想家、社会学家、种族历史学家和著名评论家等参与撰写的《新黑人》(The New Black:What Has Changed—and What has Not—with Race in America,2013)一书中,这批被称为全明星阵营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从民权理念出发,分别对美国既有的民权运动框架、美国种族辩论的新界限、“黑人生命珍贵”运动与总统政治/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种族格局等等,提出了种种新颖、尖锐的看法,其中讨论到的“种族政治”概念及相关理论,从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给出了超越黑白思路去思考种族问题的新思路——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不仅需要有对黑人底层生活的深入了解,更需要有相关的学术基础,这些已非笔者力所能及。
在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思想深度且富有学术传统的研究领域,依个人管见,多存在于学界对本国最复杂、最具悲剧性的历史/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就如同德国的大屠杀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研究等等——如果这个国家拥有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的话。无他,这样的问题理应会吸引这个国家具有人文情怀和思想性的学者们一代又一代地持续投入其中,这样的学问也极可能生产出具有深刻反思性的学术成果。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不仅是浮浅的,也很可能是有害的。
但不无悖论的是,在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以学习他国优秀文化为己任而远赴世界各地留学/访学的中国的学子学者们那里,最吸引他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议题却是中国研究。已有研究者以详尽的资料说明,二十世纪上半期留美生有关中国题材的博士论文共计三百一十四篇,占同期留美生博士论文总数的23.74%,数量相当惊人。对此学术现象,今天的分析者站在理解之立场,大多认可了民国学者们自己所做的解释:民族危机背景下,那样的学术旨趣彰显了留美生学以致用、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现实观照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以及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深刻影响(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以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心的考察》)。

时过境迁,可无须讳言,中国出外留学或访学的学生学者,所做研究至今仍多以“中国的”问题为议题,尤其是在经验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亦可以如民国留美学生那样以“利用他们的前规,做我们方法的借鉴”的说辞来自辩,但不能不意识到,“以学术报效国家”,遮掩的是不无尴尬的事实:我们大多缺乏对超越于母国或其他(作为职业工作对象的)具体国别之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社会”的强烈的价值关心和探索兴趣,而且也往往不具备足够的问题想象力、思考力,以及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
如此,不无遗憾的是,习惯于在世界各国学术边缘地带寻找容易上手的中国议题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不仅回避了对所在社会展开专业化研究的学术挑战,由此也很可能放弃了对所在国最具深刻内涵的学术领域的真正了解,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以世界为镜子来认识自身社会的能力养成的机会。须知,每一个他人身上都会有自己,人类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孤例,世界各国的进步源泉或悲剧因由,在本质上都具有相似性。
这不仅是我们一代学者的局限,也是中国知识界的短板。笔者真诚地寄望于年轻的学子和学者,期待他们的超越。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