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立的“斯汤奇文学奖”将产生第一个获奖者,希望能借此鼓励惊悚小说择除对女性施暴的情节。对此,《幽灵墙》的作者莎拉·莫斯向我们讲述了她是如何书写暴力的。她认为,重点不在于我们应不应该写父权制的暴力,而是如何书写这种暴力。

莎拉·莫斯:“在我们眼里,最有趣的故事总是牵扯到权力与虐待。”摄影:David Levene
“斯汤奇文学奖”(The Staunch prize,Staunch有“止血”、“坚定”之意)的第一个短名单即将出炉,该奖项旨在嘉奖“没有女性被攻击、被跟踪、被性剥削、强奸甚至谋杀”的惊悚小说。这个新设立的文学奖项成功抓住了公众对施暴于女性的行为的愤怒。长期以来,作家们总是会否定“有人已经框定了小说讨论的议程”,还有种说法——描写加之于男性的暴力就没那么大的问题,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不过即便如此,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虐待女性的情节能让小说销量更好看些。
写作这本新书的时候,我 [指本文作者莎拉·莫斯(Sarah Moss),著有小说《幽灵墙》(Ghost Wall)] 脑中的主题就是暴力。过去,我写作的主题往往是家庭不睦以及破裂的关系,但尽量避免描写肢体上的伤害。而在《光之躯》(Bodies of Light)中,年轻的女孩随时都会受到伤害。在构想这些情节的时候,我就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想呈现一种带有诗意的痛苦,不想岔开读者的注意力,忽略人物不断沉积的心理上的痛苦——毕竟那些淤青、抓挠和尖叫的场面,你随时随地都能在大荧幕上看到。除非你是个医生,否则生理意义上的暴力就不那么重要,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那些文学结构,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施暴者会对他人造成肢体伤害,并由此衍生出代际创伤。一部电影或者一本小说如果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粉刷卧室墙壁时摔下梯子、撞坏脑袋,这样的情节并不会吸引多少人;但如果这个女人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个地方,受到了一个头顶棒球帽的男人的攻击,故事就变得生动起来了——在我们眼里,最有趣的故事总是牵扯到权力与虐待,而不是生理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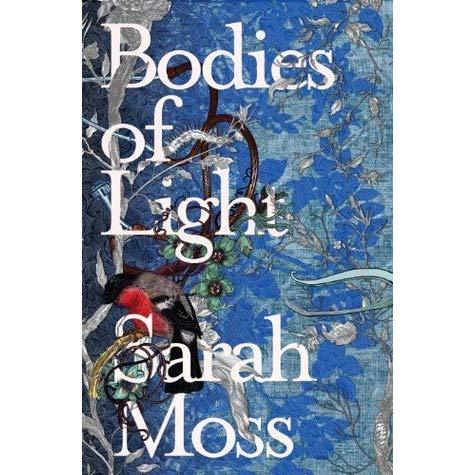
从某种程度上看,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小说中的暴力因素往往火候太过,而且对情节发展没多大裨益。我大可以这么写:“球棒敲在她长着一头金色秀发的脑袋上,重击之下轻轻弹起,敲击声令他都有点错愕。他琢磨,血在哪呢,因为她刚涂上蓝色的墙壁上已经溅上了猩红。然而他没有如愿以偿,女人开始摇晃,带动着脚下的梯子,歪斜,倾倒,她掉了下来。木地板上沾满了油漆。他想,覆水难收。这时候,男人还是想亲眼看到鲜血,于是把匕首从皮带上抽了出来。”我大可展开想象,从侵犯者的角度给读者们创建一种攻击美学,透过那个棒球帽男人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我也可以用暴力行为玷污整个家庭生活,让你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看待她,而不是与她同一战线。在这个场景中,这个身处险境、痛苦不堪的女人不过是一个工具,为的是让男人的内心世界外显出来。我还可以继续想象:“她转过身来,看到他扬起的手臂,看见这个阴影映在自己薄荷绿的墙壁上,升起,挥舞。这是一击棍棒的敲打……她想,天呐……棒球棍。哦,但一切都太迟了。”同样的事情你会理解的,但并不意味着要将其呈现在你眼前。如果读者们对权力的幻想也被否认了,故事就不那么有意思了。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看,遭到痛击绝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更具破坏性的是另一个事实:你就是那个“能够”被打击的人,那个本应该爱你的人——也许确实正在爱着你——同时也想要伤害你,并且他还给自己颁发了许可证,只要自己想要,随时随地都能伤害你。这正是我想要写的东西:讲述一个成年女孩的故事,而她的父亲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控制,他坚信真正的男人都得动武。

我暂时给这本书起名为“法尔玛库斯(Pharmakos)”,也就是在危急时刻被逐出古希腊的恶灵化身。我明白我要出版这本书不能扣着个希腊语的书名,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把它和化学扯上联系。但写作越往深处去,我就越执着地把目光放在替罪羊的身上,也就是被牺牲的受害者、罪恶的背负者。许多家庭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色,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在社会群体乃至国家中亦是如此。总有人要负起罪责,而这个人就是那些开启争论的人、那些犯下罪过的人、那些讲述不忍卒读或者难以置信的虐待故事、与此同时赚得所有好处的人。而这个人不会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因为我们责任共担。
于是我们便选择另一个人去责备,但并不会杀了她,也不会将其流放远方,因为这样一来生活中就会出现一个缺位。我们把她留在身旁,这样自己一旦发火了还能有地方出气。但这个替罪羊就很难做了——并不是因为会受伤(虽然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是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你的错。那个造成伤害的人也不好过(虽然没有受害者那么难受),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所说所做所想的一切都必定是完美无瑕的,否则这整个系统都得崩溃。
实际上,小说创作不会死抠结构。你不会想着要写一个“关于国家身份认同”或者是“关于家庭暴力”的故事,虽然这不失为可行的解读角度。当我们谈到小说内容的时候,会说我在写一个关于简·爱和罗切斯特的故事,或者是伊菲麦露和奥宾仔(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小说《美国佬》中人物)的故事,对我而言,就是西尔维和父亲比尔的故事。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讲述一个关于替罪羊和暴力的故事,就应该围绕比尔伤害西尔维展开,然后让读者们自己去想象这种阶级之间的战争和“有毒的”男子气概。萨利·温莱特(Sally Wainwright)执导的英剧《幸福谷》(Happy Valley)中就呈现了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女权主义应当如何展现身体被侵犯的痛苦?我们要如何才能得体地写出男人对女人造成的伤害,同时又避免沦为虐待狂窥阴癖的养料?温莱特在视觉媒体领域工作,在这里,凝视就是一切。她的处理方式就是避免具有视觉冲击力、吸引力的画面,另一方面,不管是何种身体创伤,她都坚持在真实的时间长短内呈现。温莱特片中的暴力镜头让你不忍直视,确实也理应如此。我也会试着让读者们站在西尔维的角度,超出痛苦的场景之上,看其所见,听其所闻,想其所思,再将目光转向别处。读者们应该能够理解,在你听不到、看不到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看到暴力场景会感到不适,我和我的编辑麦克斯·波特(Max Porter)也因为这一点对封底内容进行了好些有意思的讨论。第一版的想法是“可怕的高潮”,但我提出了质疑,我知道这样一来有些读者就会觉得他们买的这本小说太血腥。那“令人不安”或者“值得警醒”呢?我提出了几个柔软一点的话术,麦克斯则认为:“我觉得‘可怕’这个词恰恰表明了我们在这个价值亿万美元的图书行业的立场,现在的小说中,女性被折磨、被杀害,女性的痛苦几乎成了一种用来消费的娱乐,读者们的神经也受到了挑战,他们该开始思考,真正可怕的到底是什么。”麦克斯是对的,西尔维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但更可怕的是她自己并没有那么恐惧,因为这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不过我还觉得,有些读者可能会期待血腥和尖叫,如果发现书中这样的情节达不到期待,不免气恼。最后我选择了“悲惨”这个词,可即便如此,网上还是有些书评抱怨故事不够暴力、不够残忍,仿佛这些读者花了一大笔钱,满心期待一场角斗厮杀,最后却发现自己置身歌剧院中。
我们需要阅读恐怖、记录创伤,在站在施害者角度展开想象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受害者。与我们一样,施虐者也是有故事、有历史、有血肉的人。文学中大量的暴力也可以是一种幽默与戏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退回到18世纪,哥特文学肇始,而阅读这种可怕的文学亦有其门道:如果有一小群人拥有所有东西,而且几乎具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绝对权力,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干出的事能糟糕到什么程度。让我们在阁楼里与女佣们嬉闹,互相撺掇着对方走进酒窖,派对结束,再让我们一把火把这一切烧掉。女性哥特文学以探索家庭关系和暴力为显著特点,几百年来,这些故事的恐怖之处都是结构性的,而非表现在戏剧性上。在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中,少女凯瑟琳痴迷于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中的灵异和谋杀情节,以至于连蒂尔尼将军误以为她是富家千金、贪图她的钱财都没看出来。还有一只怪物,但他就坐在桌子的首席位置,而不是躲在窗帘背后。当年轻的简·爱在红房间里看到那个“幽灵”的时候,感受到庞大的威胁是真真切切的。而她眼前的这个恶魔并不是任何非自然存在,其根源就在于,在富有的舅妈和表兄弟姐妹们面前,这个孤女的脆弱展露无遗。诡异的东西也可以很有趣,比如说我就很喜欢读到古怪的幽灵在树上游荡的场景。
女权主义写作出现了一种新的传统,它往往是怪诞的、哥特式的,控诉了父权社会的暴力和残忍,将厌女症和恐同的因素放到她们的结论中。我脑海中浮现出菲奥娜·莫兹利(Fiona Mozley)的《艾尔迈特》(Elmet)、索菲·麦金托什(Sophie Mackintosh)的《水疗》(Water Cure),以及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暗黑系小说。但要是单单讲述关于仇恨的故事,把我们对于看到年轻貌美者承受痛苦的这种迷恋撇在一边,小说也是不完整的。我感到柳原樱(Hanya Yanagihara)的《小人生》(A Little Life)不忍卒读,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在孩子身上施以极端暴力已经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策略,意在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算是对作者坚持不懈的犒赏。只要孩子们仍在受伤,作家就必须描述这种伤害,然而要缩小窥阴癖的空间并不是别无他法。我很期待斯汤奇奖花落谁家,但对我来说,设置这个奖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应不应该写父权制的暴力,而是如何书写这种暴力。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