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43年,小说这种形式对于麦克尤恩来说仍有着持续的吸引力。他说,小说是“一项古老的发明,不需要电池驱动,也无需高深的科技,但在道德上和审美上却高度复杂,当它登峰造极之时,美得无以伦比”。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
“今天是我来中国的第二天,这两天我一直在谈论自己。而当一个人不断谈论自己的时候,他学到的东西很少。当我能不说话的时候,我就能学到东西了。” 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芝加哥中心的的会议室里,当被问及第一次来中国的观察和感受时,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不失风趣又有些无奈地回答道。这是他来北京的第二天。这一天下午他参加了“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致敬典礼,之后是媒体群访,第二天下午他马不停蹄赶去一场与中国作家格非和评论家李洱的对谈,在这期间又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接着,他将到达上海,等待他的仍是一连串的活动与采访。
作为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如今70岁的麦克尤恩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成为了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盛事。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不甘落后,争抢报道和采访的先机;邀请他来中国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每天在公众号发布麦克尤恩最新日程,供广大读者了解;而他的粉丝也如朝圣一般,在这个寒风乍起的秋天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在各项活动的问答环节里,他们高举手臂并激动地起立,对麦克尤恩的作品如数家珍。
也不必对这番盛况感到意外。毕竟,如果我们回首麦克尤恩的创作生涯,会发现它的确可以用“风光无限”四个字来形容,在活动海报上,麦克尤恩甚至被冠以了“英国文坛神话”的盛名。1975年,他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这本收录了八个故事的短篇小说集中,他从童年、青春期、青年等不同时期的男性视角出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能力揭露了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界地带。次年,该书获得毛姆奖,麦克尤恩在文坛一举成名。在那之后,他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创作节奏。在迄今为止43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已经创作了18部小说(其中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和5部剧本。2001年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赎罪》在获得全美书评人大奖的同时,也被改编为电影,斩获了2008年金球奖最佳影片奖,麦克尤恩的名字在全世界流行了起来。他是电影改编的幸运宠儿,也从未被国际各大文学奖疏远。从最初的毛姆奖开始,麦克尤恩已先后斩获了布克奖、惠特布莱德奖、全美书评人大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与此同时,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物。伴随着在主流文学圈不断获得的肯定与嘉奖,麦克尤恩已经成为了图书市场上常青不败的销量保证。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梳理了麦克尤恩北京之行的两场活动——在“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上发表的演讲以及次日和格非、李洱的对谈,并结合他于26日在北京接受媒体群访时的回答,希望向读者一表他关于小说作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学形式的看法,以及对于数字革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科幻小说的种种思考。
麦克尤恩对小说这种文体充满信心。在43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坦言也有一些时刻会让他质疑小说和写作的意义,但这种动摇并不会持续太久。小说创作对于他来说仍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在麦克尤恩看来,小说是“一项古老的发明,不需要电池驱动,也无需高深的科技,但在道德上和审美上却高度复杂,当它登峰造极之时,美得无以伦比”。
那么,在如今这个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在这个我们足不出户动一动手指便可尽知天下事的时代,小说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在27日题为“大众媒体时代的虚构写作”的对谈活动中,他与格非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格非想到了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提到的问题。在卢梭生活的年代,社会话语、机制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已经让他难以忍受。一方面,个人存在的意义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在发声。这样一来,文学、艺术都是在同行之间取悦彼此的舒适氛围中被生产出来的,但这样的氛围不仅不能帮助确立自我,反而容易造成自我的弱化。因此,卢梭当时对文学艺术抱有强烈的排斥态度,唯一让他有好感的艺术形式就是小说。在格非看来,卢梭对于小说这种形式的好感或许可以在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那里找到一些线索。卢卡奇曾将现代小说定义为“上帝死了以后的史诗”,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叙事文类,小说是一个新的产物。对小说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作为作者的观念,而是小说里面的人物作为他者的思维和情感。作者通过叙事者,和小说人物与读者在一个非常开放的场域里面进行交流。如此一来,小说不是教训和说服,而是提供一种可能,使得各种不同的声音、思维和情感在一种尽可能排除偏见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在格非看来,这是小说这个独特的文体带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格非认为,在麦克尤恩的作品《赎罪》中,曾有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在小说的某个章节里,叙事者曾感叹说,这个世界上有二十亿人(故事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十亿人都忙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回到当下,我们如今面临的众声喧哗的情况与卢梭当时感受到的困境极为相似。在大众传媒时代,大家都充满了表达欲,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相对的,无法说服彼此。在今天的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观点、价值层面的观点上,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有的时候很难通过说服和争辩加以缓解。但格非坚信,小说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交流的方案——也许我不同意你的价值观念、不同意你的政治态度,但是小说提供了可以包容你的情感、你的价值、你的政治信念的一个模拟的空间。它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后果: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会被你的叙事所打动,从而对我自己固有的观点进行反思——这恰恰就是小说的优势所在。
麦克尤恩在他26日的演讲中也提到,小说具有交流沟通、理解他者的功能:“要想进入别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容纳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说依然是我们最好的途径、最好的工具。小说家是在他人的思想之海上扬帆的水手。电影直观易懂,也很引人入胜,但它并没有像许多人预言过的那样让小说消亡。只有小说能呈现给我们流动在自我的隐秘内心中的思维与情感,那种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觉。”
而如果我们将“他者”的维度扩大——在这里,他者不仅是与写作者不同种族、国家、时代、地域的人,同时也可理解为在这个科技日益发达、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可能创造出来的全新的有意识体——小说仍然能够成为人类与有意识的他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工具吗?麦克尤恩对此抱有十足的信心。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小说将是人类理解全新有意识体的最佳途径,”麦克尤恩说到。
“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我确信它可以进入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头脑中。因此,它也可以进入一个类人机器人的头脑中。小说可以尝试着预演我们未来的主观意识,包括那些我们所发明的头脑的主观意识。在我们争论究竟应该给我们的造物注入何种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并阐明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麦克尤恩继续展望了属于人造人的未来,“而当一个人造人写出了第一部有意义的原创小说——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这将确凿无疑地证明一件事:一种全新的,有意识的造物已经降生在我们身边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将就此展开,无论它带来的会是美好还是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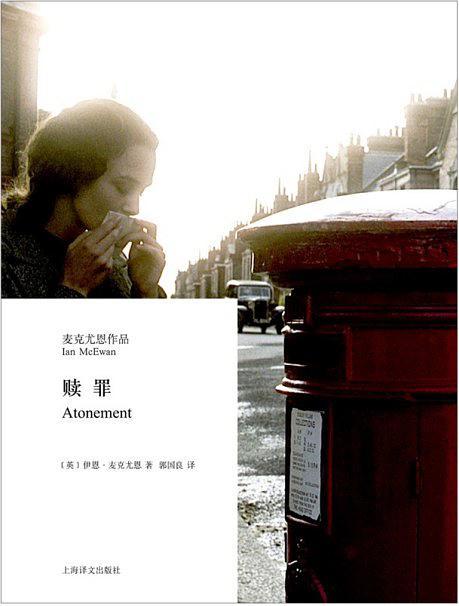
麦克尤恩这场演讲是以数字革命为主题的,“我想要开启一段短暂的路程,踏入不可知的未来。我的出发点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已经发生的一项深刻的改变,而它影响的是这颗星球上的绝大多数成人,还有孩子。当然,我所说的就是数字革命。”这位自称是老派的、成长于模拟信号世界的、使用公共电话亭通话、了解信息时求助于书架上百科全书的“报纸瘾君子”式的人物,如今也被催促着慌忙笨拙地过渡到一个数字宇宙。
“但这仅仅是开始。”麦克尤恩说,“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目睹了计算机科学的一场革命。人工智能时代已经降临。25年前,一台计算机打败了一位国际象棋大师。那台计算机的程序中塞满了数千场象棋赛。每走一步棋,它都会演算出每一种可能性。但就在去年,另一台计算机仅仅被输入了比赛规则和要求取胜的指令。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比赛开始了,它下出了一步又一步非同寻常、步步见血的妙招,而这些绝不是人类能够想出的招数——譬如说,开局弃后。一台机器再定义了人类的游戏。机器学习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兴旺期。利用算法,基于我们之前的购买选择,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给我们提供书籍和电影的网上导购建议了。它能够规划商业航班线路,还将在自动驾驶设计中大放异彩。”

作为一位从事书写工作长达半个世纪的小说家,麦克尤恩自然没有置身于这场数字革命之外。实际上,他最新完成的小说正聚焦于这一主题。在这部将于2019年4月18日在英国出版的作品《Machines Like Me》中,麦克尤恩将背景设定在了1980年代伦敦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英国输掉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本恩正在展开权力斗争,艾伦·图灵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个故事中,他关注的是一段特殊的三角恋情:混吃等死的查理、查理的学生米兰达以及查理购买的第一批人类设计生产的机器人亚当。企鹅出版社称,麦克尤恩的这部新作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人类何以为人的标准是外在行为还是内心生活?机器人能够理解人类心灵吗?
虽然外界倾向于将这部最新作品与科幻小说画上等号,但麦克尤恩自己并不认同。首先,这本小说将时间设定在了1982年,写的是过去而非未来。麦克尤恩在书中巧妙地改变了当时的科学进程和政治局势。在他的设置中,1982年的科技比历史上1982年到达的科技水平稍显高明。当然,这种假想另外版本历史的写法在科幻领域也并不陌生。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在《高堡奇人》中也试图将历史反转,假想了同盟国在二战中战败、美国被德国和日本瓜分的情形。但在麦克尤恩看来,故事的真正内核其实是大家都熟悉并且具有悠久历史的三角恋情节,并非什么新颖的科幻题材。实际上,他希望通过这本小说探讨的,是机器人是否有会自我意识以及人工智能究竟是否需要道德感。这些问题对于麦克尤恩来说并非关涉未来,而是指向现在。毕竟在一个自动驾驶即将大规模投入使用、女性机器人索菲娅被赋予沙特公民身份的时代,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界限、机器的意识和情感、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都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棘手难题。“现在一些轻浮的科幻小说过多沉溺于对技术的畅想、对未来的幻想上,而忽略了现在。我认为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写的就是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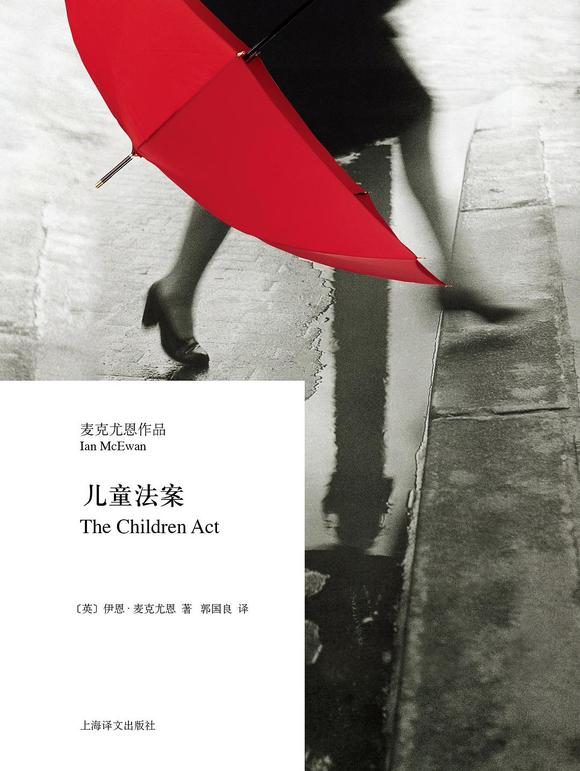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大众传媒极度兴盛的时代,小说家该何去何从?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担心纸质书会被电子书取代一样,如今很多人也在担心,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对此,这棵小说界常青树麦克尤恩并不那么担心。在他看来,小说家就是站在信息以及不实信息风暴中的人。而正是这一暴风之眼的位置,为小说家带来了机遇。“在古时或者过去,小说的主要作用是探究人心,揭示人与人或者人与他所处社会的关系,这部分到今日还是小说主要的功能。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关于小说时代要结束了、小说要灭亡了的预言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但我个人认为,小说还是会继续延续存活下去。原因在于小说家会在这种巨大的信息或不实信息的风暴当中找到一个静止的中心,这些严肃小说家将在这个中心位置继续探究人心,继续研究所有真相以及谎言。”
可他也并不否认,或许终有一天,小说家这个职业,会像工人、白领、医生、会计等其他职业一样,最终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有朝一日,人工智能具备了主观意识和自我意识,甚至能够获得人类以躯体肉身在世间行走时获得的种种体验,那么小说家终将被取代。“也许在一百年以后,未来伟大的小说将由电脑写成,小说家不得不再另谋职业,我是活不到那个时代了,对此我还是很开心的。”麦克尤恩笑着说道。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