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戴小华的《忽如归》不止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反映大时代变迁和两岸复杂关系的家族史。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戴小华觉得,她的《忽如归: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被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评价是继“聂华苓《三生三世》和齐邦媛《巨流河》之后又一部现代民族痛史”,实在是过誉了。
戴小华1953年生于台中大渡乡,父亲戴克英为国民党总政作战部上校。“忽如归”这个书名取自曹植《白马篇》中最后一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忽如归》不止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反映大时代变迁和两岸复杂关系的家族史。通过记录母亲和大弟戴华光作为经历抗战流离到台湾的两代外省人的漂泊与奔走,戴小华也试图刻画上世纪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大弟因在台湾戒严期间呼吁两岸和平统一,以“通谍”罪名被判为政治犯,后台湾解禁,父母魂归故里合葬在沧州,大弟也被释放回到大陆母亲老家沧州,经营起了一家西饼店。“第一代人为理想而战争,分裂以致家破人亡,”陈思和总结说,“第二代人又为了理想而奔走,呼吁和平来弥合创伤。”
“《忽如归》的基调是痛而不恨。”戴小华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专访时说,“这部作品不是批评和控诉。历史需要不断补充,历史探讨需要不断诉说。我希望除了官方的历史纪录之外,还有民间历史的补充,让后世人看到更全面的内容并引以为戒。”
戴小华1975年嫁到了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凭借以大马股市风暴为原型的剧本《沙城》成名,在马来西亚、台湾和大陆出版了多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祖籍大陆河北沧州、出生和成长在台湾、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三重经历,在书写家族史的过程中赋予了她在地与抽离的双重视角。
在今年香港书展期间,从这本书出发,戴小华与我们聊了聊她的家族故事、她对于上世纪台湾动荡的看法、在非虚构与虚构领域的创作经验,以及作为曾经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和作协会长,她对于马华文学的过去与未来、题材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的观察与态度。

界面文化:类似的家族史作品,我们熟知的有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和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外作家在写反映国族的家族史。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的位置和特殊之处?
戴小华:聂华苓和齐邦媛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和老师。她们有过去(战争)的经历,我们没有。《忽如归》写的是家族史,其实是两代中国人悲欢离合的历史,也隐藏了大时代的离散和集体创伤记忆。《忽如归》的故事有两条线:一个是我母亲,在台湾过世、灵枢从台湾运回河北沧州、安葬故土,回顾了她的一生;另外一条线就是大弟戴华光,土生土长的台湾外省小孩。他们代表了两代人的人生,经过战乱、灾荒、流亡,最后想要回归故土。
聂先生和齐先生是上一代的人。那一代人有流亡离散和战争的经历,生活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所以他们对过去是缅怀的。包括我母亲回归故土,向往的还是过去的生活。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没有经过战争,我出生的时候两岸已经分离了。我们也有理想,从上一代的记忆里和阅读的材料里,我们知道了战争的恐怖,不想再有战争,所以大弟为和平奔走呼吁,想要弥补分离的创伤。这两代人是不一样的。
“归”是这本书的核心,既是上一代流亡到台湾或其他地方的国人希望回归故土,也象征戴华光这批为和平统一付出代价的热血青年视死如归。
界面文化:对于有些作家来说,动荡的台湾50年代孕育了文学黄金一代。你怎么看待你出生的那个时代?眷村的台湾外省小孩对大陆可能没有那么向往,但我们在《忽如归》里看到了你作为外省第二代的不同讲述。你认为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戴小华:我想这和我们家的经历有关。1949年之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母亲也随父亲一起过来了。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身边,又因为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本地居民对外省人没有好感,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被欺负是自然的事,母亲都隐忍下来。除了来讨饭的,那时候和其他人没有来往。
在台湾戒严时期,人们不可能自由离开。我们年轻人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要么留学,要么去航空公司工作。大弟戴华光赴美留学,正好碰上“保钓运动”和中美建交之前的动荡——那是台湾政局最动荡的时代。戴华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这类事不会坐视不理。他认为美日分裂了两岸,所以他就逆国民党当局而为,去做和平统一的请愿,准备去壮烈牺牲,做好赴死准备。
我们对大陆的牵挂,主要是尽孝。这种“孝”,是因为父母对他们家乡的感情而爱屋及乌,就算父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们为家乡的捐赠都一直在做,是为了完成父母的愿望。

界面文化:你弟弟戴华光的经历是这部纪实家族史里最重要的素材,也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从你的讲述中,我觉得他有些像清末的谭嗣同,怀有至深的家国理念。你觉得这种理念来自何处?当时在台湾社会怀有相似理念的这一批人,是不是主要是外省小孩?
戴小华:这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弟弟。弟弟刚烈耿直视死如归,甚至有点傻冒。很多事情,都需要一点傻气才能完成。台湾作家黄春明说,他(弟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无可救药就是傻帽。在理想主义中,有些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有些是达不到的——不管达到达不到,他都要去做。
弟弟从海专毕业后,英文很好,通过台湾当局留学考试,赴美研究国际政治。在美期间阅读了很多“禁书”,也曾到越南实习,发现很多事情和小时候受到的教育不一样。他从美国回台后,一直呼吁抵制日货和美货,和朋友去大学学校门口卖一些“禁书”。
戴华光于1977年11月被捕,1978年1月11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在各界的干预下以“匪谍渗透”的夸大罪名判处戴华光无期徒行。他后来说,要勾结早在美国就勾结了,自己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回来就是准备送死,送死的原因就是发出声音,台湾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也有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的声音。他很单纯,以为中美建交、台湾没有靠山,自然就统一了。
和弟弟一同被捕入狱的还有五个人,除了戴华光是国民党军官的小孩、是外省人,其他五人都是本省人,是劳工阶级的孩子,他们六人都是受国民党教育的台湾小孩。戴华光说,大家差不多年纪,谁都没有办法影响谁,只是都有类似的想法,一拍即合。可能还有一群持有相同理念、但保持沉默的人,因为发出声音会带来危险。
戴华光抱着赴死的决心,没想到会连累一家子,他认为这是“一家哭”胜似“一路哭”,倒霉也就倒霉一家。有时候想想会怪他,出国留学不好好学成归来孝敬父母,闯这么个大祸。可以又一想,他也没有错,也没有罪,又不能去怪他和放弃他。后来台湾解禁,两岸三通,戴华光的诉求达到了。他觉得十年牢坐得好值,无怨无恨,出狱后也不参加任何政党竞选,回到母亲的家乡沧州开西饼店去了。

界面文化:作为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这是你第一次尝试书写家族史。你曾提到,一开始写此书时觉得没信心,是因为和既往的写作不同吗?主要原因在技术层面吗?
戴小华:处理家族史,最大的困难是缅怀往事,第一就是要把过去的创伤重新挖掘。当时的知情者不愿再提,有些人已经过世,有些人散落在各地,要找到他们收集材料,核对再核对,查证再查证。资料收集也很难,不能有一丝差错。资料多,我不在现场,事隔这么久,去访问当时的当事人难度很高,也不知道是否能把这些当事人都找到。
另外,从繁杂资料中挑选自己所需、甄选出更能潜入人心的东西再表达出来,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如何写才让人觉得好看、容易接受?我从自己对事件的疑问出发,用一种带读者解密的剥洋葱式的悬疑手法将故事呈现出来。中间也有一些象征和隐喻,比如蝙蝠象征牺牲的精神、铁狮子象征坚毅和对不合理事情的反抗等。
界面文化:写本书时,你有参考或者阅读哪些历史纪实的作品吗?哪本书对写作《忽如归》产生的影响比较大?
戴小华:家族史这一类,我去看了《巨流河》和《三生三世》,看别人是如何把握大时代背景题材的家族史的。别人也有苦难,但我们是特殊的政治犯的苦难。虽然我叙述的是血泪交织的往事,在下笔的时候,还是用爱来反思和超越这个痛。书写坎坷和苦难,但不沉溺坎坷和苦难中。
界面文化:你自1998年始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及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会长,2001年主持出版了500万字的《当代马华文存》十册,2004年又主持出版了500万字的《马华文存大系》十册。马华文学自身也非常复杂,有一种评价是说,马华文学既带着浓厚的台湾印记,也深受大陆文学影响,同时也模仿国外小说,原创的马华文学空间比较小。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戴小华:马来西亚自1957年从英国治下独立,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都参与了建国。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每个民族都有享受母语受教育的权利。在马来西亚,有1300多间以华文为源流的小学,小学有政府津贴,不过母语教育只限小学,到了中学教育政府就不管了。
早期在大马的华人大多是劳工阶级,重视教育,认为华人只受小学教育是不够的,很坚持和维护中华教育,所以民间成立了60间独立华文中学。大马华人都参与了赞助学校,每年都在用各种活动方式筹款。这些中学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以校养校。马来西亚早期的大学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一些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不以成绩来录取,以种族比率来录取。你也可以说不公平,也可以说公平。如果不用种族比例,全部靠成绩的话,那进好学校的90%的都是华人,因为华人读书厉害。这样会造成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心理不平衡,容易产生冲突。
1969年,大马经历了“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来大马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扶植占人口比例60%以上的马来人,实行配额制。配额制造成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进不了公立学校读书。早期私立大学的师资水平不如公立大学,费用又高,中国大陆和大马也没有建交,所以很多华人学生选择去台湾留学。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是在台湾接受的高等中文教育,台湾《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等设立的一些文学奖项也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得奖。
后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又和大马建交,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对外招生,一些好的大学也有针对海外的招生名额,这样马来西亚学生纷纷进入大陆大学,也就受到了当地教育的影响。所以留学生的中文状况是,在马来西亚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后,又到台湾和大陆接受高等华文教育得到提升。像黄锦树这一批作家,就是从马来西亚去台湾的留学生。那时候大马不承认台湾和大陆的文凭,认为会影响本国就业,所以在台湾和大陆留学的人很多就留在当地教书,或继续从事和文学相关的工作。
大马的华文教育和文学界的人确实受到了大陆和台湾的影响。早期,大马的华文报纸都是以前中国南下的报人创办的,现在大马报界也有很多是去台湾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在供职。

界面文化:你认为马华文学在华语文学谱系中处在一个边缘地位吗?
戴小华:(笑)马来西亚的国语是马来语。在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要学三种语言:马来文、英文和中文。华人有时候用方言,客家话、潮州话、广东话很多,所以中文环境不是那么纯粹,是掺杂式的华文语境,话语里会很自然地掺杂马来语、广东话和福建话,语序有时候是广东话直译过来。因此,早期的马来西亚华文创作语言不是一种很纯粹的中文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带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不能用好与坏来定义。我是中马建交之后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作家。当我向大陆引介马华文学的时候,也会觉得语言表达怪怪的。不过这是马华的特色。
马华文学在大的华文创作圈来说,确实比较小。我想,马华文学处于华语创作低端,是因为华人文化和文学没有被大马列入国家文化和国家文学。在这方面若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文学创作很难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在大马也不太可能有专注创作的华文环境。一些很出色的作家回国可能就没有工作机会,因为要自掏腰包或者跟一些会馆申请基金出书,或者没有版税和稿费。
像早期的方北方,他是马来西亚第一届作协会长。在他的时代创作很不容易,那时候连出版社都没有,他让别人把《树大根深》的稿子打印出来,一页一页用手粘了两百本。所以,这不能说是低端,但从创作群体的环境来看,这样的环境很难孕育文学盛世。
界面文化:两岸三地或者在更广的亚洲范围内,是不是有一个华语文学圈存在?你认为,使用中文创作是这个文学圈的连接和标志吗?台湾学者王德威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马华文学也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作家王蒙为你的《忽如归》作序,王安忆出席了《忽如归》在上海的新书座谈会。你和这些华语作家的交游密切吗?
戴小华:我没有什么特定的圈子,可能是因为我有三地的经历,又独得机缘。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看到大马的金融风暴,正好家里又是做股票的,就写了剧本《沙城》。《沙城》在报纸上连载,后来变成书,进入中国大陆,大陆又邀请我来讲学,我就好像变成了这个圈子里的人,而且接触得越多,感动就越多,就越觉得要参与(文学)和为之付出。
我跟王德威的互动比较少。最早认识他是因为马来西亚华室研究中心和报馆举办文学研讨会,王德威是海外最好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所以一定会请他,他也很关注马华文学和东南亚华语文学圈。
和王蒙是更特殊的关系。早年,河北出版社出版《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那时候我正好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社邀请我组稿。丛书在北京发售的时候邀请了王蒙,正好大家都是沧州人,可以用沧州话聊天,就觉得很亲切。后来我们又请他来大马文学研讨会做主题演讲。1997年,《沧州日报》和《沧州晚报》策划了本地作家的故乡行,邀请了我、蒋子龙和柳溪,我和王蒙就有了更久的接触机会。《忽如归》也是王蒙为了激励我早点完成,主动说要为我写序,让我很感激。
和王安忆是她来马来西亚认识的。王安忆和莫言1991年去新加坡参加国际文艺营的评审,也安排了马来西亚的行程。当时中马之间刚刚解严,中国作家公开演讲还没有被马方获批过。我联系了马来西亚内政部的政务次长,安排了王安忆和莫言在吉隆坡、槟城和怡保等地六场巡回演讲,轰动一时,算是大陆作家来大马的破冰之旅。
后来中马作家之间建立互访计划,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前辈叶子铭夫妇等一些朋友,在相处过程中也很有共同语言。这种联系不是刻意的,都是机缘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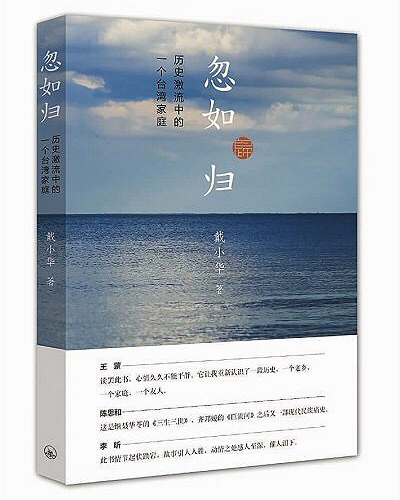
界面文化:此前的大马华文作家更多关注国族和身份认同,现在的年轻作者随着知识结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关注的主题是不是也出现了变化?
戴小华:第一代马华作家确实关注国族认同。那时候华人大多是从大陆过来的,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马华文学也分为好几个时代,有爱国文学阶段,在日本统治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没出什么作品。八十年代时局动荡,社会对华人质疑增多,激发了华族的忧患意识,这个时期的作品除了民族自觉之外,更多的是对民族及个人前途的思考。
后来,主题就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困惑了,华人就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华裔,就是以这个创作身份去写的。现在,大马的华文教育更完整,和国际交流更多,得到的养分也很多。马来西亚是除了大陆和港澳台之外,华语教育最完整的国家了。
马华文学其实有很好的创作素材,因为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有不同民族的冲撞和交融,华人在上世纪社会经济的动荡和政策的偏差中的挣扎与困境,我们需要花功夫和靠自己的能力将它展现出来。很多作家在抽离了环境回望的时候,故事和记忆就渐渐浮现出来。也正因为有距离,视野更开阔,才看得更清楚,用第三视角才表述得更冷静、理性和宽广。如果本土题材不擅长,也没必要非要“应本土而本土”。文学其实不是用主题和地域来划分的,写自己最擅长和把握的、最能给自己带来冲撞力的就行。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