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

1953年,芝加哥,退伍军人休·海夫纳在自家的厨房餐桌上,编辑出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是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内页既有梦露的彩色裸照,还有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日光浴的黑白照片,这本为中产阶级男性服务的杂志后来迅速成为了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1957年,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开始使用自制的“性交机器”,研究关于性满足的秘密。1968年,一对厌倦了一夫一妻的平淡中产生活的夫妻在加州创立了主张自由性爱的砂岩俱乐部,召集与他们类似的人们前来享受不受婚姻制度约束的、更加平等的自由性爱。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出版于1980年,详细追溯了上述种种在美国发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的变化,为人们理解美国20世纪后半叶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一种视角。
时隔38年,当这本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时,美国的性文化已今非昔比,刚刚完结不久的美剧《随性所欲》(Casual)可以被视作这种变化的一个注脚。这部美剧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一对亲生姐弟以及姐姐的女儿,其中弟弟Alex是一个单身汉,他使用自己创办的热门在线交友网站结交漂亮女性,并与她们发生一夜情,却无法发展出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而刚刚经历了离婚的姐姐也试图通过弟弟的网站寻找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试图以此来解决婚姻危机。在如今的美国,随意性关系以及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成为各类文化消费产品的常见主题。
从性解放运动的诞生到约炮文化的盛行,性是如何与生育、婚姻以及较为稳定的亲密关系一步步松绑,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由、无附加条件的性关系神话的?在这条性自由的神话之路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当我们终于能够公开、大胆地谈论性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作为一种人际和身体互动关系的性,还是作为一种象征解放和自由的符号的性?在性的符号化背后,被忽略的又是什么?去年《纽约客》杂志上一篇引发热议的虚构作品《Cat Person》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解答。通过生动具体地描述一段糟糕的性爱经历,这篇小说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勇于言说一次糟糕的性爱以及它带来的感受,是戳破如今大众媒体和主流文化营造出的关于性的神话和泡沫的第一步。

1971年的某天,39岁的盖伊·特立斯和妻子从纽约的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了开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某栋楼的三层窗户闪烁着红色霓虹灯招牌,几个刺眼的大字“现场裸体模特”映入眼帘。虽然当时性解放的风潮已经席卷美国——伴随着1960年代避孕药的开发上市,性与婚姻和生育的逐渐松绑,引发了美国社会内部关于性伦理和堕胎是否合法的种种争议,这些争议的逐步扩大最终引发了美国的性革命——但如此明目张胆的生意仍然让特立斯惊讶不已,并决定一探究竟。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前往那间闪烁着诱人灯光的房间,一位长发、穿蓝色牛仔裤、戴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接待了特立斯。规则如下:半小时18美元,特立斯需要从在桌上摊开的六位女按摩师的照片中任选一位。
这是特立斯在按摩店的初体验,也是他书写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开端。9年之后,他那本聚焦美国性解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以及在中产阶级人群中发生的性革命的作品《邻人之妻》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在书中,特立斯追溯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在性行为和性观念方面的种种变化。在这九年中,特立斯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并且成功地在两家按摩院担任义务经理。1973年,他有机会去到欧洲几个主要城市展开考察,考察中他发现,出入按摩院的大多为男性,“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他在《邻人之妻》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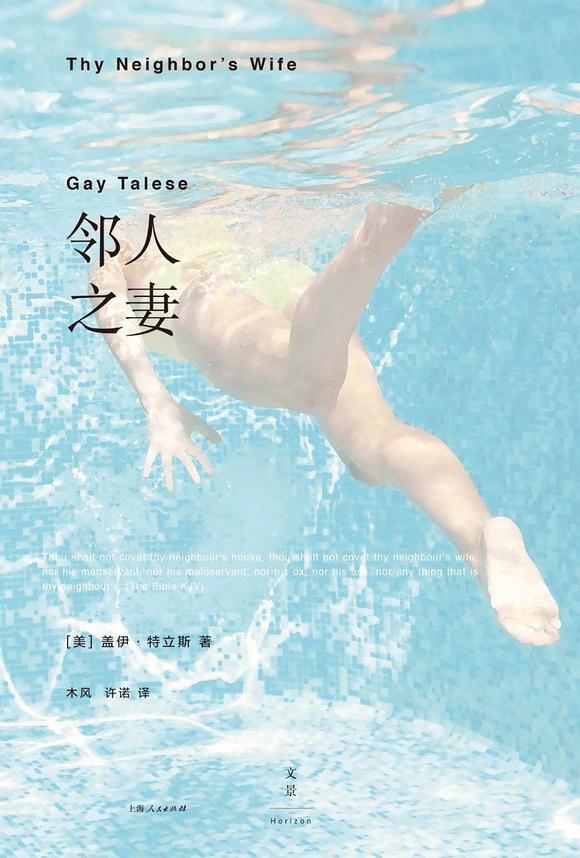
从欧洲回美国后,特立斯游历了美国内陆,采访了许许多多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与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等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试图在与这些人谈话的过程中梳理出一条美国性解放运动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开拓出的道路以及分支。整个游历过程让特立斯开始思考,虽然性解放运动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等等,但许多美国夫妇最爱的书目仍然是《圣经》,他们忠于婚姻,他们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仍是处女。与此同时,尽管全国范围内的离婚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但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他也注意到,即便70年代有许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美国社会最终会回到更加保守的50年代,但巨大的变化确实在发生:聚焦中产阶级娱乐消费的、以性感女性裸照闻名的《花花公子》杂志,在1972年创下了超过七百万册的销售记录;60、70年代,露骨的色情电影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大屏幕上。特立斯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近距离观看了一部色情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这部充斥着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以及对于性来者不拒的女性的电影,稍后出现在了美国大城小镇里限制级影院的大屏幕上,满足着男性顾客的愿望和幻想。
在接下来的加州之行中,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1968年由约翰·威廉森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克拉默创办的、位于托潘加峡谷私人庄园里的开放性爱实验基地。在这个不存在双重标准、不存在用钱交换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也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自由性爱社区,特立斯度过了两个月中的大部分时光。在砂岩社区中,约翰·威廉森带领着由他和妻子招募来的、厌倦了一夫一妻平淡生活的中产夫妇们,试图在此建立一个性爱自由的乌托邦社区。在这里,性自由是连接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手段,团体婚姻而非一对一的专偶制婚姻,满足了他们对于更加纯粹的、与霸权解绑的平等爱情的想象。
虽然作为一位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特立斯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他深入美国性解放运动的路径和方法——也正因如此,他涉及的基本是异性恋的、中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解放,而对于性解放运动中女性、性少数群体以及中产阶层以外的群体涉及甚少——但《邻人之妻》依旧揭示出脱离了婚姻和生育而自由存在的、颇具革命性和解放性的自由性爱,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旧有的观念逐步被打破,关于性的全新逻辑逐步建立起来,在性解放运动中,有关性爱自由的话语逐渐占据主流。

如果说性解放运动是对于之前既有的、陈旧的关于性和亲密关系规则的一种颠覆——即性不只是发生在正统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内部,也不仅仅是为了生育服务,它更多关乎纯粹的乐趣和快感——那么到了千禧年,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经在美国青年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约炮文化是一种接受和鼓励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的文化,包括一夜情以及相关的活动,这种性行为不一定包括情感联系或者长期的承诺。从2000年前后开始,“约炮文化”一词在美国被广泛使用,这种更加随意的性关系不仅局限于大学年轻学生的范围内,很多研究都显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尝试随意性关系,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各类约炮软件则让这种性行为更加便捷化了。

随意性关系当然并非一种全新发明,这种行为在性解放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2015年发表于《性行为档案》的一篇名为《美国成年人的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1972-2012》的论文中,三位作者通过分析来自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认为,随意性行为的比例在过去30年里呈上升趋势。在18-29岁的声称非伴侣性行为中,35%的“被遗忘的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于1970年代的美国人)在1980年代末期发生过随意性行为(其中44%是男性,19%是女性);到了2010年,“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出生于1980-2000年之间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是45%(男性占55%,女性占31%)。
美国年轻人看似全然被约炮文化笼罩或“腐蚀”,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在《男孩变成男人的那个冒险世界》(the Perilous World in which Boys become Men)一书中指出,在一项针对全美男性大学生展开的有关性生活的调查中,他询问了男生们认为在任一周末他们的同班同学过性生活的比例,他们给出的平均答案是80%。但实际上,权威数据(the Online College Social Life Survey)显示,在超过24000位美国大学学生中,80%有过性生活,但在任一周末有性生活的学生比例仅为5-10%。另外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博尔格(Kathleen Bogle)在调查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有趣的一点是,凯瑟琳发现,不管她采访的学生自身的性生活有多频繁,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然会假设其他年轻人有着比自己更加频繁的性生活。
是什么导致了感觉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偏差?大众文化“功不可没”。年轻人之间的约炮和一夜情行为充斥于大众媒体,在美剧、电影以及色情片等其他文化消费品中,裸体、随意的性爱已经成为了刺激人们感官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问题或许在于,这些文化产品倾向于将性当成一种流于表面的符号,性在其中就仿佛烹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对于一道菜品的色香味尤为重要,但没有人会去深究调味剂本身的成分与味道。更重要的是,鲜有文化产品敢于戳破约炮文化营造出的、带有幻想性质的美好泡沫,指出性爱中可能存在的糟糕体验,以及这种糟糕的性所带来的后果和伤害,尽管实际上,除了其符号化的一面,糟糕的性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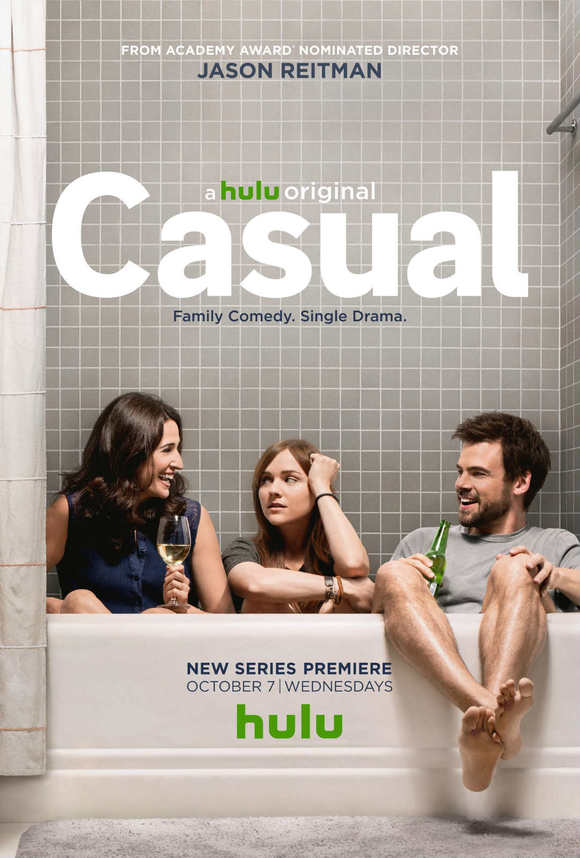
这其中有一个隐含假设,即在性解放运动过后,性(即便是糟糕的性)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性的匮乏和缺失往往被视为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生活。正如蕾切尔·希尔斯(Rachel Hills)在刊于《Time》的文章《每一代人对于性有何种误解?》中谈到的,性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糟糕的,但它一向意义深远,对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今的性文化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愧疚感——因在性方面不够活跃而感到愧疚。在这种氛围下,自由性爱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神话。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2017年12月《纽约客》一篇名为《Cat Person》的小说便显得尤为特别和重要。小说讲的是一位叫做玛戈特的大二女孩和一位叫做罗伯特的男性的约会经历,以及他们二人一次糟糕的性爱体验。小说以玛戈特的视角切入,从他们在玛戈特打工的电影院初次相见讲到后来持续数月的短信交流,到在酒吧的约见,再到玛戈特去罗伯特家两人的性爱体验。在描述两人的肢体接触时,故事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朝着浪漫和美好发展,作者Kristen Roupenian反其道而行之,勾勒出了一系列在玛戈特看来体验十分糟糕的肢体接触,比如罗伯特糟糕的吻技和更加糟糕的性爱技巧。
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个糟糕的性爱过程因为作者极其细腻的文字呈现和玛戈特数次感官和心理上的嫌恶反感,而显得异常漫长难耐。在整个过程中,玛戈特不止一次打退堂鼓。罗伯特把裤子褪到脚踝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鞋,于是他尴尬地俯下身去解鞋带,他那被毛发覆盖的腹部臃肿而柔软。玛戈特看到上述场景时,心生反感,但她随即想到立刻叫停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互发短信数月,她在酒吧时也暗示罗伯特他们可以发展到性关系的地步,并且如今她已经坐在罗伯特家中等待他脱去衣服——在此刻叫停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温柔,就好像“在餐厅点单之后,送上来的菜品不合胃口,她突然改变主意并将其退回”。当罗伯特将自己的体重压在玛戈特身上并亲吻她时,她“知道她享受这次遭遇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消失了,但她仍然会将其进行到底”。在她被翻过来转过去的过程中,玛戈特感觉自己像个玩偶,一个用橡胶制成的玩偶,柔软而有弹性。

作者Kristen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她让人人都可能经历过、却鲜有人公开谈论的性经历中那些糟糕的感官,通过语言的微妙力量走向公众视野,变得可见,甚至可以被公开讨论。而同时,她也直接指向了亲密关系中的同意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Cat Person》提醒我们:一方面,性是最私密的话题,它关乎两个或者多个性伙伴之间亲密无间的身体互动,它代表着一种最为赤裸的坦诚,虽然过程中也不乏伪装与欺骗;与此同时,性也是最具公共性的话题,它是被约炮文化统领的美国校园中学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影视文化消费品中的常客——虽然在影视作品中,它时常被简化为一种符号性的指称。大众文化对于微观互动中性行为可能包含的不适、感官的错位、对于快感的误解以及对于同意的误区,都极少给予严肃的讨论,性因此成为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快消品和刺激物,被不断商品化和符号化,激发着人们的无限欲望与遐想。
于是,在当下,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窘境之中:人人都在谈论性,但由于每个人对于性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差别,彼此交流和分享性经验变得十分困难,对于性的谈论由此沦为了对一种空洞符号的探讨,而这种表面化的谈论方式恰恰消解了性的严肃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为何性是政治的?这是因为,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人们背负着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属性,也背负着自己的种族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以上种种背景交叉角力而生成的权力关系。
在性解放运动过去60年之后,当约炮、一夜情、无需承诺和责任的性爱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时,当拥有性生活成为一种无需辩驳的默认设置和政治正确,当性本身被剥离了具体内容和互动关系而成为一种被神话的符号,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敢于戳破这层神话泡沫的勇气,是在让自己感到不适的性关系中拥有及时喊停的勇气,是在性爱话语漫天飞舞的当下拥有能够公开而具体地谈论性的勇气。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