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的胸脯与妇女的“奶子”有何区别?贯穿其中的是怎样一种由崇拜到贬损的审美态度变化?在那些想象由女性的乳房抵达身体的作品中,女人的心态又是如何变化的,是自我献祭,还是对抗挣扎?

在小说《玉米》中,毕飞宇构建了一个泛性化的世界,男女老少都呼吸在性的空气之中。连农民耕耘的大地都是“丰乳肥臀”,“洋溢着排卵期的孕育热情”,在这个小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在通奸。在玉米的母亲频繁怀孕的时候,玉米的父亲、村支书王连方就在外面与别人家的老婆通奸。村里的每个老婆都与王连方睡觉,她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顶着她们男人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家的”,比如裕贵家的、有庆家的、富广家的,好似显示着村支书对这里男男女女的彻底征服。
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女玉米刚一登场,她的身材就被父亲注意到了,“她的胸脯鼓鼓的,腰身线也明显了,”这个写法还算含蓄;而当成熟女人出现时,毕飞宇开始频繁地使用“奶子”这个略显粗俗的称呼来指涉她们的胸部。少女的胸脯与妇女的“奶子”有何区别?其中贯穿着的是怎样的由崇拜到贬损的审美态度变化?说到女人的胸部,英国作家D.H.劳伦斯也写两性关系,也会想象由女性的乳房抵达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女人的心态又是如何变化的——是自我献祭,还是对抗挣扎?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哺乳的形象都被赋予了圣洁的光环,然而这种圣洁是真实的吗?哺乳迷思缘何而来?通过对几部中外正规出版的小说的分析,我们希望可以为以上几个问题作答。
在毕飞宇创造的村庄里,性事频繁发生,“奶子”也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意象。相比于胸部和乳房这样的称呼,毕飞宇更偏爱用“奶子”一词 ,这也不算他独创,汪曾祺在《受戒》里就写过,“姐们长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小说《玉米》中有一段荒谬的描写,发生于王连方在跟裕贵家的上床之时。裕贵家的捂住自己的胸脯,她说,“支书,你都睡过了,你就省省,给我们家裕贵留一点吧。”王连方先是笑了,紧跟着是这么一句,“你那两只奶子有什么捂头?过门前的奶子是金奶子,过了门的奶子是银奶子,喂过奶的奶子是狗奶子。她还把她的两只狗奶子当做金疙瘩,紧紧地捂在胳膊弯里。很不好。”
在叙事学上,这段议论属于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没有明显的作者与人物叙述的界限,无法分清这话是王连方的人物叙述还是作者的议论。然而它传达的道理很清楚:女人“奶子”的价值与她的性经历和哺乳历史成反比。 或者可以说,在女人等同于性资源的语境之下,她们的“奶子”会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中迅速贬值。

比如少女玉米的胸脯,在毕飞宇笔下,就属于“金”的那一类。玉米换上了新衣服,他写道,“最精心动魄的是在胸脯的那一块,凸是凸,凹是凹,比不穿衣服还显得起伏。”接着又对这胸脯加上了一句通感的形容,“挺在那儿,像是给全村的社员喂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全村要像一起种田般团结在一块儿吃奶,但作者明确的一点是:少女的丰满胸脯,才是令人向往雨露均沾的。
如果跟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段描写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和张爱玲对于少女胸部审美有着明显的差异。张爱玲如此描写烟鹂,“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她没有将“挺”、“凹凸”还有使男人“惊心动魄”作为审美标准,也没有将女性的胸部和“喂奶”急不可耐地建立起联系。与这样有血肉、不完美的身躯相比,毕飞宇笔下的玉米仿佛一个千篇一律、缺乏实感的人体模型。
即使是缺乏实感的,这样以抽象的丰满为美的态度也可以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而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不仅男作家会以“丰满挺立”的套路想象乳房,女作家自己也会信服并屈从于这一标准。严歌苓的小说《芳华》里有一个晾乳罩的段落,大院的晾衣绳上出现了一个乳罩,乳罩露出了两个凹型搓澡海绵,这幅画面让女兵们一同缩起了身体,红了脸孔。严歌苓写道,大家虽然有丰胸的向往,但谁都耻于这样做。接着,她为女性的“丰胸”向往做了一段文化史层面的解释,“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虽然认为乳罩符合女性的“集体潜意识”,严歌苓仍然没有忘记,假的毕竟是假的,何况还是粗陋的廉价的,跟天生的丰满胸部无法相比。她几乎是饱含赞美似地写道:“长着丰美的胸”的女兵,是无法体会胸部作弊的苦涩的。

回到小说《玉米》的床上这段争执中,王连方先是带着嘲笑的姿态看待这个护着“狗奶子”的女人,接着又“虎下了脸”。他由“护奶子”的态度检验出对方不够配合——裕贵家的显然太在意自己和自己戴绿帽子的丈夫了。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得远不如另一家的女人更合他的胃口。有庆家的伏贴多了,“上床之后找不到一块骨头,软踏踏地就会放电。”这浪荡的姿态与《红楼梦》里跟贾琏私通的“多浑虫”多姑娘极其相像,那一位“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
在著名文学作品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与男仆的性爱过程也是从胸部写起的,“他向上撩起她的衣裙,直至胸际。他温柔地吻着她的乳房,把乳头含在嘴里,轻轻地吮吸着。”对于男人的抚摸,女人的态度却是带着颤抖的抗拒,“她身体里的什么东西颤抖起来,而她的精神上,却又某种东西强硬起来的抗拒:抗拒这可怕的肉体亲密,抗拒他此时此刻的匆忙占有。”她安静地躺着,以一种异常冷静的角度,反观男人的举动,觉得“他屁股的拱动十分可笑……是的,这就是爱,这可笑的拱动,这可怜的、微不足道的、湿乎乎的萎缩。这就是神圣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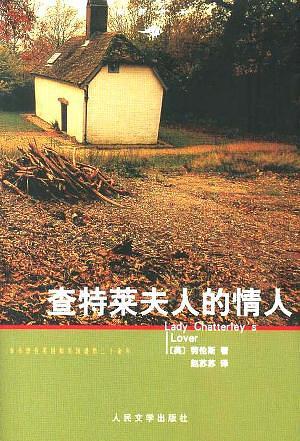
与毕飞宇所写的男性征服、女性服从的模式全然不同,劳伦斯擅长描写这样充满复杂矛盾、争斗、甚至是痛苦的性爱。比如说在上面这段引文中,他将女性的性爱描摹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颤抖抗拒——冷眼旁观——渐渐疯狂——投身于洪波之中——退潮时痛快淋漓,而并非全然被动、节节退让。在劳伦斯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狐》中,女人和男人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却还是处于一种斗争不休的状态,男人想让女人顺从,要她毫无防卫地委身于他,消沉下去,“只做他的女人”,她却偏偏不肯,仿佛对他的顺从是一场长眠,“在硬撑着不睡的固执努力与紧张中,她似乎把眼睛越睁越大。她要撑着不睡。”
以劳伦斯的康妮对比毕飞宇的玉米,玉米的性明显是充满崇拜的、缺少对抗的。与未婚夫在一起时,他摸到了她的乳房,这使得玉米吓得不轻,但是她抵抗不了,因为她崇拜他,她不像康妮一样可以反观出求爱中男性的猥琐,玉米想的是,“他的手能把飞机开到天上去,还有什么能挡得住?”所以,玉米和未婚夫之间的关系,被描写为男方的得寸进尺和女方的节节退让。玉米不是查特莱夫人,她挣扎的不是爱不爱对方,而是努力让对方不要突破最后一道“关口”——她的身体不是由器官,而是由贞洁“关口”组成的,她可不想成为道德家口中的“狗奶子”、“臭豆腐”。因此,当未婚夫承诺不会不要她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充满激情的举动——让自己的乳房裸露在他的面前,并允许他含住了自己的乳头。毕飞宇将玉米此举简介地写成“给他”,充满了自我献祭的意味。
自我献祭,任君宰割,顺从投降,这种想象女性献祭的场面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并不少见,而这些场面又无一不与上文所说的抽象空洞的丰满审美相关。比如曹文轩《天瓢》中有这么一段特写,“两道白如新雪的乳坡,带着慢慢滚动着的钻石一般晶莹的水珠,在极短的距离内,献祭一般地呈现在杜元潮的眼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的一段描写已僭越人伦,哑巴弟弟讨不到老婆,姐姐觉得难过,她将内衣解开,把自己献给弟弟,“好歹也让你尝一尝女人的滋味……玉白的乳房朝弟弟惊愕的目光迎上去。‘你就在我身上来吧,我不怪你。’”接着,姐姐又说,“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自我献祭到这种程度,已经放弃了做人,姐姐说自己“不是人”,戳中了“自我献祭”的核心;而放弃做人也必将引发更强烈的人格羞辱,玉米就将对自己父亲过于恭顺的女人不客气地称为“骚货加贱货”,“好像臭豆腐,一戳一个洞”。
遗憾的是,玉米这番对于女性“自我献祭”的羞辱,最终落到了她自己的身上。被未婚夫莫名其妙抛弃后,玉米在一次和大龄干部的相亲中,从高傲的玉米姑娘变成了主动“扒光”自己的婆娘。“扒光”这个词,作者仿佛过瘾似地,反复使用了多次,分别用来形容玉米的自尊——“玉米一个人走出电影院,自尊心又被扒光了一回”,玉米的衣服——“总不能自己扒光了,再自己爬上床”,还有玉米的皮肉——“玉米觉得扒开的不是衣裳,而是自己的皮”。 就像村里的女人甘愿或半甘愿地与她的父亲村支书上床一样,玉米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情愿地上了城里大龄干部的床。在这风平浪静毫无激情的床上,她被扒光了,乳房也不再重要了,再没有被提起过。
毕飞宇对于女人的“奶子”从金到银再到狗的价值递减逻辑,并不总是成立的。在另一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哺乳期的女人》中,他对奶过孩子的“奶子”的审美态度显然宽松了许多。《哺乳期的女人》是一个以女人哺乳——或者用作者的话说,“奶子”——为核心意象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七岁的男孩旺旺,从小母亲没有奶水,因此一直没有尝过奶水的滋味,他被送到爷爷奶奶家。母亲虽不在场,“奶子”处处出现。爷爷奶奶也会有意无意调侃起他妈妈的“奶子”,奶奶将牛奶、奶糊、鸡蛋黄的混合物喂给他吃,并提醒他说,这是“你妈的奶子”,爷爷则愤愤不平,他觉得现在女人的肚子被国家计划了,但奶子总不能跟着瞎计划。奶奶和爷爷,一个是自认为在制作替代性的“奶子”,一个是站在国家政策高度发牢骚,二人分别以自己的角度呼唤着缺席的儿媳的“奶子”。
旺旺家的对门,有一个长着健硕胸脯的女人惠嫂。作者将惠嫂的乳汁比喻为了某种类似中华文化或自然瑰宝的资源——“源远流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将乳汁比喻为瑰宝,这实在没什么新奇,莫言在《丰乳肥臀》里写喂奶,也细致地写那“混合着枣味、糖味、鸡蛋味的乳汁”,将乳汁比喻为“一股伟大瑰丽的液体”。不仅如此,女性在铺子门口喂奶的姿势也被认为“格外动人”,不解开扣子,直接撩起上衣,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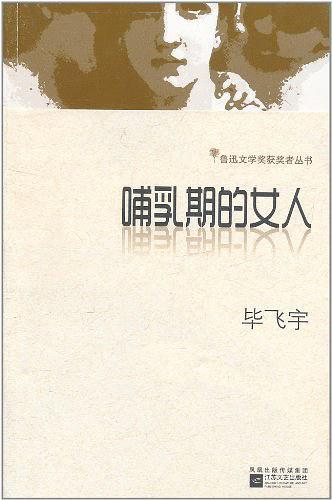
惠嫂哺乳时的“圣洁”会不会遭到亵渎呢?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写“我”的媳妇坐在门槛上喂奶,也是充满爱怜的,“看她坐在门坎上,露着点胸,给小娃娃奶吃,我只能更爱她,而想不起责备她太不规矩。”然而,比毕飞宇小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哺乳并没有让“我”的媳妇更“圣洁”,她最后还是跟人跑了。反观《哺乳期的女人》,从没吃过奶的旺旺被惠嫂喂奶的画面诱惑了,也被这不绝如缕的奶香包围了。有一次趁惠嫂不注意,男孩狠狠咬了她的乳房一口,惠嫂一声尖叫吵醒了半个镇子的居民。而她对乳房被咬这件事的反应却令人浮想联翩,惠嫂是又疼又害羞,“责怪旺旺说:旺旺,你要死了。 ”这不像是成年妇女对孩子的责备,反倒接近于媳妇儿对成年男子的嗔怪,例如《金瓶梅》里潘金莲对陈经济的怒骂,有着调情的意味。
耐人寻味的是,惠嫂被咬的事情给整个镇子都知道了,他们也都想沾点儿旺旺的光。就像全社员都要玉米“喂奶”一样,村民调戏惠嫂说,“惠嫂,大家都‘旺’一下。”除了惠嫂的婆婆,大家都觉得这个笑话有趣。旺旺受到了爷爷的教训,生了一场病,再也不坐在门槛上看惠嫂喂奶了。惠嫂反而觉得愧疚——为他不敢出来、只躲在门里面偷看喂奶而愧疚。一个喂奶,一个偷看,毕飞宇写道,这层互动日复一日,变成了这个妇人和这个孩子之间的“秘密”。有一天,惠嫂忍不住了,抓住了旺旺,把他拖到了杂货铺的后院,撩起了自己的上衣——就像玉米对未婚夫,就像《马桥词典》里的姐姐对弟弟那样——对旺旺说,“吃吧,吃。”见男孩惶恐不安,她说,“是我,你吃我。吃。”后来还说,“傻孩子,弟弟吃不完的。”
男子吃奶的故事,在谷崎润一郎的《梦之浮桥》里也有写到。与“全村社员”对少女玉米胸脯的集体觊觎不同,《梦之浮桥》中的主人公“我”对母亲的回忆是独特的,属于童年的,那是一个“混合着发香和乳香、在带着体温的怀抱中甜美的而又微微发白的世界”。亲生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娶了新的妻子,“我”也改口唤她母亲。有一天夜里,这位继母来到“我”的房间,说起了五岁时还吃妈妈奶的故事,并领“我”与她同睡,那时的“我”已经长了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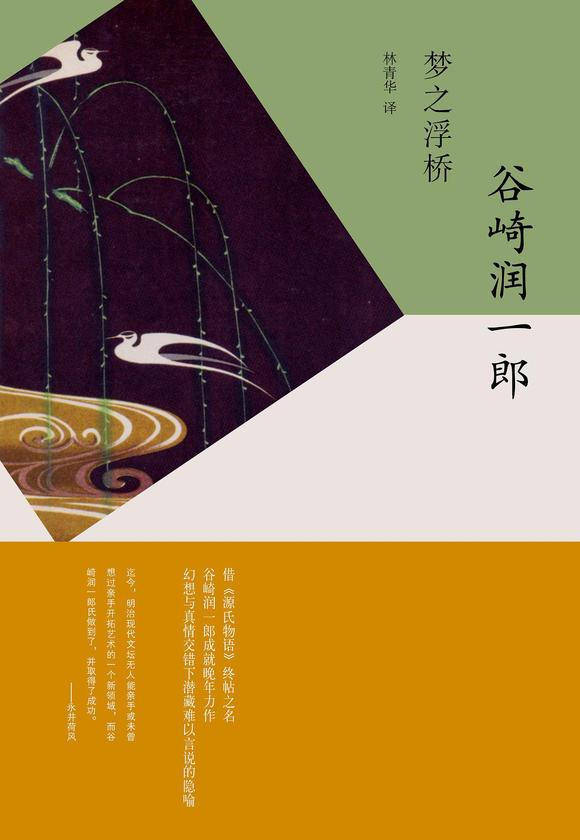
怪异的一幕出现了,“我”在她身边躺下,鼻尖碰触到她和服的开口,找寻到乳头,用舌尖吮吸个没完,但却吸不到奶水。“吸奶”的惬意感使得“我”仿佛怀旧似的,又再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发香和奶水混合的世界”。“我”如此与继母相处,一直到十三四次岁。几年后,继母产下一个弟弟——然而孩子却被父亲送往了很远的地方。在涨奶时,继母又一次叫上了成年的“我”。比继母已经高了不少的“我”,又一次撩起继母的衣襟,吮吸起她的乳房,“团着身将脸埋入母亲的怀中,贪婪地吸着不断涌出来的奶水。”《梦之浮桥》处处暗示的都是“我”与继母之间的乱伦关系,被父亲送走的继母产下的弟弟就是明显的证据。主人公正是借着对那个甜美的、发白的童年世界的怀念,与“继母”的关系才得以发生。
七岁的旺旺渴望缺席的“奶子”,咬了哺乳期的邻居胸脯一口,而被迫断奶的“我”希望在继母身上得到慰藉。他们的共同理由都是对母亲的向往,然而在替代的女人的胸脯之上,他们却滋生出了母子天性之外的暧昧想象。只不过,在毕飞宇笔下,惠嫂几乎是以一种献身的姿态向男孩敞开胸脯,“巨大浑圆的乳房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旺旺的面前”;而在谷崎润一郎这里,继母对“我”的态度是委婉的,只是让“我”不再接受其他的女人而已。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