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落后的性别观和可疑的儿童观,以及厄齐尔发表声明退出德国国家队背后足球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落后的性别观和可疑的儿童观,以及厄齐尔发表声明退出德国国家队背后足球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7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常立称,自己上三年级的儿子在学校被要求阅读指定课外书、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儿子看得很生气,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小孩“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常立安慰儿子,儿子回答道:“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妹妹以后还得看。”常立听了这句话后,“脊梁骨发凉”,想到刚刚两岁的女儿以后还要读《草房子》,并且作为学校的指定课外书,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阅读此书,“这件事,对一个父亲来说,太吓人了”。这并非“新京报书评周刊”第一次讨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该媒体曾集中发文数篇,探讨曹文轩作品落后的性别观和以成人世界为目的的儿童观。
北京时间7月23日,德国中场球星厄齐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在声明中,厄齐尔直指自己在德国遭遇的种族歧视问题。厄齐尔在声明中写到,自己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在德国媒体引发巨大反响,有人因此指责他为叛徒、骗子。与此同时,厄齐尔认为自己受到了德国国家足协主席格林德尔的不公正对待。厄齐尔写到:“在格林德尔和他的支持者眼中,比赛赢了,我就是德国人;而比赛输了,我就是个移民。”厄齐尔的这份声明激起了关于足球与政治、种族问题的种种讨论,也涉及德国国内极端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难民涌入对于德国的影响。在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些问题却不会随之消失 。
在《草房子》中,男孩桑桑从一年级起就跟随自己的的父亲、在油麻地小学做校长的桑乔,开始了自己在油麻地为期六年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桑桑从一位喜欢通过搞破坏得到他人关注、与同伴竞争的孩子,变成一位以利他主义为中心的五好少年。在《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一文的作者常立看来,《草房子》中的性别观是存在问题的。在故事发生的麻油地,那里的家庭总是缺少母亲,那里的姑娘们大多选择离开,那里的女性总是沉默,即便唱歌,也唱的是无字歌,那里的女性总是很苍白很柔弱。
事实上,早在“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7月28日发布的《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一文中,作者童蓓蓓就分析了小说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童蓓蓓发现,故事里的已婚女性基本上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被纳入繁衍序列,她们被称为某某妈、某某奶奶。对于这种叫法,油麻地的每一个人都默默认同,无人抗议,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油麻地不可动摇的潜规则。除此之外,《草房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从懵懂的少女到恋爱中的女孩,再到婚后无子的妻子,每一种形象都被父权和夫权牢牢控制。对于书中无子无女又丧偶的秦大奶奶,当地政府要征用她的地建小学,秦大奶奶的反抗无济于事。在政府号召下,全村老小出动,民兵架起秦大奶奶将她拖走。最终秦大奶奶为了救小学的一个南瓜而溺死。
那么《草房子》中的男性角色又是怎样的呢?童蓓蓓以桑桑的父亲桑乔为例,分析了在桑桑身患绝症之后,桑乔从自己小学校长的身份中醒来,带着儿子四处求医,给儿子买零食、陪儿子聊天,恢复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在父亲带着桑桑求医的过程中,儿子喝下医生开出的药汤后,有一段描写值得玩味:“当他看到一股棕色的尿从桑桑的两腿间细而有力地冲射出来时,他舒出一口在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压抑于心底的浊气,顿时变得轻松了许多。” 童蓓蓓认为,桑乔在此处采取的观看范式,是针对男性的特定动作,紧盯儿子尿液从而纾解了浊气,象征着只有男孩才能被看做后嗣,只有男孩才能让父亲扬眉吐气。由此,校长身份虽然让桑乔有荣誉感,但那代表公权,最终让他感到释然的是他作为父亲的身份,公权让位于父权,这是油麻地的终极价值所在。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曹文轩在建构油麻地这一村庄时,“动用了他对美好的所有想象,但这美好里,并不包括女性。”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发布的另一篇文章《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中,作者塔娘认为,在曹文轩笔下女性形象鲜有突破,女性总是代表纯洁、温柔、善良,服务于男性欲望,而非努力建构自身主体性,而这说到底,是“阳具崇拜的文学体现”。与此同时,曹文轩并非孤例,这种性别意识的流露基本上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一大“通病”。

塔娘认为,在曹文轩的作品中,女性的名字大多是纸月、紫烟、乔纨、艾雯、秋蔓、幼菊等纤弱缥缈的名字,加之曹文轩的“古典式”创作方式,他笔下的人物名字中的意象符号和形象特点基本保持一致而非对立反讽的关系。
相较于对女性的温柔化纤细化处理,曹文轩对于男性的处理则着眼于男性生殖器,并以此体现阳具崇拜情结。在《狗牙雨》中,他写到:“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在《根鸟》中他写到:“裤裆里的那个小家伙,挨了河上吹来的凉风,紧缩得很结实,样子小巧玲珑,就很像那些在芦苇叶上鸣啭的小雀子。” 而一涉及女性身体,曹文轩的描述便是,胸脯的起伏是“风拂的春水”,女孩“没有瘢痕”的身体是 “洁白无瑕的玉”。两相对照,则形成了男性对女性,阳刚对柔弱,保护对被保护,主动对被动等一系列关系。
更进一步,塔娘认为,曹文轩的创作和时代语境不无关系。当代儿童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经历了“重新发现”“性别”这一时期,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带着冲破在那之前统一政治话语的强烈愿望,转向对于青春期发育题材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也有理论研究者提出要建构“少女美学”。在塔娘看来,在不同时期,“女性”一词成为一种修辞式的运用,拥有自身主体性的女性形象仍旧没能够在儿童文学中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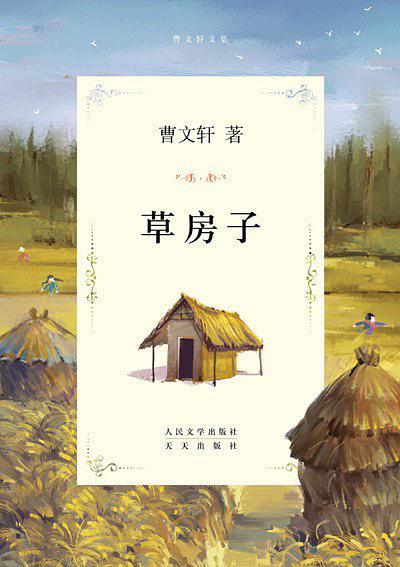
谈到儿童观,常立认为曹文轩的儿童观是可疑的。常立引用曹文轩近作《关于儿童文学的几点看法》中的观点:“他们(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甚至是不可靠的。”与这样的观点一脉相承,在2016年“书评周刊”发表的《曹文轩:“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安徒生的性别观很落后吗?”》一文中,曹文轩强调自己的一部作品《天瓢》是成人作品,孩子们不该看。常立认为,在这种儿童观的影响下,儿童的成长成为对强大现实的被动接纳,而非对无理现实的无理超越。
在《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一文中,曹文轩提到自己坚持儿童文学创作的原因是“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东西,满足我的美学趣味”,“这可能是我选择儿童文学的重要原因,其实还真不是单纯地去为了孩子写东西。我发现当我站在儿童视角,一旦投入到那个语境之中,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全部改变,就像产生了很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在作者童蓓蓓看来,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实则是自我满足的路径,在他的儿童观中,儿童是工具而非目的。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另一篇《曹文轩先生,童年哪有那么多苦难啊?!》文章中,作者张婷婷分析了曹文轩的作品《细米》。她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儿童小说,但故事中儿童和成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却脱离了当下的童年语境。 张婷婷首先分析了故事主人公小男孩细米用刻刀划花村中四根廊柱而被父亲责罚的情节。父亲发怒是由于父亲是学美术的,廊柱承载了父亲莫名的情愫。张婷婷认为小说中对四根廊柱的描写止步于此,而非对更加深厚的情感关联或道德意义的铺垫,沦为成年人的自我设想。在这场闹剧中,成年人对孩子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作者看来,因为成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惩罚一个儿童,放在当下,这种情感关系和逻辑叙事很难被称为适当的、现代的。
而在描写细米对于雕塑的热爱时,曹文轩通过设置梅纹这一教导者的角色,将儿童自己的声音隐蔽起来。梅纹将自己儿时的经验投射到孩子身上,对细米做出判断:“当年,爸爸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将她从重复的、无休止的玩耍中拉拢到他们的世界里去的。细米需要由她来细说——细说天地。”在张婷婷看来,这样一位将自己的经验和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的启蒙者无法真正为孩子打开属于自己的世界。细米在小说中始终是失语的,他的形象也是懵懂无知的,体现了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失衡。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自由的眼”的文章《种族歧视?无法融入?政治天真?厄齐尔推出国家队之始末》中,作者大安按照事件脉络梳理了厄齐尔的足球之路。早在厄齐尔出生前,厄齐尔的祖父带着只有两岁的厄齐尔父亲来到西德的一座小镇定居。1988年厄齐尔出生,拥有德国与土耳其双重国籍。2006年厄齐尔在家乡的德甲俱乐部沙尔克04开始职业生涯,2008年转投德甲俱乐部云达不来梅。2007年厄齐尔放弃土耳其国籍,成为单一国籍的德国人。2010年因在南非世界杯上的优秀表现,厄齐尔被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签下,2013年又以4250万英镑的身价转会至英超俱乐部阿森纳。值得一提的是,厄齐尔的土耳其裔身份一直备受关注,2010年10月8日,在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上,德国对阵土耳其,厄齐尔被在场观战的土耳其球迷竖中指。屡次因种族和民族性问题在公共场合备受诘难的厄齐尔在2012年表示:“我想要作为一名球员被众人评价,足球是无国界的,更与我的家族之根在何处毫无关系。”

在2010年德国以3比0战胜土耳其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更衣室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合影留念,这幅画面在当时也彰显了德国卓越的融入政策和向世界开放的积极姿态。与此同时,同一天晚上厄齐尔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并留下了合照。当时那张合照并未引起什么波澜,而今年二人再次合照却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成为最终厄齐尔退出国家队的导火索。2018年5月下旬,当时正在追求大选连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英国伦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厄齐尔与另一名德国国家队的土耳其裔球员京多安被安排与总统会面并拍摄合照。在欧洲主流舆论中,埃尔多安的形象负面又消极——他曾将成千上万的异见者(包括几名德国记者)关进监狱。这张合照立刻引来德国媒体对厄齐尔的口诛笔伐,德国国家足协主席格林德尔表示,应该将厄齐尔驱逐出国家队。尽管德国主帅勒夫顶住压力将其带到俄罗斯世界杯,但厄齐尔在赛场上发挥欠佳,甚至成为德国队小组赛惨遭淘汰的替罪羊。在世界杯德国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厄齐尔保持沉默;第二场迎战瑞典,厄齐尔坐在替补席;第三场对阵韩国,德国战败,球员离场路过观众席时,厄齐尔听到有球迷攻击他的土耳其裔身份,便与球迷发生了冲突。之后,厄齐尔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

在梳理了厄齐尔在德国的足球之路后,作者大安认为厄齐尔退出国家队事件暴露出欧洲右翼极端主义的崛起以及德国长期存在的融入问题。在世界杯期间,德国右翼极端党派afD(德国的选择)多次公开表示厄齐尔是德国的叛徒,蓄意让德国失利。对于afD来说,厄齐尔与埃尔多安的合照是一个绝佳的攻击借口。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言论确实引起了一部分民众的共鸣和愤怒。融入问题则是德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70年代,由于西德劳动力短缺,大量土耳其劳工奔赴德国工作,在德国生儿育女。德国允许双重国籍,因此拥有德国国籍的土耳其裔人数在德国高达百万。但由于宗教原因,他们也并非完全融入了德国社会。在德国城市中仍有许多土耳其社区,其中的民众虽然在德国生活数十年,但仍然不会德语。作者认为此次厄齐尔事件是数十年移民历史下“又一声唏嘘的扼腕叹息”。同时,在埃尔多安的大选中,德国有权并参与投票的德国土耳其人(双重国籍)或者土耳其人(在德国生活的单一土耳其国籍)有65%选择了有违民主价值的埃尔多安,甚至超过土耳其本国对埃尔多安的投票率(53%)。这群人的选择也值得深思。

在发布于公众号“占豪足球分析”上的《从厄齐尔宣布退出国家队看德国的撕裂》一文中,作者洪爷从难民潮的角度分析了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群危机。由于在德国的土耳其群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和文化圈子,并且拥有稳固的宗教信仰,他们成为德国少数族裔中最热衷于政治表达的群体。在过去数年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坚持包容的思想原则,这体现在2006年在德国国家足球队中显现出来的多元化用人思想,在世界杯、欧洲杯等比赛中,移民后裔球员逐渐成为德国队的中坚力量。但难民的不断涌入、欧盟体系的连连危机,让德国面临分裂。2016年德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德国的民粹主义力量开始抬头,移民群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洪爷进一步指出,厄齐尔事件背后实则是一个撕裂的德国。根据2016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调查,22.5%的德国居民有移民背景,伴随着种族多元化的是贫富不均的加速。德国当前处于失业率历史最低点,但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60%的家庭数量,却从2015年的14.7%上升到了2017年的15.7%。同时,德国政府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40%的德国工人的真实工资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基本没有增长。洪爷认为,这种加剧的贫富悬殊助长了德国人对于外来人口的歧视,他们一边维持自己仅有的财富,一边认为是外来人口抢夺了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资源和机会。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