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当时生活在北平的人来说,1930年代,这座城市并非《邪不压正》里那样。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7月13日,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引发热议。这部根据张北海小说《侠隐》改编的电影,让民国时期的北平再次进入了观众视线。为了呈现北平风貌,姜文特地在云南搭建了一个四万平方米的影视城,并还原了北平当时的平房屋顶,供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屋顶“跑酷”和骑自行车。
姜文操刀改编之后,蓝青峰取代李天然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角和终极大boss,而整个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无厘头对话和黑色幽默桥段也充满了姜氏风格。唯一将姜文和张北海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是他们对于北平的描绘。电影中的北平有着延绵的灰色屋顶,有四合院,有人烟稀少的胡同,这也几乎是张北海笔下的北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读者和观者描绘了一个中产以上、甚至是特权阶层眼中的北平。正如张北海在新版《侠隐》书末收录的对谈文章中提到的,“小说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家世,大部分属于中上阶层。今天,我猜多半只是这些人会去追怀那已逝去的老北京和好日子。这么说好了,如果骆驼祥子没有死,而且拉了一辈子洋车,我怀疑他会认为三十年代北京有过什么好日子。”北京从北伐到抗战的这十年间的光景,被张北海明确定义为“金粉十年”,是有钱人的乐园,是老百姓的清平世界。
那么,除了《邪不压正》和《侠隐》里那个有钱人眼中的北平之外,这里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呢?有钱人的世界和老百姓的世界之间真的彼此隔绝吗?本文首先试图深入小说《侠隐》,带领读者领略书中“金粉十年”的富人生活,以及富人阶层在北平城市空间中形成的空间区隔。其次,我们将转换视角,将视线从散落在胡同中的深深庭院、充斥着异国风味的饭店和灯火通明的百货商店,转向街道、胡同、天桥等平民聚集的场所,看看当时在北平的大多数民众过着何种生活。然而,讨论中上层和底层的北平,并非是试图刻意制造一种阶级上的二元对立和分裂,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借鉴历史学家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的观点,通过对于天桥这一特殊消费场域以及北平当时独特的“回收系统”的探讨,来说明社会阶层消弭的一种可能性。

“四合院儿真是安静,李天然坐在那儿,像是身在山中野庙……大门一关,外边什么杂音飞土都进不来。完全是个人的小天地。”李天然甫一回到北平,便被自己的养父马大夫接到了位于干面胡同十六号的四合院。蓝青峰所在的蓝公馆则更为气派,坐落于东四九条三十号,大门口有两尊石狮,两棵大榆树,院子内分为前院、垂花门、回廊、内院,家中的摆设则是“有中有西,有新有旧。很讲究,可是不过分”。但相比卓十一的卓府,马大夫家和蓝公馆都逊色得多。卓府的院子是以前的昆王府,是个七进院子,还有大花园,可以由四院的一道门抵达。“李天然一进园子就感到这是另一个世界。而且跨了一个时代。”院子里满是洋派的味道,“正有个人在弹钢琴,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拨弄着大提琴伴奏。客人一圈圈,一堆堆,有的围着草地上几个炭火盆暖手说话,有的坐在桌边用餐。轻轻的刀叉声倒是没有扰乱水亭那边飘过来的《蓝色多瑙河》。这里的客人没二院三院多,可是比较突出。大都是年轻点儿的,大都是洋装。”富人阶层所在的四合院掩藏在深深的高墙之内,内部歌舞升平,一派洋气,与外界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四合院在这里成为了某种异托邦式的存在——在这个空间内,新与旧并置,中与西结合。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空间均在此汇聚,这也是李天然产生“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且跨了一个时代”这种感受的原因。
除了起居场所四合院,饭店也是当时北平上流人士时常光顾的场所。小说中几个颇为重要的场景都发生在一个叫做“银座”的饭店。“李天然一进房间就觉得眼睛一亮。几乎全是白色。家具摆设都非常摩登。女仆接过了大衣,引他到一张乳白丝绒沙发前。他边坐边取下了墨镜。落地灯很柔软,只是靠墙一排玻璃架上的摆设有点刺眼。”这是唐凤仪宴请李天然时选择的饭店,从“银座”这个颇具东洋风味的名字便可知道,这里多日本人。唐凤仪为他准备的是香槟配鱼子酱,“咬了一口,吃在嘴里,一阵‘哔哔卜卜’之后,有浓浓一股腥中带香,喝了一口香槟,更有味道。”
除了日本餐厅,当时的北平还有俄国餐厅。一过东直门大街的北小街上,就有一家名叫“凯莎玲”的俄国餐厅。这是一座红砖小洋楼,两层,二楼地方不大,只有三张桌子。李天然去的那日,虾炸得非常好,随咖啡一起上来的还有一盘奶油栗子粉。在当时的北平,上流社会人士时常光顾银座饭店、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其中银座饭店多日本人,而六国饭店则以外国人为主。连书中那位外国记者罗便丞也感叹道:“这个时候,有钱有闲,住在北平,可真舒服……”。

除了幽深安静的四合院、充满异国风情的各色餐厅外,百货商场也是当时上流人士的好去处。冬至那天,李天然去王府井中原百货给师叔德玖挑了一顶水獭帽,又在西单商场买了一幅九九消寒图送给美国来的记者罗便丞。而后他再次回到王府井,给自己买了一个银钥匙链环和一件“厚厚沉沉的黑呢大衣”。
王府井和西单是在民国时期北平城中迅速崛起的两大商业空间。虽然王府井在晚清时期便已发展起来,但真正兴旺发达还是在民国时期。王府井商区毗邻使馆区,加之本身是西方和日本势力在北京的副产品,很多店主都是外国人,几乎所有店面都卖洋货。上面提到的大名鼎鼎的北京饭店,就是1907年法国人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建成的,一开始规模不大,十年之后扩建成了一座七层楼高的法式建筑。1915年,洛克菲勒家族买下北京饭店街北的豫王府,建成了协和医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嵌入王府井的外国商家中有7家英国公司、3家美国公司,还有德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的公司。除此之外银行、百货公司、保险公司和旅馆也相继进入王府井。1934年英文版《北平商会会员录》一共列出了136家入会的王府井商家,其中包括外国银行,亨得利钟表店,经营钻石和金银器的利威洋行,经营丝毛鞋帽的力古和新华,经营高档时装、纺织品、化妆品和装饰用品的吴鲁生和福隆,以及涉及拍卖业的品德和恒生公司等等。与此同时,在清末新政的支持下,西单也发展出了一个市场空间。1913年,六家商店集资兴建西单市场。1916年,著名糕点南货铺桂香村在西单开业,伴随着商铺、戏院影院的增加,西单逐步发展为西城的商业中心。
这些新兴的以洋货为主的购物空间,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区分北平城市内部不同阶层群体的物理标识,它们逐渐成为了那些已经确立自身社会地位的精英消费者市场时常光顾的场所。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一书中指出,随着王府井生意的发展,再加上它靠近使馆区的便利位置,外国人成为了王府井十五家古玩店的购买主力。除此之外,中国的富人也喜欢逛王府井,因为那里是北平城中唯一有干洗店、发廊和西药房的地方,那里还有出售最为时尚的西式服装和家具的大百货公司。在一篇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府井商业区营造出的“消费天堂”氛围:
“在这里好像是不分春夏秋冬似的,摩登的密斯们已经都穿上了隐露肌肤的夏衣,老太太却还穿着扎脚的棉裤……商店是一家连接着一家……卖的东西,都是最时髦的衣料,高等化妆品,就是日用杂货也都是极考究的……”
“不分春夏秋冬,”这种丧失时间感的表述直指现代消费内核。这里的商品没有时令限制,涵盖中外最新款式,而王府井的店面内外都装有电灯,不管白天黑夜,一概灯火通明。正如董玥所言,“王府井汇聚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光彩——这是一个无视自然循环、恒久常新的市场。”
这种不断涌入北平的琳琅满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货,在《侠隐》中,也通过李天然供职的《燕京画报》上的广告罗列呈现出了一种消费主义奇观:美国鱼肝油、德国维他命、头痛圣药——虎标头痛粉、鲸鱼羊毛线、柯达六一六/六二〇镜箱、味之素、“奇异牌”收音机、西门子电器、大长城香烟……当然了,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于北平的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费幻象罢了,它们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停留在报刊杂志上,却从来未曾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毕竟在这个城市中,仍有很多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北平的大多数人,在张北海的小说中几乎是隐形的。只有一处,李天然走进胡同里,“后头跟了几个要饭的。他给了几角钱,还有好几个孝子在叫爷爷地跟,一直跟到东四大街才不跟了。”正是这隐蔽而不可见的大多数,构成了当时的北平居民主力。
在《民国北京城》一书中,题为《社会学:诊察城市病》的章节提到,根据1917年一份警察厅的调查报告,大约有1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基本生存线以下。而在1926年公布的《北京社会各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分布表》中,赤贫人口数为42982,占总人口数的16.8%,此处对于“赤贫”的定义是一文不名、没有任何生存手段的人。贫穷的标准则是除非接受赠送和救济,否则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这部分人口数量达23620,占总人口数的9.2%。换句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全部北平人口中,有26%的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曾将北京大多数赤贫者描述为“半死不活”,其中多是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者。支撑这些赤贫家庭的一般都是老弱车夫、小贩、仆役、非技术工人、警察以及店铺伙计,这些家庭里的老妇人和小孩常常去垃圾堆中翻找,将他人丢弃的东西转变为有价值之物。
《侠隐》中只出现过一次的那位乞讨者,在当时的北平其实随处可见。Y.L.童在《北京的贫穷和救济》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乞讨者:
“众多体格健全的人都靠乞讨过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无处不在。一些人坐在路边,把他们不堪入目的伤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而另一些人则会一直尾随过往的行人强行乞讨,这样的行为通常非常的恼人。在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披着破布,半裸着身子,沉重而缓慢地走在街道上,而因为寒冷和饥饿死在街头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与此同时,为躲避农村生活的艰难与战乱,农村难民大量涌入北平,成为了北平的新穷人。作家许地山曾经在小说《春桃》中刻画过这样一对新穷人,主人公春桃和她的丈夫李茂,在乡下成亲当天由于乱兵冲击,两人在逃跑中走散。春桃流浪到北平,“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堆里讨生活,有时沿途嚷着‘烂字纸换取灯儿’。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李茂后来也到了北平,成了一个叫花子。

除了乞讨者和拾荒者,人力车夫也是北平底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6-1937年之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的小说《骆驼祥子》中,老舍所描绘的正是一位当时北平的人力车夫。据“大象公会”《1937北平城市生活指南》一文介绍,人力车(也叫洋车)是当时北平的一道风景。1934年,北平人力车登记数达到54393辆,人力车夫108786人。而1937年北平市人口约为160万,也就是说,每15个北京人中就有一名人力车夫。而一个车况正常的车夫,每天的收入大概能买80个烧饼,月收入相当于如今的2000块钱。可一般来说,这些钱基本就是车夫所负担的整个家庭的全部开销。如此算来,这些家庭大概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根据上文李景汉的划分标准,即刚刚跨过贫困线。在小说的开头,老舍开门见山地为我们介绍了人力车夫系统中的等级规则。在当时的北平,人力车夫分为很多派别:有年轻力壮的车夫,他们出车和收车时间相对自由,最终或者是拉包车,或者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像后来用三年时间攒钱买车的祥子那样;也有岁数稍大的,因身体或家庭原因拉整天或者半天的;也有年纪四十以上或者二十以下的,他们的车比较破,跑得慢,因此要价也低些。
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眼中,贫穷与犯罪是交织在一起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家严景耀在1926年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将北平的犯罪分为经济罪、性欲罪、仇害罪和政治罪四类。当时北平的大多数犯罪(84.55%)都可以归为经济罪,包括窃盗、欺诈取财、强盗、诱拐、鸦片交易、赌博等等。而在25-29岁的男性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是偷盗和抢劫,女性犯罪中也有82%的人有经济动机。在研究中严景耀还发现,45%的罪犯生活在城里,37%生活在城外,另外有超过17%的罪犯居无定所。而在城内的罪犯中,大部分生活在外城,集中在前门外的贫民窟和天桥周围。在冬季里,他们白天设法乞讨到六枚铜钱,晚上则蜗居在二三十个男女混住的避难所,夏天就干脆露宿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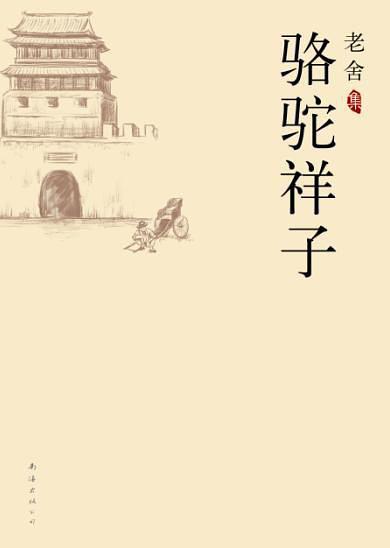
“一鼻子臭味儿不说,沿街到处都是地摊儿,修皮鞋的,粘扇子的,锔碗儿的,剃头刮脸的,磨剪子磨刀的,卖估衣的,打竹帘子的,捏泥人儿的,吹糖人儿的,编柳条筐的,焊洋铁壶的……‘也没人管,爱摆哪儿就摆哪儿’!”
李天然的师叔德玖去天桥的时候,着实被上面这番景象吓着了。其实在正阳门大街和珠市口拐角下了电车就有点预感,“黑乎乎的人群和灰土”告诉德玖,如今的天桥大变样了。“什么‘新世界’、‘城南游艺园’、‘水心亭’,这些他从前逛过的场所全不见了。戏园子,说书馆,落子馆倒是跟从前差不多,只是一个个都显得破破旧旧。”
天桥原本得名于明代建造的一座桥,是皇帝每年从皇宫到天坛和先农坛主持祭礼所用。1907年桥被拆除,但名称沿用。天桥区域在外城共占地2.5平方公里,位于皇宫正南方,北起东、西珠市口大街,南至永定门,西起东经路,东至天坛。
德玖提到的水心亭,是1917年由商人捐助修建而成的,1920-1921年间被烧毁。在当时,天桥算得上是北平的一处上等休闲中心,到1926年,内务部决定拆除先农坛外墙,将土地出售给商家,一些市场逐渐在天桥开张,天桥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上流社会名望。在德玖生活的那个时期,天桥已经成为了北京最廉价的市场,是并不富裕的城市居民购买日常所需之处。但逛天桥的不限于贫民百姓,也有“有西装革履的少爷,有奶妈跟着的小姐,有穿着校服的学生,还看见两个童子军……”天桥还是外国人时常光顾的场所,尤其是当时居住在北平的欧洲和美国妇女,她们喜欢在这里购买便宜的二手皮草、丝绸、刺绣和衣物。德玖看着这番景象,“说不上来这种变是好是坏。”

德玖对于天桥这种无法诉诸言语的感受,实际上体现了天桥的复杂性。它多元、杂乱,甚至充满危险,它难以像百货公司那样被清晰归类、它持续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目光。不同于百货公司那种门槛较高的消费场所,天桥汇聚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其中贩卖的商品也自然五花八门。据1930年《北平日报》统计,民国头十九年间天桥有三百余家注册店铺,其中包括八十二家二手服装店和七十九家绸缎庄,三十七家饭馆、三十家茶社、六家酒铺、一家茶店、七家洋货行、三家钟表行、一家西装店、二十四家杂货店、二十一家木器行、十六家刷子点、 三家草帽店和两家鞋底店和四家鸟笼店。除此之外,天桥还汇聚了三家照相馆、十七处吸“白面儿”的以及大量的妓院。甚至还有二十余种室外娱乐项目,包括说唱、评书、相声、把式、摔跤、魔术、春宫图,一应俱全。在董玥看来,天桥如同一个大熔炉,收纳着无家可归的乞丐、猎奇的外国人,也收纳着各种来历不明、几经转手的商品。
二手货是天桥的显著特点,也是它区别于售卖崭新商品的百货公司的主要特征。在天桥市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二手货,他们是商贩从北平各个地方的家庭、当铺、收破烂者那里低价收购的。其中,做绸缎、鞋子、香烟和钟表买卖的生意人最喜欢“卖假货”——绸缎庄将旧布匹浆洗,变成光鲜的“新布”;酒铺为了赚钱,不仅往酒里掺水,还加砒霜、鸽粪等等。在这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购买的商品质量之间并无正向相关,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较高的消费者并不能在天桥获得百货公司里的购物体验——社会地位越高,经济实力越雄厚,就能买到质量越好的商品。恰恰相反,天桥的消费体验亦是混乱无序的,接近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狂欢,它打破了百货公司精心营造的社会等级和秩序,让人们的购物行为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上流人士和底层贫民回归平等,融为一体,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机智狡诈、费尽心思、投机取巧的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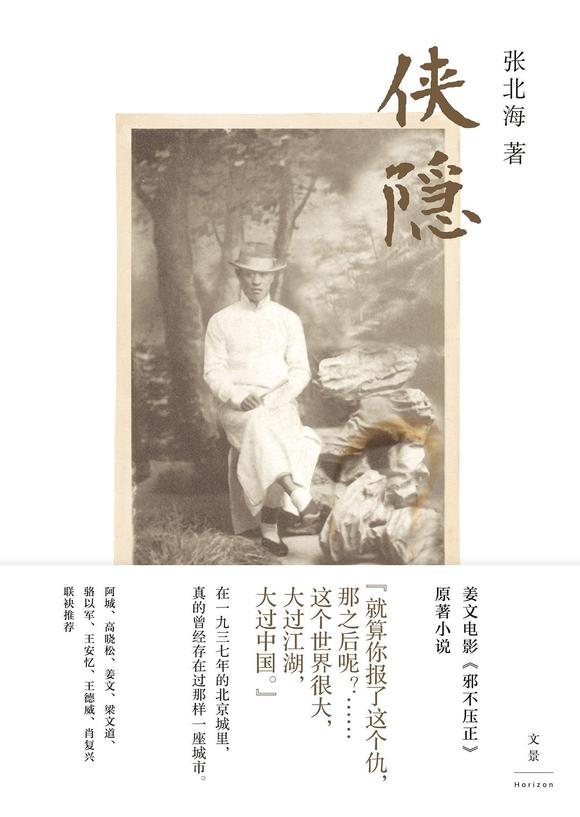
参考资料: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董玥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0月
《侠隐》,张北海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7月
《骆驼祥子》,老舍 著,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3月
《春桃》,许地山 著,北京阅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