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南方适宜农业生产,为什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到了两宋时期才实现了黄河流域古来有之的人口密度?安史之乱是否与中国古代的鼠疫疫情有关?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进程的另一种视角。

如今,许多人早已从书中或电视纪录片中了解到,在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一个小部落可能因为一个外来人带来的流行病而全军覆没,因此,死于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的印第安人,实际上要远多于战场上死于欧洲人刀剑与枪炮的人数。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也曾在他的知名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到这一段历史。实际上,戴蒙德的思考与结论深受一位历史学家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了。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2016年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观点。
麦克尼尔看到,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历史当中,西班牙人以不足六百人的兵力征服了人口数百万的阿兹特克帝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阿兹特克人遭遇到了西班牙人习以为常的疫病——天花。在公元前430年左右的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当中,人们常常将雅典的失败归结于政治体制等因素,麦克尼尔则指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场瘟疫改写了这段历史及其后续的历史……
可是,长期以来,瘟疫其实一直都是史学家忽略的对象。麦克尼尔认为,这是由于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常常来源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以至于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同样的疾病在熟悉它并且具有抵抗力的人群当中流行和当年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爆发,会产生天差地别的效果或影响。而且,历史学家低调处理疫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刻意突出那些可以预计和可以控制的因素——如果把疫病看作一个时代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过去的历史解释力就会变弱。
在麦克尼尔1976年首次出版、至今影响依然广泛的学术著作《瘟疫与人》一书中,他所做的尝试正是把疫病纳入历史诠释的范围,“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在他以后,疾病、细菌、气候、动植物以及整个环境,都逐渐从历史的布景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无论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是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哥伦布大交换》,无不受到了威廉·麦克尼尔的启示。

威廉·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牛津大学教授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语)。在论述罗马帝国的奔溃、欧洲的扩展、大英帝国崛起等历史现象时,麦克尼尔都能够指出疫病在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瘟疫与人》并不是一本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作者在其中也讲述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瘟疫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对疫病的适应反过来又如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一直以来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既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地位十分显赫。而同一时期的南方,虽然拥有温暖气候、充沛雨量、肥沃土地等优越的条件,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江南地区依然地广人稀,经济停留在原始状态。从东汉末年开始,军阀混战,导致黄河中下游地区“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在北方经济遭到破坏的同时,大批农民为了逃避战乱南迁到江南流域。从东晋到隋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生产遭到破坏,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逐渐赶上。到了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族群掠夺中原,而相较之下,南方却有着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造成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甚至形成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的局面。南宋的建立更是被视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时间上的分野。从此以后,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
一直以来,寻求稳定的政治和生产环境都被看作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不过,威廉·麦克尼尔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的前提是一个新视角上的新问题:既然南方适宜农业生产,为什么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直到两宋时期才实现了黄河流域古来有之的人口密度?
在威廉·麦克尼尔看来,大多数时候,人的生命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型寄生”构成的平衡体系之中。“微寄生”指的是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这些微小寄生物能够在人体组织中寻找到可以为生的食物源。从“微寄生”的层面来看,古代中国人在南下潮湿地区时,越往南行进,越受到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等疾病带来的威胁。虽然长江流域温热的气候、丰沛的雨水都对农作物生长有利,长江也没有黄河那样有沉积物淤塞在下游河道的问题,但是南方湿热的环境却可以滋生出更多的寄生物。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这一问题上进展非常迟缓。
而“巨型寄生”主要是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且消费食物,因此成为了依靠生产者为生的巨型寄生者。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皇帝、官僚等统治阶层就是依靠压榨农民维生的巨型寄生者。从“巨型寄生”这一层次来看的话,过去,从在黄土地上进行旱作,到发展出与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灌溉农业相适应的水利技术,耗费了古代中国人数世纪的努力。在约公元前600年以后,中国人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以及传染病的适应方面,都获得了在黄河流域冲击平原生存的能力。而在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实现了政治统一以及建立在农民身上的稳定的“巨型寄生”关系。收租的地主和收税的皇室官僚这两大“巨型寄生”与农民之间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平衡关系,他们虽然对农民进行了剥削和压迫,但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也会控制权力的滥用,让农民依然能够实现基本的生活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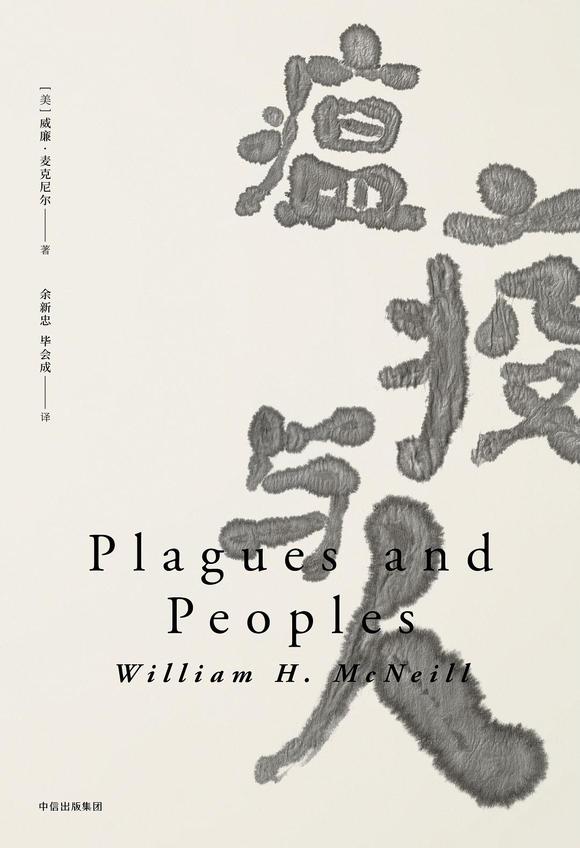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葛洪《肘后备急方》等文本中,威廉·麦克尼尔梳理出了中国的几次重大的疫情。在公元161年、公元312年、公元322年前后,三场瘟疫曾经引发了特别突出的大规模死亡。在公元37年至公元653年之间的某个时刻,天花和麻疹这种人们过去未曾接触过的新疫病也从西北跨越大陆,来到了中国。在公元542年入侵地中海的鼠疫,则在两代人的时间之后,于7世纪初经由海路来到了中国,在沿海省份引发了大规模疫情。762年“山东省死者过半”,到806年浙江省也出现了类似的死亡率。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由于这些疾病,中国人口在公元2年统计的大约5850万的基础上急剧下降。而瘟疫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政局:安史之乱(公元755年)之后的中央集权的奔溃,时间点上与鼠疫疫情爆发极为相近,因此威廉·麦克尼尔推测,鼠疫很可能使得政府无法从未受动乱影响、却遭到疫情蹂躏的沿海省份征集资源、镇压动乱。因此,皇帝只好请求回鹘军队提供帮助,导致回鹘人迅速把帝国财富转为了己有。
同传染病接触的增加使得死亡人数开始降低,早先疾病的侵袭增加了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比例。由于传染病发作的间歇期缩短,假定某种疾病时隔10年复发一次,只有经受过上次疫情并存活下来的人,才会有孩子。就这样,一种传染病让幸存者获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间隔复发,这样的传染病便会成为“儿童病”;相较于袭击整个社会的疫病来说,“儿童病”给人口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宿主和寄生物迅速地进化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存模式。到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同困扰祖辈的疫病已达成了生物意义上的成功调适,人口开始迅速增长。
在过去,疟疾、血吸虫和登革热很可能阻碍了人口的南移。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复原中国农民如何适应南方生活环境的过程,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直到8世纪,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人口的稠密现象尚不明显,到12世纪,成千上万的稻农才充实了华中和华南相对广大的区域。
在1200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约1亿。要实现这样的规模,他认为必须要具备两点条件:一是在“微寄生”的层面上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达到互相适应,二是“巨寄生”的关系得到规范,能够让农民留下足够的产品,维持很高的自然增长率,因为只有这样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人口稠密程度。
“巨型寄生”的层面的调整与“微寄生”层面的发展齐头并进。随着宋朝的建立,虽然北方依然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相对有效的官僚制度已扩展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科举制作为一种相对合理的培训和选拔高级官员的方式也已经定型。虽然官僚压迫并没有结束,但是,对官僚阶层的制度性监督可以限制明目张胆的腐败。当南方农田得到开垦,迅速增长的人口依然可以吃饱饭,这样一来,传统的租税依然可以让农民生活下去。而另一方面,正如同外来的疾病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引发并维持了某些抗体一般,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融入了官方儒教当中,构成了道德和智力上的“抗体”,抵御着其它外来宗教的拯救之路对农民和其它无教养阶层产生的诱惑。就这样,中国在适应巨型寄生的关系上也取得了成功。
本文写作参考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以及《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中信出版集团,2018)。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