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很脆弱的,人不见了,文学就完蛋了,整个消失。”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
从2018年3月出版到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集《雨》,在豆瓣上被222人标记在读,527人标记读过,8843人标记想读——这对一本短篇小说集来说着实是个不错的数据。就连负责此书的后浪出版社编辑、同为小说家的朱岳也在豆瓣上说“第二次卖断货,有点生自己气”,因为“印少了,人穷志短没魄力”。《雨》是后浪华语文学系列中的一本,也是黄锦树在大陆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第一部是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死在南方》,距今已有11年。
这部潮湿的、夹带着来自南洋的风和雨水的《雨》,收录了黄锦树2013-2015年间创作的16部短篇小说。其中有8篇,是以同一个舞台(橡胶林)和四个相同人物(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为基础写成的变奏作品,通过人物轮替的在场与缺席、死亡与重生。他写马来西亚胶林中的童年、写不知是梦还是现实的记忆碎片、写胶林中的大黄猫和老虎,也写曾经日本人和华人在胶林中的对抗与博弈。
对于大陆读者而言,胶林中吹来的湿润的风、连绵不断的雨、胶林中蛰伏的身体硕大的蚂蚁和目光炯炯的老虎散发着别样的吸引力,它们带着南洋的异域风情,带着万物有灵般的奇幻体验,也带着一段与马来西亚华人有关的复杂纠缠的历史图景。也是凭借对于故乡马来西亚不倦的书写,黄锦树曾斩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小说奖首奖,以及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他日前来到北京,获颁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文学奖对于外人或许不足道也,但却是文学界内部选拔文学新人和竞争文学话语权的重要场域。而话语权,正是来自华语文学边缘地带的他所看重和奔走呼告的。
在黄锦树看来,马华文学处于华语文学“鄙视链”的最底端,马华文学的背后是已经消失的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华人文学。他悲观地认为,马华文学最终也会消失,因为“文学是很脆弱的,人不见了,文学就完蛋了,整个消失”。如今,马来西亚国内的华文教育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种种因素让马华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因如此,黄锦树对于马华文学怀有一种使命感,总是力图在华语文学的场域内为之争取更多话语权,让更多人了解和看到马华文学。
4月底,借黄锦树来北京领奖的契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黄锦树进行了专访。作为1986年从马来西亚赴台求学,1996年至今在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文学老师,黄锦树拥有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这也让他的小说充满了可以自我解读和自我剖析的空间。在黄锦树看来,如何定义好的小说?小说的技艺意味着什么?马华文学内部的脉络及其与台湾和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马华文学内部是铁板一块吗?又需要应对何种危机与挑战?而作为一直致力于书写故乡的马华作家代表,马来西亚对黄锦树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故乡的执念在文学上的意义何在?作为处在华语文学“鄙视链”底端的马华文学代表,在文学领域对于霸权的挑战和抗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有是否可能损害文学本身?针对上述种种问题,黄锦树在访谈中一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界面文化:针对你曾经提到过的“问题小说”这个概念,我们能否理解为是由问题意识推动的小说,而引发这种问题意识的,是一种对于马华文化的危机感?
黄锦树: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都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意念先行,而是借由小说来思考特定问题。透过论述方式可能没办法清楚表达,可能变得教条;小说则可以让我们更微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问题小说”,有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比如马共(注:马来亚共产党的简称,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到底怎么回事。我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不断学习,一方面是为了思考马共的存在或者华人史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是为了小说本身。不仅为了一个问题而写小说,还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我这个小说艺术的开展有什么帮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界面文化:但你的写作确实有很多对于马华文学的思考,包括对于国族、身份危机的探讨。
黄锦树:这是没有办法的,基本上是我的处境决定的。我的很多文章也谈过,有的前辈或者同辈一直要把马华身份去除,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马华这个身份就是很边缘很地方的,这是所有思考的起点。我们被生在马来西亚就决定了这一切,即便这个身份被刮掉了也能轻易被还原。
界面文化:你之前也谈到,马华文学内部也有不同的流派,能展开讲一下吗?
黄锦树:年轻一代没那么明显,早期受到中国革命文学影响的一批人没有论述能力,直接从中国照搬,形成了所谓的现实主义,后来有一波现代主义对抗它,再后来是后现代。其实马来西亚没有多少东西,所谓后现代都是假的,都是从台湾转口进来的。台湾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但马华文学从事的人很少,写得好的更少,玩不起这样一个跟随和模仿的游戏。因此马华文学写作者要想清楚,在这个位置自己能够做什么。当然有的人是本身的性向问题,他觉得自己只能够处理同志题材——但那是小众中的小众,边缘中的边缘,更加少。
界面文化:在《雨》的跋中,你提到马华文学自诞生以来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30年代受左翼文学支配,直到70年代,这里也造成了一种观念,即低技术要求的写作便足以反映现实,而艺术的要求毫无必要。在《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一篇中,你写到“像一篇写坏的文章,因过于年轻而不懂得技艺的微妙”。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十分看重小说技艺,你的小说写作是反对这种低技巧观念的一种实践吗?
黄锦树:当然啊。我们都努力告别其实早已破产的马华革命文学。我们都是努力在学习,从一开始的不懂,慢慢就知道:一方面马华文学是跟台湾文学最近,因此整个台湾文学场域所有的名家,基本上该看的都看了;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八零年代文学爆炸,从韩少功一路往下,从莫言、苏童一直看到余华、格非,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同时,我们也向翻译作品学习,比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等等。这是技巧本身,可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是一个艺术品,不是一个宣传品。不管要表达的是什么,技术层面都是一个基本要求。我不能忍受那种技术非常差的作品,除非它里面有一种独特的原创性,可是不容易遇到。
界面文化:一方面小说是需要技术的,另外一方面如何避免你刚提到的对于大陆台湾或者是外国文学的模仿?
黄锦树:这个看个人修为。有的人学习某个对象,就会带着那个对象的腔调。但写作的人要有一个自觉,一开始很迷恋某个人没有关系,可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和他/她告别,不然一辈子都是某人的影子。这是一个写作的基本常识。
界面文化:还有一个和技巧有关的问题,你在一篇访谈中提到八十年代末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委张大春的技巧至上主义,并且你后来写了《谎言的技巧与真理的技术》批判他,你对于他的技巧使用的批判具体是什么?
黄锦树:张大春当时整个的姿态是后现代主义,学院里有些教授一直为他捧场,文学批评界的名流也全部都一致叫好,从王德威、蔡源湟、杨照到林耀德等。他这种技巧至上主义非常红,所有人都认为他当时是最有希望的中文小说家,没有第二人。他在很多文学奖评审里都是决审。在整个文学奖机制中,如果有人非常推崇某一篇,并且很会讲话、很会论述的话,基本上那一篇就会通过。其他人讲不过他,不服气的顶多是评审里的一个到两个,他如果很强势的话,最终也会说服不同意见。我那时候也开始写作,我会仔细阅读当时不同的大型文学奖的评审记录,可以看到他每次挑的作品都是某一种类型,或者说,可以看到他总是贬抑什么。
界面文化:具体是什么类型?
黄锦树:技巧非常好的,比如袁哲生的《送行》和骆以军的《手枪王》都是他力荐的。因为我自己当时也在学习、在理解小说,他又是文坛上最强的势力,是大家的模范,所以我对他的作品也非常熟悉。他那时候就玩所谓的后现代技巧,他挑出来的作品是一回事,他自己的展现其实比他挑出来的作品更加技巧至上,包括他的短篇小说集《公寓导游》 和长篇《大说谎家》等。他的短篇小说《将军碑》也非常有名,获得了1986年第9届时报文学奖的小说首奖。他是台湾后设小说(又称元小说、超小说)的最早的操演者之一。他反记忆,反历史,拆解乡土,一切价值都被他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疑惑:小说到底在做什么?小说难道就是为了虚无而写作吗?我怀着这样一个问题写了这篇《谎言的技术与真理的技艺》,算是清算张大春以及张大春所代表的一种小说作风。

而具体到文学奖,就比较复杂。因为有的作品其实技巧很简单,但其实是有意为之的,可以看到里面有某种力量。遇到这种在技巧上故意显得质朴的作品,我们会比较谨慎和小心,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作者,看他/她的其他作品,看是真的技巧不好,还是有意为之。这种其实非常厉害,故意用最初级的技巧来测试一下这个文坛。
回到张大春,他的小说实践——比看他的评审记录更清楚——呈现出一种彻底的虚无。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他其实很不喜欢也瞧不起现代小说,他操纵这种技巧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老外的玩意儿我也会玩,我玩得比任何人都好,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可这后面的价值其实是虚无的。我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如果让他这样玩下去,台湾的现代小说会被整个毁掉。
那时候张大春才三十几岁,汪曾祺的小说开始引进台湾时他很称赞。他有篇文章叫做《随手出神品》,称赞了汪曾祺的《八千岁》,他说汪曾祺的小说是“真正的中国小说”。我也看过他的一篇文章讨论所谓的“中国书场”,发现他最推崇的是笔记小说。在他看来,五四以来整个文学道路都走错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他这么虚无,原来他认定小说不应该这样写,小说应该用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方式走,他的价值观原来是这样的。
那问题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死命写一些现代小说?写那么多,而且把所有的技术操演一遍?就我刚刚说的,他要毁掉它。问题是这种所谓中国书场的小说能够走多远?我是很怀疑的。如果这条路那么好走、那么有可能性的话,为什么像鲁迅这些人会引进一套全新的东西来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张大春想象的好的小说,他没提沈从文,他提高阳(高阳,历史小说作家,代表作有《胡雪岩》《慈禧全传》等),高阳是他真正的老师。他后来走向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回到用中国传统素材,用笔记小说的写法,都是一种传奇故事。坦白讲这里面没有真正思考的层面,因为中国书场本来就是娱乐的产物,是大众娱乐早期的市民阶级的玩乐,所以它绝对不可能是“问题小说”。因此总体来说,我认为张大春矛盾重重。
但我们很多人都受惠于他,他毕竟大我十岁左右,也是骆以军的老师,所以很多技巧我们是跟他学习的。去年在台湾获奖很多的黄崇凯的《文艺春秋》,还是可以看到张大春技巧的影响。但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就跟他告别,每个人的告别方式不同。技巧对张大春来讲可能是一个表演场,对我们来讲不是,技巧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做一种探索问题的途径,这样就避免陷入虚无。

界面文化:可以看出来,在《雨》这本书中,你对于技巧的使用极其娴熟,尤其是作品X号系列,其中有相同元素的堆叠、相同主题的变奏,作为能指的象征物在不同篇章中的不同所指,相同人物在不同篇章中的缺席或者在场、死亡或者重生。当时为何想要构思一个这样的系列?
黄锦树:本来只想写四篇,就是四个角色,每个角色死一次,每次有一个人不在场,这样变奏。像绘画也很多这种,一号作品,二号作品……
界面文化:但这样会不会又变成一种纯粹技术上的游戏?
黄锦树:不是。你会看到历史进来,写作不是在真空环境发生,很难避开历史。在大陆,如果角色设定是一个二十世纪三零年代的人物,他一定会遇到日本侵华,离散,灾难一样一样的来。马来西亚情况一模一样,这段华人史我们不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小说本来就是处理可能性,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游戏”,不知道你如何看待卡尔维诺或王小波的小说?总的来说,这是我的小说课,也即我的人生课。
我在《雨》的后记里也讲到,我小时候到青少年时期都是住在胶林里,其中有很多生活细节。我最早的小说因为技术比较不好,所以会用很多经验性的自传性的元素。但到了这个阶段,我用一点点经验材料就够了。我家里其实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如果太贴近经验,那这个故事会很复杂很难写,不能够让某些人跑龙套,所以我把故事精简化,变成四个人物,父母加两个小孩,排列组合比较容易展开。但是有些基本背景,包括日本南侵、马共、种族这些历史元素免不了会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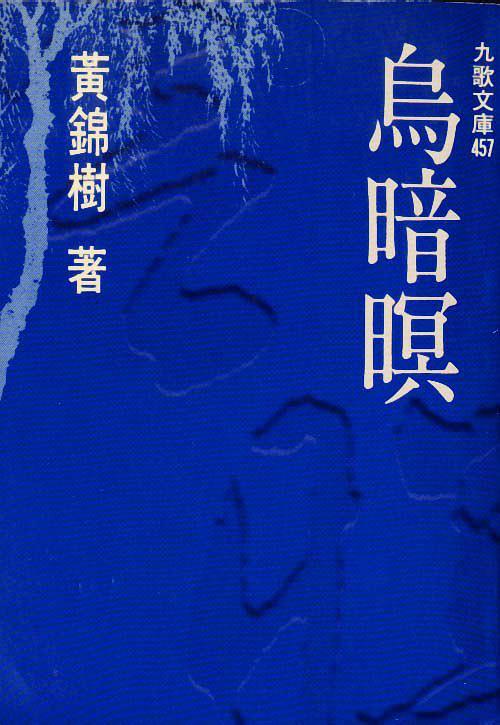
我们往过的所谓马华现实主义小说,只要写到胶林,就是愁苦,隐喻一种受苦。马共也把它当做一个隐喻,胶林割下去,汁液流出来,流失殆尽后就把整棵树砍掉。但胶林不应该只是一个悲伤的隐喻,里面其实有痛苦也有欢乐。另外的一种方式是一些用幼童视角去书写的胶林题材散文,又太快乐了,好像纯粹是一种诗意的、童话式的、美好的回忆。因此我想传达的,是一种带有恐怖意味的、诗意的童话,可以避开以上两种对于胶林的刻板印象。
界面文化:说到历史,我注意到有一篇小说使用了很多有关日本人如何对待马来西亚华人的真实历史材料。
黄锦树:那段历史其实是很残酷的。马来西亚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当初日本人来的时候做足了功课。因为台湾当时属于日本,有一部分台湾人被日本人送去马来亚前都被要求学习马来语(1957年马来亚建国,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以方便和马来人沟通。日本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分化了三大民族:游说印度人回印度抗英,搞印度独立;帮助马来人赶走英国人,解放马来亚,因此马来人后来的主流论述基本上是感激日本人的。事实上可能也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外力进来,英国人可能不会走;华人就是在抗日,而凡是有抗日的地方就有大屠杀。日本人很早就派一些伪装成商人的日本间谍对华人的整个居住状况做过完整的调查,我在台湾看到过一本重印的日本人编的书,都是马来半岛各小镇有头有脸的华人的资料。比如他们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他们的隔壁是谁、哪一家最有势力,日本人对整个华人市镇了如指掌。所以只要听到一点抗日活动,就开始大规模屠杀。但马来西亚官方完全不理会这段记忆,他们认为这是华人的事情,因此政府常常对华人设立的抗日纪念碑颇有意见。
界面文化:《雨》这本小说中最后三篇在场域上其实不限于胶林这个环境,那么后三篇和前面以胶林为主题的小说之间有何种关联?这是一种断裂吗还是合起来构成了《雨》的整体?
黄锦树:你说离开胶林,其实没有。只不过我用了更复杂的方式来呈现,这当然跟里面预设的一些互文有关,比如跟我写过的一些散文、小说有关联,有的东西已经在别的地方出现过了,就不用展开。除非读者对这部分有相当的了解,不然读者只是勉强看到其中一条“折痕”而已,他不知道有东西被折叠起来,不知道要打开。
《后死》中的Belakang Mati是比新加坡还南的一个岛,是南方以南的一个场景。那个岛现在属于新加坡,在历史上可能属于寥内群岛,是印尼群岛的一部分。因此这当中有一个地理轴线的移动,从半岛移到半岛的南端,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关系。整个马来亚建国是一个复杂的计算,本来婆罗洲跟马来半岛一点关系都没有,砂朥越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后来被日本人搞得很惨之后,不得已才让渡给大英帝国,和马来半岛在历史上没有太大关系。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关联很深,尤其以华人历史为例,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这三个地方叫做海峡殖民地,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半岛本身比较内陆,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所以新加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直都是华人最集中的地区,有华人精英、富商以及所有的公共建设,包括电影院、印刷厂。1963年,李光耀野心勃勃,尝试合并后建立一个多元种族马来西亚,他喊出的口号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当时马来人就吓到了,当时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是一比一,李光耀这个呼吁如果实现,他可能变成马来西亚的总理,马来人怎么可能接受?他们觉得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你们都是外来者。所以才有了1965年新加坡(被)独立。
对我来说——我可能已经是老一代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该是个整体,但是华人群体从来没有探讨新加坡分割对于马来西亚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完全是政治的划分,莫名其妙,一个关联不深的婆罗洲拉进来,另一个历史渊源那么深的新加坡却要割掉,单独建立一个国家,几十年之后,一个变成欧洲一个还是非洲。因为这种种族政治留下的伤害一直在,所以我的叙述一路往南,一直包含新加坡。曾经有一位评论人认为《南方小镇》中场景没有太大的移动,但实际上移动了很多次,你会看到一部分在台湾地区,也有一部分在新加坡。这一篇的空间为什么要移动呢?这不是我要解释的,我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当然那几篇变奏的,场景比较固定,就是同样一个舞台。那至于场景变动的和场景没有变动的关系如何,就让有心的读者自己探讨。

界面文化:你在一个访谈中提到,至今仍有一些看法认为,到台湾留学的人对马来西亚的认识停留在离乡的十九岁,而看你这本书,写的很多也是对童年故乡的怀念,那么在你看来,离乡多年有必要保持和故乡的联系吗?书写故乡是否就一定要了解故乡的当下,还是你现在想书写的就是记忆中的故乡?
黄锦树:我不断回应这个问题,这是标准的愚蠢问题之一。在我刚来台湾留学的时候,几乎看不到马来西亚报纸,家人从家乡寄过来要花上一两个礼拜。但现在是网路時代,我们的资讯和故乡基本上是同步的,只不过他们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不能参与。也就是说,这个不在场一直变成我们的原罪,彷彿离开就是不应该的。其实我们对故乡的认知很多来自专著或研究论文,个人见闻毕竟太过有限。
我后来一直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其实他们是把民族国家整个内化了,想任何事情一定会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国籍、整个公民身份得来不易,所以内化之后大家非常紧张,觉得这个身份无比珍贵,很容易产生认同焦虑。马来人会认为华人坚持华语、坚持民族文化是不应该的,华人中有些人也将其内化,认为华人要努力学好国语(马来语),甚至用国文写作,根源还是认同焦虑。
很多这类问题的产生,都和民族国家有关,就是透过国小、国中教育把很多价值观和历史解释内化,这些华人不敢去骂马来人,所以就来质疑离开马来西亚的人,离开好像就是对不起国家民族。我这次获奖之后,我以前的一个已经回马来西亚教书的学生转来一则信息,说恭喜老师得大奖,然后感慨马来西亚人才外流。我听了就很头痛,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台湾刚得一个小奖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呼唤我们回去爱国。
我曾写文章谈过,这些整天叫别人回去的人有没有看看那些真的回去从此二三十年默默无闻消失在文坛的人,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些人?这些人很多。我前几年和朋友合编了一本《我们留台那些年》,让大家写一下留台时光,收稿很踊跃,编得很顺利。续编《返马篇》来稿很零落,几乎编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回去非常辛苦。我们念完大学大概二十二三岁,回去有工作压力,台湾文凭大部分在马来西亚是不受承认的。你得去找工作,要有稳定的工作;多数会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家庭压力,有小孩要养;父母老了要照顾,有的还得照顾兄弟姐妹,所以根本不可能写作;如果有点剩余时间,看看娱乐节目就已经很开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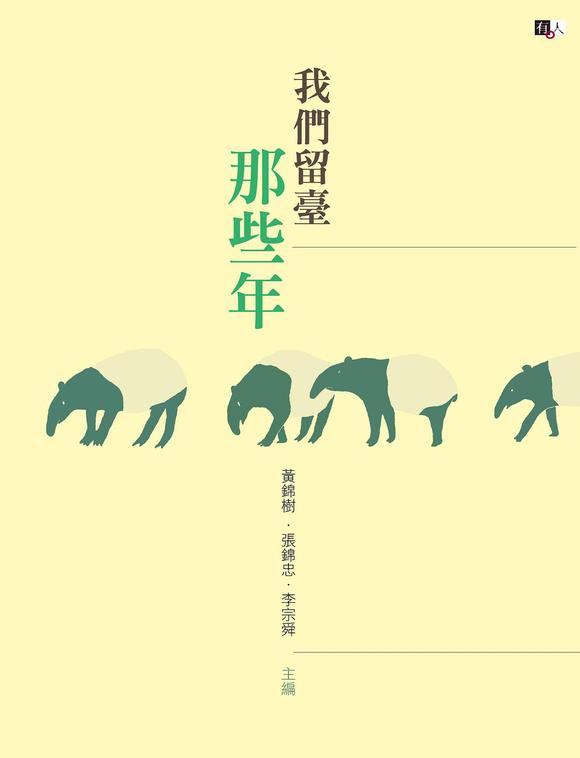
尤其对文青来说,他们不愿意去回忆这一段。有的人到了退休之后才重新开始写作,从散文开始,中间至少二十年都荒废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问题是质疑我们不在场的人,从来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有表现的仿佛变成一个靶子,只要头伸起来,就很好打。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回应过这个问题,我引用的是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小说家略萨,他说:如果留在外面对写作有帮助,就留在外面;如果回去有帮助,就回去。为了写作,就这两个选择而已,很简单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同乡为什么想不明白这个小问题,我不是很想回应,愚蠢问题回应了没什么帮助,但有时候就是不得不回应。
界面文化:你刚提到《雨》这本书比较像童话,而确实也有儿童视角在里面,如果说这本书是有自传性成分在里面的话,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写的其实还是一个记忆中的故乡而不是现在的故乡?
黄锦树:因为胶林已经不见了,殖民者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巴西把橡胶树移到马来半岛大面积栽种,因为纬度类似,他们在新加坡植物园种植成功之后就在马来半岛大面积推广,非常成功。最早橡胶叶需要到亚马逊流域的原始森林中寻找,尤其是刚果,殖民者强迫当地黑人到处搜寻。直到现在橡胶还没办法人工合成,只能是天然的。
一方面因为马来半岛的锡矿的发现,另一方面是橡胶树,所以需要大量劳工,英国人因此引进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下南洋的。有一次我回马来西亚发现以前是橡胶树的地方已经全部变成油棕树,整个景观完全不同了。从我祖父那一代,到我父母一代,直到我小时候,都有割胶的记忆,而我现在四五十岁了,整个地表场景完全被铲除了,坦白说我很吃惊。我们太熟悉那种胶林的感觉了,虽然不是雨林,但也是树林,而棕榈树就完全不一样,像是沙漠植物。
再下一代不会有胶林经验了,至少在马来亚这块土地已经没有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伤逝。我最后一篇也写到,这跟我母亲过世有关。我祖父母和父母两代人都过世了,两代人都是割胶的,我们小时候参与过。如果没有离开马来亚的话,我一个可能的人生,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去割胶。那个时代没有太多选择。但胶林突然的消失促使我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很感慨,因为很多人的故居尚在,可以还原,而我们热带是这样:在树林里盖一间木板房子,无人居住后很快有用的东西就被别人拔走,蚂蚁把木头吃掉,新的树木又长出来,房子完全消失,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灶台,因为它是水泥做的。我们一代一代的记忆都是这样,留不下来。
在整个故乡的写作者中,到目前为止比较在意胶林消失的、会特地花很多篇幅去写的、为它编一本书的,可能也只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编那本《胶林深处》时尽量找最开始有涉及胶林的写作者以及写得比较好的作品,收录整理,我这一代之后也就没有了。后面的世代很多都是都市的孩子,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后,乡村经验已经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
我早已没有故乡。故乡只在我的写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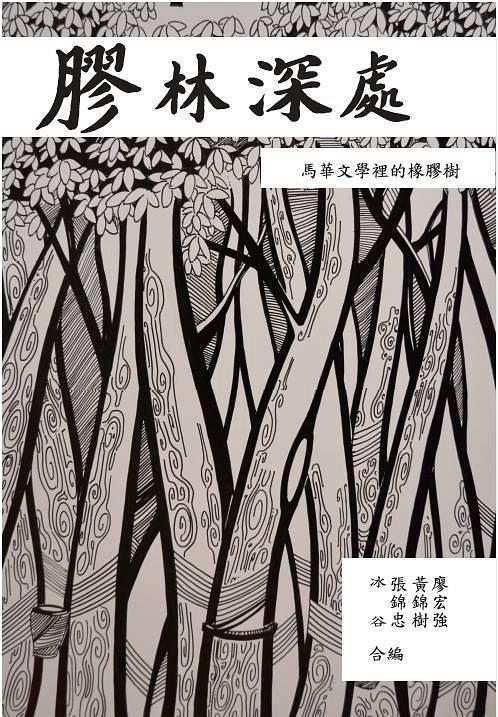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在《小说课》里两次提到了文学奖的问题,你设置了一位老师教育初学者要努力获奖,而你这次来北京也是领奖的,对于文学奖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黄锦树:文学奖有两种,一种是征选奖,即主动参加然后竞选得奖,对刚入门的选手很重要,相当于获取一张文学入场券,但写到一定阶段后就不应该再参加了。另一种是推荐奖,或者说标志成就奖——给一本书一个肯定,可在整个华语世界和中文世界,普遍缺少推荐奖。推荐奖很重要,但需要有良好的评选机制,也需要好的评论者,这样有助于建立一个时代不同的文学里程碑。我这次来领的算是推荐奖,但对这个奖我其实了解得不太多。
界面文化:在这种推荐奖中,占主导的是文学家的话语权还是作品的质量?
黄锦树:这个是相互的。以我这次参加的文学奖为例,一开始我不知道评委是谁,后来大概知道评委有哪些人后,我大概确定我的书主要是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推荐的,我猜想对于我这次获奖的作品,大家应该是被他说服了。领奖那天的报告说,本来小说这个奖项只给长篇,而我的作品在目前的归类里叫做短篇。当然我对小说分长短还是有意见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文学奖常常是这样,有一群评委是一回事,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去读,真正读得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也参加过文学奖的评选,很清楚在过程中如果没有人极力推荐,很多作品第一轮就自动消失了。
界面文化:所以文学奖的评选还是有很多霸权在里面。
黄锦树:文学奖本来就是一个话语权的竞争,看评委中谁的论述最有利,甚至还牵涉到这个人在文学场域里的位置,这是不可避免的。
界面文化:你刚提到对于长篇短篇的分类还是有意见的?
黄锦树:我最近接受的一个访谈的访谈者在整理我的作品表单时,要注明短篇小说集,我说你不要注明是短篇,注明是小说就好了。至于读者怎么去看,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长期养成习惯,整个文学体制特别侧重长篇。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好几个奖项小说类都只给长篇,短篇或其他类型全部删掉,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当前整个新文学形成的过程中,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后来者居上,长篇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主要是在左翼思潮里推进得比较完整。比如为什么一开始鲁迅都是短篇,他的整个准备那么好。所以短篇长篇其实不是问题,写得好不好、有没有力量才是问题。很多学者一开始就被长短篇问题转移了焦点,很多题材可以一万字写完,偏要写二十万,甚至三十万。从技术上来讲,要写长一点都不困难,所有读过理论的、对小说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很多东西都是不断填塞进去的,这一点卡尔维诺讲过,昆德拉也讲过。所以我认为对长篇的迷恋是一个当代的迷思,很可能无意中内化了整个西方对于长篇小说的期待。小说翻译成英文的情况也类似,老外会觉得写太长了,按照他们的阅读长度可能十五万就够了,你写三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不知道在大陆场域和台湾场域,作家想象的读者是什么?或者说这么长的长篇写作,到底是跟谁在作比较?
界面文化:你在跋中也有提到,学界时常讨论现代性时间上的迟到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文学链条:第一世界(西方)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中的马华文学,对于基本处于世界文学图景链条末端的马华文化来说,不断地发声和抗争以确认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必须?
黄锦树:鄙视链是这样的,中国大陆文学——港台文学——其他,我们属于其他。马华文学不是鄙视链的最底端,最底端已经消失了,比如菲律宾文学泰国文学印尼文学。我比较悲观地认为马华文学迟早会消失。只要华文教育一消失,马华文学就会跟着消失。
印尼的历史是最明显的,1965年大屠杀,我记得印尼的华校本来有一千多间,印尼华人比马来半岛还多,它的华校、会馆、报章杂志都很多。可是政治势力的清扫非常快,一旦大屠杀发生,烧一烧,赶一赶,文学是很脆弱的。人不见了,文学就完蛋了,整个消失。菲律宾也是如此,70年代菲律宾的中学禁止华语教学,全部用菲律宾语,马来西亚也差不多,只不过华人人口太多,废除华文教育一直无法实现,所以才会有文学幸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湾所谓的“侨教政策”(即马来西亚华人赴台读大学,成为“侨生”的政策),让我们在中学之后可以继续学习。但这都是历史的偶然条件,台湾什么时候被同统掉我们不知道,再加上现在留学大陆的人也越来越多,是不是能开展新局面,也很难说。
界面文化:你之前也提到马华文学的状况很复杂,这里头也涉及到文学阵营的划分,包括你谈到的文学奖,也是有话语权的问题,这其实涉及文学里的政治问题。那在你看来,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用政治的话语(比如霸权、阵营)去讨论文学,是否会损害文学本身?
黄锦树:这是没有办法的,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本来就很边缘很脆弱,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评论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是马来西亚设立的华语文学奖项,取“华宗”谐音,象征华人之所宗,即华人所向往、崇仰的事物),声势浩大,每次评审结构要组合的时候,一定要给本地评审位置,可是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目前知道的唯一的最好的就是张景云先生(祖籍福建同安,1940年生于缅甸,二战后在槟榔屿长大,16岁辍学,青壮年时期生活在新加坡,后从事新闻工作,著有新诗集、随笔集和小品文集),他已经快八十岁了,其他那种大学毕业刚回来的,到中国大陆修读博士的,成气候的并不多。这很明显是非常弱势的、没有话语权的。
如果说在地的学者没有强烈的解释能力的话,就只能让别人判断。王德威对我们算是非常客气的,他也尊重我们的论述,也很努力了解我们的想法。但有的评论者虽然有做决定的权力,但是完全不看我们的东西。如果他们敢公开发表言论的话,我们可以回应,可以批评,甚至是攻击。但如果沉默不作声只是投票,那我们毫无办法。但是马华文学很多情况下都是后者,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就只颁给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从来没有给过马华作家,也没有给过马华旅台的作家。余光中、白先勇都是上一辈的人,李永平(华文小说家、翻译家,生于婆罗洲北部,后赴台湾、美国留学,最终定居台湾。小说创作以探讨自身族群以及文化认同为主题,通过书写婆罗洲、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对于原乡的讨论)难道成就比他们差吗?为什么到死都没得奖,死了后就更加不可能了。张贵兴(旅台马华作家,与李永平同为旅台婆罗洲华文文学代表人物)会比他们差吗?。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颁奖者认为还是要仰望中原,中原有两个,一个大一点的中国大陆,一个小一点的台湾。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华文学在论述上、在各方面都一直觉得矮人一等,一直要看上面的意思,甚至很多人努力地想要被承认。这就跟小国本身的状况很像,要独立自主做自己写出有意义的东西,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会遇到解释的问题、遇到认可的问题。如果一直不被认可,很多人写着写着就消失了。我这几年发现若干早期作品很好但未曾被肯定的作家,有的七十几岁了,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了。因此即便出现过好的作家,我们也没有好的评论去保护他们,他们就放弃了这条路,走向大家都走的、比较安全的道路,也就是很平庸的道路,这种状况不是很罕见。
因此我在马华文学的场域常常呼吁,要有一个健全的文学评论机制,后来发现不太可能。一个是写评论得罪人,二来是要非常有鉴赏力,这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中国大陆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在马来西亚。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