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句俗语: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和皮囊,他们的好运和厄运也都得照单全收。

1984年,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河附近。图片来源:Pierre Perrin/Gamma-Rapho/Getty
多年以前,一群追踪来自立陶宛犹太人聚居地凯尔默(Kelm)拉比后裔的系谱学家找到了我(指本文作者Pam Weintraub,《Aeon》心理与健康板块编辑)丈夫。这座贫穷的小镇以严格的犹太教神学训练而知名,《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伦理的核心——这套伦理学体系十分严密,它基于逻辑以及心意纯正的实践,透过冥想的方式来自省与祷告。
根据我们最终收到的电邮版本,这一庞大的系谱涵盖了生活于五块大陆的十六代人持续四百余年的不幸经历。我丈夫的祖先是来自凯尔默的拉比,算得上是社会菁英,在1648年哥萨克袭击尼米诺夫(Nemirov,当时属于俄罗斯治下的波兰,现属于乌克兰)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六千余名犹太人打算依凭高墙固守。不料哥萨克却打着波兰旗号混入了城池,相传他们杀死了许多儿童,将受害者投入装满沸水的大锅,甚至还活剥人皮。尼米诺夫的拉比、丈夫的曾(上溯九代)祖父杰希尔·米歇尔·本·艾利泽(Jehiel Michael ben Eliezer)当时逃向了墓园,盼着至少能给自己留个全尸——但最终却被乱棒打死,暴尸野外,史称“尼米诺夫的烈士”。
屠杀发生后,拉比们四散逃往分布于各“定居点”(Pale of Settlement)的犹太社区——该区域横跨了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欧洲国家的部分领土,犹太人被允许在此生活。1768年,居于乌克兰的杰希尔曾孙茨维·赫希(Zvi Hirsch of Lysyanka)被哥萨克杀害,之前他从基辅附近的家逃出,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再到土耳其边境,一路被追杀了数百英里。四年后,我丈夫的曾曾曾祖父艾利泽·古特曼在立陶宛的普朗格(Plunge)出生了。1810年,他迁到了贫困不堪的凯尔默,任该镇的拉比首领,开办了一所后来远近闻名的犹太教学校(yeshiva)。后于1831年去世,享年58岁。
与许多从乌克兰大屠杀中逃难而来的犹太人类似,19世纪的古特曼一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穷境地。随着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第二次分离,他们被迫承担起繁重的兵役义务,12岁以上的犹太男子都被征召入伍,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服役期限为25年。艾利泽的女儿、丈夫的曾曾祖母瑞贝卡因其生下了四个女儿以及五个儿子,且后来都当了拉比,在家谱中被誉为“黄金贝莉”(the Golden Belly)。她的子孙后代则大多在纽约谋生,与那一代犹太人的基本处境并无二致。
1902年,其中一个女儿成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当时还登上了纽约各大报纸的头条。她们欺诈那些可怜的意大利移民,忽悠他们购买假的珠宝,一旦受害人付不起帐,便会被投入私设的假监狱里,这些“监狱”乃是她们从腐败的政府官员那里租来的,雇有假“警察”负责看管。上述这支后裔生活在纽约下东区格兰特大街的一栋配有电梯的豪华大楼里;她们的所有婚礼皆由我丈夫的曾祖父(“黄金贝莉”最小的儿子)犹大·萨克斯(Judah Sacks)主持,他生活在曼哈顿区。另一群女性后裔则参与了耶路撒冷米尔神学院(Mir Yeshiva)的筹建工作,该校1814年成立于白俄罗斯,分支遍布世界各地;如今,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塔木德》研究机构,主要钻研一套名为“穆萨”(Mussar)的伦理学体系,凯尔默的拉比们对该理论多有贡献。
留在凯尔默的堂亲们则亡于纳粹之手,1941年7月29日,纳粹将他们赶到神学院的操场上并加以射杀,后来一并葬在当地某农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子嗣有不少活跃于医学、法律、宇宙学与艺术等领域,建树颇丰。他们当然可以说是既聪明又成功的。不过,即便他们在医学上的贡献延长了他人的寿命,生着一头红发、来自凯尔默的家族后裔们却没有多少能长寿的。家谱的记载清楚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犹大·萨克斯1903年在纽约去世,享年58岁。我丈夫的叔叔梅耶在洛杉矶做服装生意,1975年时因急性脑溢血去世,享年58岁。丈夫的母亲是个擅长感伤情歌(torch-song)的歌手,长期受心力衰竭的困扰;她是“黄金贝莉”的曾孙女,1997年在加勒比海旅行时因饮食含盐量过高而离世。我丈夫的堂兄则是米尔神学院在现当代最具影响的领袖人物,2011年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68岁,当时有不少人身着黑衣上街参加了哀悼活动。
我越是细读这本家谱,就越能感到这一家人是多么的不幸。我自己家的亲戚活得要长很多,有不少都活到了将近百岁,那群凯尔默后裔们则大多英年早逝。由于担心丈夫也重蹈覆辙,我催着他去看心脏病医生,第一年暂无大碍。但当他60岁第二次去看医生时,却被查出颈动脉有95%的阻塞,最多还能活几个星期而已。手术和药物救了他一命,并维持其健康至今,但我怀疑这背后有股隐而不显的力量:英年早逝可能是拉比们艰苦生活的必然代价,悲伤、恐惧和痛苦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死死地压在他们身上——而他们的后裔今后也将继续承受这一代价。
俗话说,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和皮囊,他们的好运和厄运也都得照单全收。诸如我们受到“家族诅咒”(family curse)、肩负着过去的重担之类的观点,自人类最初学会思考开始,便是其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时代文明的崩溃留下了各种大灾变的传说;古今中外的种族清洗数不胜数;地震、火山、海啸与洪水时刻困扰着我们;瘟疫与其它流行疾病也没少光顾过——凡此种种,皆被保藏在我们世代相传的种种仪式与故事当中。不过,直到最近这些年,受过科研方法论训练的心理学家们才逐步开始分析历史创伤对后代所造成的影响。直到最近这个世纪,我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些历史创伤,并试图在代际间寻求和解与疗愈之道。
这方面最出名的研究是针对欧洲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的,比起同代人而言,他们罹患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的几率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他们身上。多项研究表明,在非洲-北美奴隶贸易受害者的后裔、广岛与长崎核爆受害者的后裔、卢旺达大屠杀罹难者的后裔以及“911事件”中世贸双塔崩塌之幸存者的后裔们身上,均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玛利亚教授(全名为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她有原住民身份,原名如此——译注)主攻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是研究代际创伤的顶尖专家,也是一名拉科塔(Lakota)部落的成员。她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讨论历史创伤疗愈的论文,目前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经典文献。1890年,拉科塔抵抗运动领袖“坐牛”(Sitting Bull)在南达科他州的立石保留地(Standing Rock Reservation)遭到蓄意杀害,数百名随从在恐惧中四散奔逃,后于附近的伤膝河(Wounded Knee)附近尽数被戮,他们的遗体被草草地扔进合葬墓。“这场屠杀长久地回荡在拉科塔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心灵与脑海中,”她写道。原住民的孩子们很快便被送到寄宿学校去了——校址与家庭及原住民社群的距离有时甚至达到1000多英里——创伤因此而进一步深化。孩子们在学校里会遭到殴打、捆绑,被拴在床柱上。由于环境过于拥挤嘈杂,以一岁以上的儿童计,1936-1941年间的一场肺结核流行竟然夺去了其中逾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玛利亚将美洲原住民所经历的那一类历史创伤定义为“源自大规模群体创伤,终其一生、世代相传并具有累积性的情感与心理伤痛”。这种创伤所造成的代际间反应则包括抑郁、自毁行为、心智麻木、易怒、较高的自杀率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时至今日,拉科塔人的心脏病死亡率也差不多是美国平均水准的两倍左右;自杀率则是平均水准的两倍有余。
按玛利亚的说法,这些历史创伤产生了“难以缓解的悲伤”与“作为巨大的失落体验之一部分的、颇成问题且不时复发的哀痛情绪”。伤膝河大屠杀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坐牛”的后裔们仍难以从伤痛中走出来。其中一人告诉玛利亚及其同事说:
“我认为,失去故土才是最痛苦的……姑妈、叔叔和父亲的音容至今犹在……他们告诉我,有的人被射杀了,我的祖母也在其中……他们忍饥挨饿……你们应该明白,最大的谎言就是人们被迫相信历史书里写的那些东西,还要向那面抹去了整整一代人、对其实施奴役并强迫其改变信仰体系的旗帜肃立敬礼……我心里有个巨大的黑洞……这一切何时才是尽头?”
历史幸存者无法将就过活。他们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深陷其中。
许多探讨历史创伤的文献都沿用了玛利亚提出的概念框架。波特兰州立大学社会工作教授乔伊·德格鲁伊(Joy DeGruy)多年以来致力于发展这一框架,2005年出版其成名作《创伤后奴隶综合症》(Post Traumatic Slave Syndrome),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根据她的解释,为期339年的美国奴隶贸易史,可以说整个就是一部充斥着滥权举动、人口买卖、暴力以及强奸的历史。“这么看的话,说人们走出了创伤是一点也不靠谱的。不如说根本就没人关心他们的伤痛,它从来没得到承认。”并且,由于创伤从未得到认真处理,它们仍在原住民的文化中有意无意地传播着。例如,在黑人社群当中,肤色深的人可能就不受待见。黑人母亲或许还会对自己孩子的成就加以诋毁——按德格鲁伊的说法,这是对昔日场景的无意识再现:以前奴隶们不得不将更加聪明或更有吸引力的小孩卖给出高价的竞标人,因而会刻意让自家小孩显得不那么鹤立鸡群。“这就好比在曲奇饼下了毒,”德格鲁伊解释道,因为维系文化要求“适应并生存”,这一切如今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作为一个黑人而生活的意义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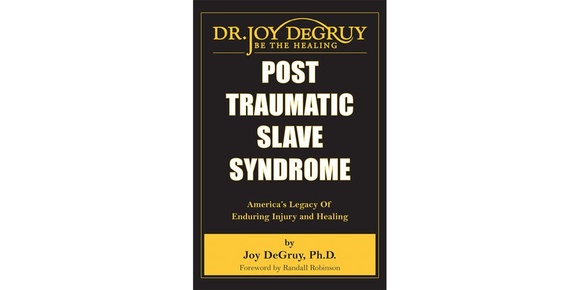
在这个硬心肠的世界里,历史幸存者们必须尽力奋斗来使自己重新振作。每当奴隶制的话题出现时,都会“马上被怼回去”,德格鲁伊说道。“你现在不是已经是自由人了么?我又没生在那个时候,也没蓄过奴……赶紧走出来吧。”但历史幸存者们是没法这么将就过的。他们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深陷此旋涡之中,如今依然难以自拔。
惨重的历史创伤令如下的激进观点得以传世:发生于各地的大洪水、饥荒或大屠杀不仅会改变我们的心智和行为,还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细胞的深层生物学结构。对于那些受到历史性剧变之影响的人而言,后果可能就是由压力引发的精神症状和慢性疾病。按某种说法,这些细胞层次上的变化并非发生在基因编码(genetic code)这一层次,而是居于基因组“之上”——亦即是透过那些控制基因表达(gene expression)的细胞来完成的——它们因而被冠名为“表观遗传性”(epigenetic)。
表观遗传创伤首次被发现,是在1944-1945年因纳粹切断荷兰全国食物供应而导致的大饥荒当中,当时尚在母亲腹中的小孩被查出患有此症。这些“饥饿之冬小孩”(Hongerwinter babies)在子宫里就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与正常人相比,成年后的他们饱受肥胖症和血糖水平异常的困扰,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相当之高。为何如此?某些关键基因中缺乏甲基。如此一来,这些细胞就好比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开关,它们附着在DNA螺旋结构上,干扰着基因转录(gene transcription)。对“饥饿之冬小孩”来说,这种低甲基化(hypomethylation)导致了某类蛋白质的超标,影响了正常的生长与新陈代谢,进而引起一连串的细胞相互作用并诱发了相应的疾病。这些表观遗传效应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但其传递机制仍是相当清楚明了的——来自母亲的压力影响了成长中的婴儿的基因表达,极大地提高了后代的患病率。

这些研究发现无疑只适用于某一代人,但也足以对前沿的进化理论形成某种挑战,后者认为物种变化乃是以千年为单位缓慢发生的,短短几个月乃至于某人的一辈子对此并无多大影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理论主张,自然界将选择最具适应性的有机体,它们能最好地在给定的生态系统中繁殖与生存。当DNA序列发生随机突变时,该过程便开始运作,其序列最适合周边环境的有机体则能够自我复制并存活下来——这引发了导向变迁的基因表达。达尔文式进化历程对地球上生命的塑造速度显然是十分缓慢的,跟亘古不变几乎没什么区别了,但科学家们却发现表观遗传信号几乎每天都能运作,且不只是透过甲基来进行。对某种环境的体验能够改变染色质(chromatin),它正是构成染色体的细胞阵列;而RNA以及组蛋白(histone)也同样会发生改变,前者乃是将基因讯息从DNA传递至蛋白质中的“信使”细胞,后者参与了染色质(它包含着基因)的包装与形构。
雄性后代有极高的肿瘤、肾脏疾病、前列腺疾病及免疫系统疾病发生率
该领域某些最重要的成果出自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压力研究专家布鲁斯·麦凯文(Bruce McEwen)之手,他多年以来致力于探索贫穷、成瘾以及家庭暴力对表观遗传变化的影响。麦凯文与同行合作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此类社会压力增加了肾上腺当中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cortisol)的分泌。这反过来对基因产生影响,使其结构中的树突(dendrites)发生扩张,一旦遇上压力,膨大了的杏仁核(amygdala)便会催生出极强的焦虑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学者们考察了132名穷人家的孩子,发现不时袭来的噪音与暴力刺激提升了他们特定DNA片段的甲基化程度——亦即负责传递5-羟色胺的基因之启动子所处的区域(简写为SLC6A4)——这意味着杏仁核将会产生加强版的“战斗或是逃跑”(fight-or-flight)反应以及更低的5-羟色胺水平,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抑郁症。
表观遗传变化可以在人的一生当中出现,也可能是怀孕的母亲将自己的压力荷尔蒙传入子宫所致。问题是,它们能否在代际间传递?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斯金纳(Michael Skinner)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与同行研究发现,“由环境引致的代际间表观遗传继承(epigenetic transgenerational inheritance)目前在植物、昆虫、鱼类、鸟类、啮齿动物、猪和人当中都有出现。”以啮齿动物为例,这种变化可持续至少10代,在植物当中更能持续数百代。
透过多年来一系列设计出色、甚至于有些令人震惊的实验,斯金纳成功地揭示出表观遗传创伤可以严重到何等程度。为实施此研究,斯金纳将老鼠暴露于一系列的一次性环境毒害(one-time environmental toxins)当中,包括昆虫极为厌恶的避蚊胺(DEET)、生产塑料时必需的双酚A(BPA或bisphenol A)、“青史留名”的虫害克星DDT以及飞机燃油或石油等羟类化合物,在时间点上,研究人员则选择了老鼠胎儿发育的关键期,即性器官在子宫中初步成型的阶段。他发现,从第二代起一直到此后未加暴露的每一世代,雄性后代均有有极高的肿瘤、肾脏疾病、前列腺疾病及免疫系统疾病发生率。如果连续四代都遭毒害的话,那效果看上去就真的是世代相传了:雌性后代患上了卵巢功能衰竭、多囊卵巢症以及性早熟。其后裔中的压倒性多数很容易就会受到刺激,且大多还得了肥胖症。“九成的动物都患上了多种疾病,”斯金纳说道。就算不考虑持续性暴露的情形,每一次毒害也都会以表观基因组的变异这一形式,留下独特的基因指纹(biological fingerprint),与此相伴随的疾病状况也会传递至下一代。

这一现象是否能解释凯尔默的拉比们大多因心血管疾病而英年早逝的情形?根据心脏病学的研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冠心病甚至于心肌肥厚都可以追溯到个体身上的表观遗传效应。验证我们能否将这些发现扩展到代际间的传递,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尽管我们知道,暴露在母亲的压力之中能改变一个婴儿的表观基因组,但使得创伤世代相传的文化与生物学机制具体各占多少比例,还有待人们的探究。
不管我们最后有何发现,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并不是非得来一场大屠杀才能毁掉一家人及其子孙后代,贫困其实就已经足够了。麦凯文及其同行业已雄辩地证明了成长于“高风险家庭”、缺乏情感支持、遭受忽视以及冷漠对待的孩子长大后将会有相当不利的处境。其成长环境越坏,表观遗传效应对海马体(hippocampus)、杏仁核乃至主管认知的关键部分——也就是额叶(frontal lobes)的负面影响也就越严重。麦凯文解释说:以此观之,许多成年人的疾病其实是从早年的贫穷、歧视或虐待发展而来的紊乱现象,只要解除掉童年时期的有害压力,这些病痛当可得到缓和。
无论表观遗传变化只是影响亲历创伤的那一代人还是会如同基因一般世代相传,“我们总归无法令时光倒流并逆转不幸经历所产生的诸多影响,”麦凯文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穿行那些经历,设法使人重新振作起来并改变其人生方向。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表观遗传变化来增强自己的恢复力(resilience)。全新的人生轨道将会在大脑以及身体上引起一些补偿性的变化,使人终生受益。”
此外,我们还能逆转大脑中的表观遗传效应。麦凯文表示,只要加以日常的训练、密集的学习以及抗抑郁治疗,海马体的尺度是可以慢慢增长的。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每天散步一小时可以增加大脑血液流量、改善记忆。心意纯正的减压活动则可减小杏仁核的尺寸及活动频率——鉴于那里是产生恐惧的中心,这样做是百益而无一害的。甚至于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也能增强大脑的可塑性——只要认知疗法能适时跟进重塑即可。
在一项堪称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对恢复力相关数据的综述当中,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学者们发现个体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回应极端的不幸与压力。“尽管某些个体产生了诸如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或重度抑郁症等精神障碍,但别的一些人则能从充满压力的体验中振作起来且没有明显的心理疾病症状,表现出了良好的压力恢复力(stress-resilience),”他们这样写道。学者们还主张,在各项有助于人们与表观遗传伤害周旋进而克服有害压力的因素中,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vity)、幽默感以及积极主动地面对诸多生活困境的心态乃是最为重要的。
美洲原住民从不被允许表现出真正的哀伤,“历史上未曾解决的哀伤”令情形愈发恶化
玛利亚讨论了实行传统哀悼仪式的重要性。对拉科塔人而言,这意味着“Wakiksuyapi”这一概念——亦即在过往历史中维系与灵性世界的联系以及对祖先的认同。玛利亚指出,美洲原住民从不被允许表现出真正的哀伤,“历史上未曾解决的哀伤”令情形愈发恶化。
在这些举措之外,医学界也在研制能够对表观遗传伤害实施精确打击的特效药。其主要目标是个体在其人生中所蒙受的伤害——如果能证明代际间表观遗传继承在人类活动中的确举足轻重的话,治疗范围也可以相应地拓展。
这大概是最好的消息了,因为始于2000年代初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也曾有过借此治疗疾病的构想,但最终失败了。事实上,目前所知的大部分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nts)对患病风险的影响只不过是边际上的,且只能解释家族疾病群集中的很小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学者目前希望,表观基因组能够填补遗传力(heritability)方面的解释空缺。来自麻省哈佛医学院、专攻癌症相关的表观遗传学专家布雷德利·伯恩斯坦(Bradley Bernstein)表示,部分恶性脑胶质瘤(glioblastoma brain tumours)和白血病乃是源自表观遗传变化的,其表现形式为细胞的过度甲基化,而这可以通过扭转甲基化进程的药物来加以治愈。
洛克菲勒大学的癌症表观遗传学家C·大卫·艾利斯(C David Allis)主要研究如何以表观遗传学来治疗癌症——他的疗法基于组蛋白,DNA正是绕着它旋转的,迄今为止已证明对某些以往认为无药可救的病人有效。RNA水平的提高是另一条表观遗传的途径,目前认为与心肌梗死、冠心病和心脏衰竭有相当确切的关联,这些病都可以采用上述疗法,凯尔默的后裔们也许能因此得救。学者们还在探索糖尿病、精神分裂、肥胖症、衰老和炎症的表观遗传学治疗方案。有一系列的可靠证据表明,表观遗传机制能也能够解释我们在现代世界中见到的大多数哮喘病。
除了为业已受到病痛折磨的人们寻求治疗方案,理解这些现象还意味着在表观遗传伤害出现之前就对其实施预防——使我们的年轻人不受贫穷、有害压力、污染、羞辱以及日常性的忽视。这意味着推进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还有利于养成恢复力的社会政策与文化。实行一定的政府规制,建立能够提供充分的健保、可负担的教育、强大的家庭、弹性的工作时间以及足额假期的商业环境,有利于保护好我们的大脑。麦凯文就此谈道:
“健康的行为习惯和人道主义的政策能够‘开启一扇可塑性之窗’,令身体的智慧有施展拳脚的空间。这一窗口的敞开,配合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能够让大脑回路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某个人即便早年生活不利,其人生轨迹也是可以改变的。”
这一切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追踪凯尔默拉比的系谱学家们也让我了解到了自己的起源,父亲长久以来对我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的祖父从来没跟我提过他们是从何种恶劣环境下迁居至此的,甚至我姓名里的“温特劳布(Weintraub)”这个词都有着刻意掩盖某些东西的考量。1979年我才得知了这个秘密,当时我的堂兄弟罗伯特告诉我,他在以色列贝尔谢巴(Be'er Sheva)的街头被一名老者拦住,对方坚称自己1901年前后曾在从埃利斯岛(Ellis Island,距离曼哈顿区十余公里,曾为欧洲至美国移民的重要中继点和检查站,现已改为纪念地,不少移民会到此寻根问祖——译注)开往纽约的船上见过我们的祖父。“你这张脸跟他一模一样,千真万确,”他告诉罗伯特说,“但他却不叫温特劳布。”
我堂兄弟是个讲求实际的化学家,他说出这个令人困惑的故事时就好像在讲笑话。“太荒唐了,”他说。但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姑妈最终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原名似乎是以‘A’开头的,”她猜测道——不过已经记不太清了。近年来,一项针对船只货单和旅客名录的考察表明,纽约的温特劳布家以前在乌克兰的犹太人聚居地什皮科夫(Shpikov)的主干道上经营商店,此地以脏乱差著称,盥洗间设在各家屋外的前院里,哥萨克不时前来扰民并殴打犹太人。那时的家族名字叫艾泽曼(Aizenman)或者相近的变体,有史料表明,艾泽曼家从东边某座主营蕾丝制品的小镇搬来,在离开什皮科夫前也并没在这里住多久。故事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另一个年龄较大的姑妈也告诉我说,蓝眼睛的“温特劳布家”有一旁支是黑眼睛,跟她相似——她认为这体现出该旁支的远东基因。“我母亲嫌我丑。生着一双黑眼睛的我们是贱民(pariah),”她说道。
我母亲那边的家族名字则是尼加莫夫(Nichamoff)——某个姨妈猜想这可能与帝俄海军将领帕费尔·纳希莫夫(Pavel Nakhimov)有关,某些舰只以及一所海军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这名帝俄将领曾有过一个犹太裔的夫人并与她生下了孩子: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我的外公看起来总是特别有“瑞典味儿”,他金发碧眼且有着很高的鼻子。

我们费劲心思扔掉自己人生中的包袱,只是为了给祖先们的包袱腾出空间?
为了在一片狼藉的历史中追寻我自己的代际间创伤,我跟兄弟一起做了基因测试——但没有什么大的发现。我们的基因大约有50%相同,这在家庭DNA树的染色体图谱上显示为一块很大的蓝色。我还在家谱上找到了一些其它的所谓关联,不过,与其说我们分享着历史的创伤,不如说它表现为世界本身的创伤。往前追溯十代人,我已经有了颇为惊人的1022个祖先;追溯十二代的话,数目更变成了4096个。是的,以四代人一个世纪这一正常比例计,我是由300年间的4000多个人构成的——我的祖先堪称是数目庞大、无处不在了。令我相当惊奇的是,我甚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犹太人。我身上也有着非犹太裔东欧人的血统,这符合帝俄海军将领的故事。我姑妈谈到的“黑眼睛”一脉包含了意大利、西亚乃至于东亚的血统。纵观我的直系亲属,也就是我在真实世界中所知晓的那些人——我的母亲活了98岁。姑妈凡妮享年105岁,萝丝享年104岁。较之于那些短命的拉比,我的家族是富有韧性且长寿的。“我们世世代代都会这样的,”我跟自己的兄弟说。就那些我在家谱上找到的人而言,我跟他们所共享的DNA是分散且零碎的。要具体说清我究竟从历史上的哪一特定时间及地点继承了创伤,是不大容易的。我不是红发的凯尔默人后代——我的基因经历了数不清的循环与淘洗,经历了许多个世界。
此外,思索祖先究竟在我的DNA当中打下了何种烙印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即便那不过是一些真相而已。我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那时是1970年代,母亲家里的姐妹们有不少认为:人要成长就必须经历一场精神分析。我的医师在诊所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光彩夺目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犹太哲学家,主要研究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译注)画像,作者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20世纪知名艺术家,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译注)。经过多年的反思自身生活的历程,我从布伯的《我与你》(I and thou)一书中获益良多。透过在脑海里演练自己家庭中的“你性”(thou-ness),我学会了不去投射他们的世界影像。或者说我本身就是这么想的。如今,经历了这一切,我有些讨厌“祖先的痛苦与哀愁将会铭刻在我的细胞中”之类的见解。莫非我费劲心思扔掉自己人生中的包袱,只是为了给祖先们的包袱腾出空间?
我决定不去理会此类担忧。对代际间表观遗传效应的研究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基于啮齿动物的研究发现未必会传递到人的身上。2016年,布朗克斯(Bronx,纽约五个市区之一,位于最北端——译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表观基因组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约翰·格雷里(John Greally)与另外两名学者合作在期刊《PLOS遗传学》(PLOS Genetics)上发表论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总的来看,以个体为基础的研究可能有假阳性、发表偏差和数据质量不佳的风险。目前的数据集仍然偏小,而某些标记(marker)也可能在人们用它来标示某种疾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重复实验以及广泛的检视和评审。
与其哀悼过去,我宁可把更多精力用来关注世界当中的各种进化时刻。说到底,我们都身处这一境况当中:我兄弟的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人在印尼学习,现在有了印尼的妻子。“我的孙子可能会是棕色皮肤了,”我兄弟兴奋地说道。我的堂妹和表妹——包括她们的孩子——也有不少跟犹太教之外的人结婚的。哪怕是凯尔默的拉比们,其后裔也广泛地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有着沃尔贝特(Wolpert)、芬克(Finkel)、古特曼或是萨克斯之类的名字,这等于说他们自己也被播洒到了全宇宙。运动、稀释与再混合乃是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现代世界的基本设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应该向前看,并且担当起我们的未来。假如条件变得十分极端、污染严重、压力巨大或危险无比,以至于我们后代的表观基因组难免面临受损的风险,那又当如何?什么样的事件或状况才算是得上表观遗传意义上的危机时刻?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以人性本身为赌注,又应当做些什么来保持中道?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