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来说,1968年的革命潮刺激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

巴黎,1968年五月,摄于游行学生与防暴警察一整晚的对抗后。摄:Bruno Barbey
1968年,我(指本文作者约翰·格雷,美国作家)也曾走上伦敦街头,参加了反对越战的大型游行示威。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场面庄重,人们保持着头脑冷静。示威者们还在担心警察骑的马匹——谣传有一群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盘算着要在马蹄下放滚珠,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谴责反对这一卑鄙手段。警察也十分克制,许多人好像只希望避免冲突。一队示威者在一个毛派共产主义者的带领下,突破了美国领馆周围的警戒线,冲到了格罗夫纳广场。这之前,在三月的一场游行中,警察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但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之后,一些人被捕,那次斗争流于失败。
游行如期进行,示威者将请愿书交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又继续前进,来到海德公园发表演说,要求政府立即叫停越南战争。然而,战争一直拖延到七年后西贡(现胡志明市)陷落南越溃败才告终。当时的内政大臣、后来成为首相的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夜间视察了格罗夫纳广场,看着人群散去重归平静。卡拉汉对示威者和警察都赞许有加,评价称,这样的游行,要是放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么快就平息下来。
在游行过程中形成的印象和观念一直伴随着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都没有消褪。在英国,1968年运动不过是独特的英国制度历史中的一个瞬间。理查德·维南(Richard Vinen)的新书《漫长的1968:激进的抗议者与他们的敌人》(The Long '68: Radical Protest and its Enemies)研究深入、描述详尽、涉猎甚广,书中一张配图完美展现了当时的气氛。《漫长的1968》展现了年轻的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僵硬笨拙地与肯特公爵夫人跳舞的一幕,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在当时是利兹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维南说:“英国保持着旧制度,世袭君主,国教教会,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上院(其成员大多数都有着贵族血统)……现在,没有比那个地方更能体现旧制度特点的了。”
他在书中继续写道:
1967年,最初作为英国君主咨询机构的枢密院商议在牛津大学进行一项改革。学校部分职位的人选由君主直接选择。实际上就是在适当“征询意见”之后,交由首相的任命秘书来执行。拉布·巴特勒(RA Butler)因此就任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他原来是保守党的内政大臣,而伞兵出身的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将军也拿到了委任状。
巴特勒和哈克特都对学生的要求给予了支持……顶着毛毡汉堡帽,系着军装领带,哈克特领导了1974年那场著名的学生运动。
在离开圣保罗公学后,历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在巴黎旅居了10年,他也有着和维南相似的看法:
我在1961年来到牛津,当时的我穿着法国左岸能找到的最简洁雅致的衣服,抽着茨冈香烟。在法国的日子里,我对英国的看法更加巩固了,和许多在六十年代早期结识的朋友一样,我觉得英国依然实行着由世袭君主贵族统治的旧制度,仍然抓着爱德华七世时代那种风格的古老过时的服饰不放。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英国当时依然是一个“爱德华七世”式的追求浪漫和气派的国家。在英国,权力被分散到不同的自治机构,通过不成文的甚至是不可明说的默契来运行。但这些机构处在一个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当时的抗议活动就反映了这一点。六十年代晚期开始,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就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不过在工人阶级中依然不多见。维南介绍说,根据安保部门的估计,1980年,在英国的25万矿工中,只有15名托洛茨基主义的激进派、9个社会主义工人党人,以及5名国际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英国最重要的商会中的数量,甚至比北伦敦大学(North London Polytechnic)还少。总体上来说,除了极少数人来自其他阶级,这场革命的主要拥趸还是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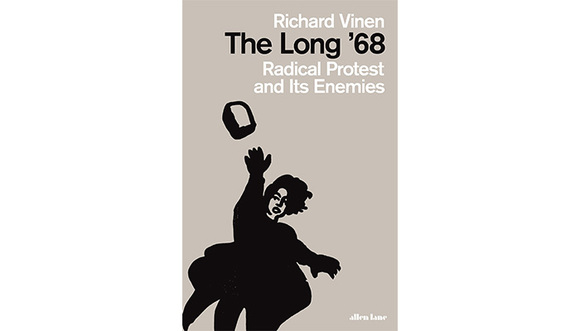
抗议活动中提到的两性关系在社会上也有所体现。六十年代早期,牛津、剑桥大学只有593名女学生,而男学生有4002人。同样地,在一本出版于1969年、关于学生力量的刊物中,刊载的12篇论文中11篇出自男性作者之手。另一方面,虽然所有人都把“第三世界”挂在嘴边,但种族政治依然处于边缘地位。抗议活动矛头指向白人少数群体领导的南非和罗德西亚(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政府,以及反移民的保守党人,典型代表就是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现在所坚持的“种族身份高于一切”的理念在六七十年代还找不到一点儿迹象。
维南在书中把“漫长的六八”定义为“一系列与1968年相关,且在这一年达到高潮的社会运动,但并不局限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运动”,维南写道:
它有几个重要因素: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代际反叛、对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国政治力量的对抗,以及围绕摇滚乐和生活方式展开的文化反叛。有时候这些反抗会交织在一起,但这点并不绝对。六八抗议者常常规避或颠覆既有的框架……有时候,他们甚至颠覆了自己原来支持的东西。七十年代早期的社会运动——女性解放运动、争取同性恋权益以及一些致力于武装斗争的组织团体——都是对1968年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的反叛,同时也可以说是延续。
六八运动是以上所有东西的集合,但也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当然了,这并不是一场代际的对抗。一方面,抗议者中有老有少。1964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事件,伯克利的一名学生示威者大喊:“不要相信任何一个30岁以上的人。”但当初1962年《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的撰写者、播下校园抗议的种子的汤姆·海登(Tom Hayden),到1968年时已经29岁了。海登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创始人之一,在SDS的青年领导者中,生于二战之后的仍然是少数。其中,巴黎反越战的学生领导者之一、美国人玛利亚·乔拉斯(Maria Jolas)来自肯塔基州一个富足的家庭。曾有一段时间,他占领了科龙贝双教堂村的一座宅子,这里后来成为了戴高乐的庇佑所和安葬园。乔拉斯生于1893年。在英国,声援反越战运动的抗议者之一是多萝西娅·黑德夫人(Lady Dorothea Head),多萝西娅出生于1907年,是沙夫茨伯里公爵之女,嫁给了一个托利党人,到1968年时年纪也不小了。
戴高乐在1966年提出了自己对“青年”的看法,总结了单纯从年纪入手分析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把青年人隔绝出来,单独看作一个群体,”他解释道,“今天的年轻人也会老去。”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评价1968年的学生团体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年轻不是永久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慢慢老去。”另外,学生团体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整齐划一的左翼分子。1968年入学埃塞克斯大学的有490名学生,其中88%的人,只有1%把自己看作“左翼工党成员”,1%认为自己是“工党中间派”,2%认为自己是“鲍威尔主义者”(Powellite)。另外,26%给自己的定位是“温和左翼无党派人士”,5%是“极端左翼无党派人士”,还有4%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1968革命表现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是与传统左翼的分裂,在美国和法国,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抗议者包含了太多冷战时期的因素,而且太依赖商会,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学生激进主义与青年文化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联系,但往往被夸张放大了。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法国新浪潮导演,当时推崇毛泽东共产主义)在1968年拍下了滚石乐队录《Sympathy for the Devil》的过程,但这并不能说明滚石乐队就认同戈达尔的观点。维南解释说,滚石乐队转移到法国,并不是为了加入法国无产者左翼组织,而只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税务局。五十年代的乡村音乐反而与政治激进主义联系更真切。

但这并不是说1968抗议者们没有受到流行文化的启发,其中包括那些公开转向暴力的人。电影对暴力的描述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位意大利的极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Red Brigades)的成员承认,他最初是被电影领上暴力政治之路的:“特别是那些美国电影,人们不会真的死去。”在伦敦,由离校生组成的左翼团体“愤怒旅”有时会在自己发布的声明下署名“虎豹小霸王”。恐怖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又名巴德-梅茵霍芙组织)的著名创始人之一安德列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最喜欢的电影就是意大利导演塞吉欧·李昂尼(Sergio's Leone)执导的《西部往事》。
许多在六十年代晚期发生转变的激进分子都受到了犯罪电影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开始写小说。共产主义活动家、侦探小说家多米尼克·马诺蒂(Dominique Manotti)认为,1968年5月对她这样的作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畅销小说《龙纹身的女孩》的作者、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在1968年参与抗议时才14岁,6年后他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
***
很小的一部分抗议者转向了暴力。维南在书中分析了六八革命分子的四个人群——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联邦德国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历史给德国留下了许多纳粹时代的恐怖遗产,同时极左分子也在转向极右。维南写道,“水晶之夜”犹太教堂爆炸案当天,有一个激进左翼团体派发了一本名为《和平与汽油弹》(Shalom and Napalm)的小册子,其他人则认为,犹太人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他们惨遭纳粹血洗的罪魁祸首之一。前德国律师霍尔斯特·马勒(Horst Mahler)后来加入了新纳粹国家民主党,他是红军派创始人之一,逃到匈牙利后,因为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被遣返德国,多次入狱。
在美国,暴力活动主要是由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主导的,而且被黑人民族主义组织黑豹党人用作防范目的。在尼克松任期时,美军从越南撤出,美国的暴力行动开始偃旗息鼓。
在法国,激进的革命活动能让政客迅速挣到好名声。在巴德和梅茵霍芙逃亡期间,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知道自己的政治关系能保护他们免受警方突袭,于是让两人住在自己巴黎的公寓里。到了1981年,德布雷在爱丽舍宫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密特朗总统的顾问。
七十年代早期,在愤怒旅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以后,除北爱尔兰的军事斗争和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对英格兰的恐怖袭击外,英国的激进政治已经不再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了。
***
六八运动的抗议者们对七八十年代的劳资纠纷并不怎么上心。1968年的革命潮影响持久,一直持续到90年代。过去的抗议者——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德国前外交部长)、比尔·克林顿和杰克·斯特劳(英国前外交大臣)等人——已经坐上政治高位,公开标榜自己为改革派。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抗议者对自己反对的经济模式作出了系统批评。能算得上批评的,就只有鲁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了,两本书都在1967年出版。奇怪的是,维南对两本书只字不提,尽管它们当时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倍受欢迎。

这两位思想家指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因反对资本主义而兴起,最终的成果却被资本主义所汲取。讽刺的是,这点在革命者自己的短命“情境主义运动”中最为突出,这场运动后来给世界的流行产业和广告业都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六八社会运动帮助资本主义克服了其文化矛盾。“资本主义要想生存,在创造生产者的同时还要有对等数量的消费者。”维南分析说。六十年代晚期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为资本主义培养了许多消费者。维南警告说:“人们过分重视‘六八资本主义’了。”六七十年代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中间,极少部分会积极地拥抱资本主义,但对个性的狂热崇拜和对集体主义经济理论的赞美在许多六八抗议者身上并存,并且对为撒切尔-里根主义铺平了道路。”
维南指出,“六八”这个词在1968年使用并不多。许多革命分子认为,这一年不过是一系列巨大社会震荡的序曲。从一定程度上看,事实确实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社会发生了当时革命者无法想象的激变。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英国,学生和教师的反抗对象——传统的自治大学已经被纳入市场规则和政府指令的麾下。不管在哪里,尽管中产阶级的收入仍在增加,但他们变得越来越缺乏安全保障。
变革确实发生了,但并不如六八抗议者所愿。许多人继续奋斗终生,努力维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正这是他们当年所抗议的。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