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正在热映的黑人超级英雄电影《黑豹》。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受到热议的一到两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呈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交锋。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正在热映的黑人超级英雄电影《黑豹》。
《黑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瓦坎达”(Wakanda)的虚构非洲国家,瓦坎达长期与世隔绝,却拥有丰富的“振金”资源,依靠着“振金”,他们发展出了先进的科技。瓦坎达的君主被称为“黑豹”,影片开头,老黑豹特查卡到奥克兰调查振金失窃案,并发现他的弟弟恩乔布正是协助黑市军火商盗窃振金的内鬼,后来,特查卡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时被炸死(这一幕在《美国队长3》中有展现),他的儿子特查拉继任王位,影片讲述的,就是年轻的国王特查拉如何应对内忧外患,拯救瓦坎达于危难之中的故事。
特查拉的最大对手,就是恩乔布的儿子埃里克,作为一个被放逐的瓦坎达人,埃里克的青年时代在奥克兰度过,后来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的训练,在中东地区从事间谍和颠覆政权的活动。经历过贫困、帮派暴力和战争残酷的他,形成了一套与其在乌托邦瓦坎达长大的堂兄特查拉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果将这两种政治愿景投射到现实中,前者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国际主义,后者则在温和的“孤立主义”和以不失去民族国家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前提的、和平的全球主义之间徘徊。这种虚构与现实中的对照引人深思,电影中的正面人物与现实中在西方/白人中心主义视角下作为他者的民族和文化一样,选择了一种在现有世界秩序下和平发展、释放影响力的道路,而电影中的反派则与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情一样,悲壮地陨落并因暴力被污名化。
提到“黑豹”,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黑豹党”。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简称BPP)是成立于1966年10月、解散于1982年的美国左翼政治组织,虽然它并没有直接出现在电影《黑豹》中,但却与《黑豹》的故事有很深的渊源。1966年7月,漫威公司在第52期《神奇四侠》中首次推出黑人超级英雄“黑豹”,这也是美国漫画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超级英雄,许多人因此猜测,黑豹党的命名可能受到了这部漫画的启发。
微信公众号“高冷门诊部”的评论却认为,“黑豹党”名字的由来可能与漫威并无直接关系,虽然《黑豹》漫画的问世要比“黑豹党”成立早两三个月,但“黑豹党”所使用的黑豹logo早在1965年就存在了,它最早是黑人运动组织LCFO的Logo,后来“黑豹党”的创始人鲍勃·希尔和休伊·牛顿向LCFO要到了授权,并将他们的组织命名为“黑豹党”。事实上,漫威官方一直努力与“黑豹党”划清界限,漫威主脑斯坦·李曾公开表示,黑豹的形象并没有受到“黑豹党”或黑人运动的影响,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本通俗小说,其中的主人公经常带着黑豹一起去探险。《黑豹》漫画的另一位创作者杰克·科尔比也透露,这个角色最初的名字其实叫做“煤虎”(Coal Tiger)。为了撇清关系,漫威还曾在1972年将“黑豹”的名字从“Black Panther”改成了“Black Leopard”,但不久后又改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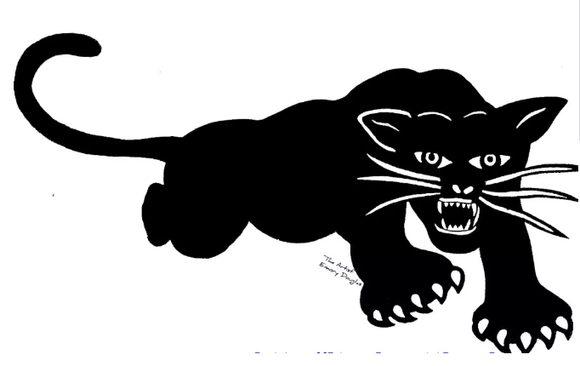
电影《黑豹》将一部分剧情设定在1992年的奥克兰,也并非偶然。奥克兰不仅是黑豹党成立的地方,也是影片导演瑞恩·库格勒的故乡。在奥克兰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次种族冲突事件,其中2009年元旦白人警察在地铁站台上射杀黑人青年奥斯卡·格兰特的事件,就曾被库格勒拍成电影《弗鲁特韦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这也是库格勒的长片处女作。
1992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澎湃新闻·有戏”的评论指出,1992年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洛杉矶骚乱”,这是由一起黑人反抗白人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引发的、波及全美的种族冲突,而“黑豹党”建立之初的主要实践,就是通过武装平民巡逻队(citizen’s patrols)来监督奥克兰警察,从而保卫黑人社区,反抗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因此,与马丁·路德·金主张的非暴力平权运动不同,“黑豹党”一直以暴力组织的面目示人,但同时,“黑豹党”也并没有像另一位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及其追随者那样,主张激进的“反向种族隔离”。
“澎湃新闻·有戏”的作者哈搭巴认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路线上的“暧昧性”,“黑豹党”很快分裂为两派,一派强调社区服务,在黑人社区兴办教育;另一派则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白人殖民主义运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埃尔德里奇·克莱沃,他认为“黑豹党”就是要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联合并推动世界各地的独立解放运动。电影《黑豹》中的反派埃里克·基尔蒙格就代表了克莱沃的主张,他是被放逐在外的瓦坎达人,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的训练,在中东地区从事间谍、颠覆政权的活动。他在推翻了时任“黑豹”特查拉的统治、成为新一代的瓦坎达国王之后,下的第一道旨意便是倾举国之力,支援世界各地的黑人反抗运动。
“黑豹党”与红色中国的渊源,恐怕就更不为人所知,公众号“高冷门诊部”在评论中梳理了这段历史。文章指出,“黑豹党”的创始人休伊·牛顿14岁时就曾因非法持枪被捕,是一个有反社会倾向的暴力青年,但他喜欢思考哲学与政治问题,阅读了大量左翼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切·格瓦拉等,其中给牛顿最大启发的,是美国黑人运动先驱罗伯特·威廉的《带枪的黑人》。
有趣的是,在威廉流亡古巴期间,曾多次给中国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写信,讲述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以及黑人民权运动举步维艰的处境。毛泽东相当重视,并于1963年8月8日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文中指出:“美国黑人斗阵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同年,《带枪的黑人》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两年后,威廉举家迁居北京。1966年国庆节,威廉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亲自赠予他一本《毛主席语录》,并签名留念。

在大洋彼岸,正处于保释期的牛顿在遭遇警察盘问时与警察发生交火,打死了一名警察,自己也身中一枪。在审讯过程中,牛顿坚称是警察先开的枪,同时“黑豹党”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释放牛顿。这次,“黑豹党”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华人,标语上写着“Chairman Mao says:Free Huey”(毛主席说:释放休伊·牛顿)。

出狱后不久,牛顿便收到了中国政府的访问邀请。1971年9月,牛顿抵达北京,开始为期十天的中国之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到机场,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中国群众一边挥舞着红宝书,一边齐声喊着:“支持黑豹党,打倒美帝国主义!”虽然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牛顿还是对这次中国之行盛赞不已,他称中国为“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一片自由而解放的大地”。
回到美国后的十年间,牛顿面对的是党内的路线纷争,昔日战友的反目,多次被捕入狱以及对他挪用资金的指控。直到1982年,牛顿彻底解散了黑豹党。七年后,他在一次毒品交易中被击毙,横尸奥克兰街头,这一年,这位曾经的革命偶像只有47岁。
理解《黑豹》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非洲未来主义”。“澎湃新闻·有戏”的评论指出,非裔美国学者卡维尔·华莱士在今年2月给《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黑豹》影评中,专门提到了这个词,“非洲未来主义”是一种融合了文化美学、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的综合概念,它主要探讨了非洲/美国非裔文化与技术之间日益扩大的交集。漫画《黑豹》对这一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非裔美国人看来,美国主流科幻文学中,黑人长期缺位,似乎在有关未来的想象里,只有以白人为代表的地球居民以及形形色色的外星生物,这种叙事本身就是白人/西方中心主义的。《黑豹》无疑是其中的例外,它讲的不是非洲殖民史,不是黑奴解放史,也不是推翻种族隔离的历史,从一开始,它就建构了一个“非白人”的语境。
然而,这种非洲部落文化与未来科技的融合,却很容易滑向两种文化窠臼。一个是所谓的“Blaxploitation”,它是“black”(黑人)与“exploitation”(剥削、利用)两个字的结合,它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指的是以黑人主角、黑人演员为卖点,从而招徕黑人观众的电影,而在这样的电影中,对黑人的呈现却往往是脱离现实、异常神勇的。其次是“negrophilia”,这个概念产生于1920年代的欧洲,指的是白人对于作为他者的、充满异域性的黑人文化(或非洲文化)的一种痴迷。
回到电影本身,瓦坎达作为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后现代国家,其自然风貌和政治传统依然是前现代的——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毫无工业文明的侵蚀痕迹,国王靠各部落推举产生,但事实上被黑豹家族垄断。瓦坎达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全靠天上掉下来的一颗富含振金的陨石,这使得它与现实中靠着石油资源发家的海湾国家别无二致。这种东方神秘主义的设定,本身就是站在西方(白人)创作者的角度对于非洲文明的他者化呈现,看似是对于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异质的,没有受到其“污染”的文明的赞美,但这种赞美背后,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仍然难以被打破。
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对《黑豹》的评论中,也提到类似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等待一部像《黑豹》那样的电影,但《黑豹》并不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
首先,齐泽克指出,这部电影受到了政治光谱上各方人士的激烈欢迎:黑人解放党从中看到了好莱坞对黑人权力的第一次大声宣扬;自由派同情《黑豹》主张的、通过教育和扶助而非暴力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另类右派的一些代表,也在电影中“瓦坎达万岁”的呼唤中看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另一个版本。齐泽克认为,当政治立场不同的各方人士都在同一个产品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产品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一个包容对立元素的、空的载体。
在齐泽克看来,电影对于瓦坎达的设定——一个与世隔绝、却因为振金陨石而发展出了先机科技的非洲国家——本身就很成问题:近代史早就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被赐予某种珍稀的自然资源,都毋宁说是一种乔装的诅咒,因为它们因此将受到以攫取资源为目的的残酷剥削。

除此之外,电影中的两个“黑豹”——国王特查拉和大反派埃里克,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愿景。埃里克的青年时代在奥克兰度过,后来成为了一名美军特种兵,他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贫穷、帮派暴力和战争的残酷;相反,特查拉是在与世隔绝、金碧辉煌的瓦坎达皇宫长大的。埃里克提倡的是一种战斗性的全球范围内的团结,他认为瓦坎达应该让自己的财富、知识和权力为全世界受压迫者所用,这样才能推翻现有的世界秩序。而特查拉则从传统的“瓦坎达优先”的孤立主义,逐渐走向了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全球主义,他主张在现存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框架内行动,推动教育并提供技术援助,同时保持瓦坎达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路线上的徘徊,使得特查拉与传统的超级英雄不同,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了怀疑,而他的杀人狂魔对手,则永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特查拉一方面对“好的”全球化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到了全球化压迫者的化身——CIA特工罗斯的支持,这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张力:非洲的美学与全球资本主义无缝衔接,传统与超现代性融合到了一起。被瓦坎达国会大厦的美丽景观遮蔽掉的,是马尔科姆·X将X作为姓氏时所追随的那种洞见:奴隶贩卖残忍地剥夺了奴隶家庭、族群与文化的根,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发明自己,去自由地形成一种比白人号称的普世性更为普世的新认同。马尔科姆·X给我们上过的珍贵一课被《黑豹》遗忘了,那就是为了获得真正的普世性,主人公必须先失去他的根——这是埃里克有过的经验,而特查拉并没有过。

齐泽克认为,电影《黑豹》恰恰证明了詹明信的论断,即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是极其困难的。但同时,这部电影又提供了许多迹象,让我们相信,创作者对于杀人魔头埃里克的政治愿景是开放的,例如在埃里克死去的一幕:他宁愿自由地死去,也不愿在瓦坎达虚假的富足里苟活,随后电影呈现了一个异常温暖的场景,垂死的埃里克坐在山上的悬崖边,欣赏着瓦坎达美丽的日落,而刚刚打败他的特查拉,则沉默地坐在他身旁。这里没有仇恨,只有两个政见不同的人,他们在战斗结束后,享受他们最后的时刻。这一幕,在以残酷地毁灭敌人为高潮的标准动作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