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收入、幸福感、健康状况等指标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在《反教育案例》中得出结论:教育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本文作者Sarah Carr认为,卡普兰以创造性的数据分析作为掩盖,所提供的是危险且极端的意识形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民读大学”的口号完全主导了学校的改革运动:全美教育界领袖承诺会帮助更多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完成四年制学业;美国各地的学校里,大厅和走廊上贴着大学旗帜,中学生被组织去大学参观,甚至还有为小学生写的“我们要学习知识上大学”之类的歌谣。
教育工作者往往会被有关大学学位经济回报率的研究结果打动:根据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的一份报告,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比仅有高中文凭的人收入高出84%。这些数据,确实极具说服力地证明增加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关键——如果不是关键——那也是在美国打破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因素。
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这些都是“胡言乱语”。在《反教育案例》(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中,他写道:“政府应该停止将税收投入到任何形式的教育机构当中。”所有的学校——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完全由学费和私人慈善机构提供资金。联邦政府用来帮助数百万低收入家庭学生读大学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应该被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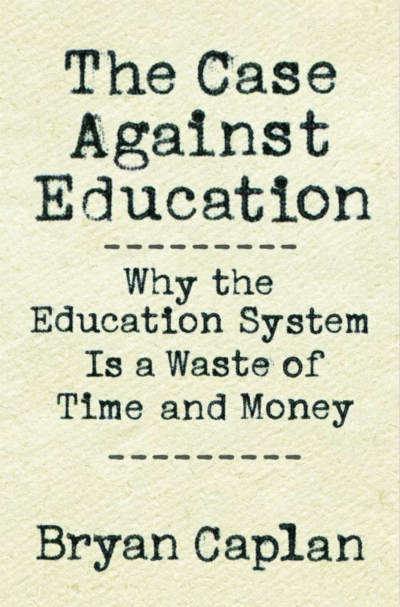
卡普兰也是《生儿育女的自私理由》(Selfish Reasons to Have More Kids)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自然本性比培养方法更重要——这意味着父母不需要如此努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模范学生和优秀公民。
卡普兰在《反教育案例》中大胆而挑衅的结论基于大量统计数据,但书中呈现的观点可能令人生厌。他的论点来源于这样的想法:教育的主要价值,特别是更高的学位,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思想家和工作者,而是来自所谓的“教育符号化”(educational signaling)——教育和学历的目的在于增强先天就存在的特性,例如毅力、智慧和遵守社会规则。“传统教育帮助学生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提高他们的地位。”他写道。
基于整体的评判标准——收入、职业、满意程度、幸福感和健康状况等一系列指标——卡普兰给出了他自己关于评估教育重要性的结论,而且他几乎总是能够推导出:教育远远没有传统理念和其他研究让我们相信的那么重要。
例如,在计算关于教育对健康状况的好处时,他列举了一系列因素证明其影响也许不是通常以为的那么大。他写道:正如许多研究文献中提到的那样,接受教育的年份更长,也许的确与更长的预期寿命相关。但可能这部分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虚弱的身体状况阻碍了受教育的进程,而不是接受教育的过程促进了人的健康。最后,他以一种微妙的自信得出结论:我最好的猜测是,接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真正的健康益处,在4分为满分的体系中大概评分在0-0.2之间。”
卡普兰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比对学术教育的要乐观,认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高中毕业率,还能增加收入并减少失业。但即便如此,改进或者增加技术培训也不应该花费纳税人的钱。他认为:“政府应该摆脱旧思路,重新估算劳动力市场能提供的所有的机会。”这其中包括恢复童工。
对于那些对卡普兰似是而非的推理不屑一顾、并且不同意他的大部分看法的人们来说,他关于职业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大学的价值所在以及教育和就业供求关系不匹配的问题,倒是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此外,关于教育的对话往往以争辩控制权为主:谁应该管理学校和控制资金。即便是关于通用核心课程标准的争论,也没有集中讨论应该被教授的内容,而是关于察觉(或“误察觉”)联邦政府侵犯了各州或地区对学校的司法权:首要问题是谁具有控制权。
卡普兰回避了这些关于谁应该管理学校的争论,对私立学校使用公共资金不予考虑(也就是政策优惠),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于一个破碎的系统,这样的调整依然不够。相反,他将审视的重点放在了学生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上,以及他自己估计的、这一切能给学生和社会带来多大的价值。卡普兰的调查所引发的好奇心,通过不同方式,可以推动真正有建设性的讨论——并且这种可能性不小。

除了以数据为幌子提供意见外,卡普兰的观点存在两大谬误和危机,都与平等有关。
首先,他的分析中将教育和教师视为庞大的整体——也就是说,相当普遍地浪费时间和金钱。他只在涉及学科领域时才会做出明确区分,例如将人文学科看作是“米老鼠”专业。
通过这个宏观的大镜头,他忽视了各州、地区、机构、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质量之间惊人的差距。比方说,如果在一小群水平参差不齐的高中之间比较,那我们可能会对“指导”作用和美国的国家教育体系产生十分不同的观点。
这不是一个宣称“所有事项都被考虑过之后,我赞成学校和州政府彻底分离”的人所应该完成的使命。他的任务也不是要彻底考量自己这个不温和的提案对国家最贫穷的公民的影响——如果公共财政的支持全部取消,这群人永远也负担不起接受教育的费用。卡普兰在接近300页的作品中,只用了短短两页蜻蜓点水般提到了这些,他称之为“这是对我们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的承诺”。
他总结道,为所有人提供义务教育就像是给每个人买结婚钻戒一样——这种财政补贴使某样事物变得普遍从而降低了它的价值。“为了看到财政补贴对社会公平的不利影响,你必须仔细研究穷人因为学术通货膨胀而失去的机会。当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读完高中时,辍学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被污名化。”
正如《生儿育女的自私理由》一书中的表现一样,他的观点似乎建立在生物性决定论的危险信念之上,这种信念与为制度化的阶级歧视辩护接轨。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我更担心他的想法通过进入主流社会,可能会微妙地逐步将辩论焦点引向错误方向),他的理念会将一个公认的、不平等的社会转化为农奴制社会——低收入公民被打发去从事基本上文盲也能胜任的最低工资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工作。
《反教育案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但除此之外,他以创造性的数据分析作为掩盖,所提供的是危险并且极端的意识形态。
本文作者Sarah Car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报道研究员,也是《教师计划》的编辑,以及《希望对抗希望》的作者。
(翻译:陈宛琦)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