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历史上,里根和撒切尔的减税看似是一整套设计好的政策,其实反而是“见步行步”的结果,而左翼力量居然在其中阴差阳错地扮演了推动作用。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特朗普政府的新税改法案。这一法案包含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引起美国内外的轩然大波。在历史上,减税是罗纳德·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支持者认为减税释放了经济活力,促使西方国家从1970年代的“滞胀”中解脱出来,而反对者则认为里根和撒切尔实际上是将国有经济私有化、撤销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红利归于减税,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招数。在今天减税一词成为热点之时,我们不妨回顾一番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减税政策,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莫妮卡·伯勒萨德写过一本专著——《自由市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在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她抛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之所以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不是因为左翼的力量太弱没能制衡撒切尔和里根的疯狂反动,反而是因为左翼的力量太“强”了。
这番结论难免简单粗暴而且充满误导,更像是一个吸引读者读下去的引子。不过,憋着股劲儿认真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伯勒萨德的这一番论述,其实颇有一番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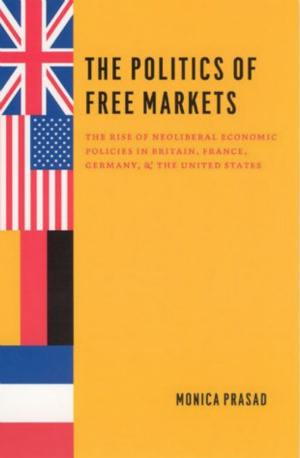
伯勒萨德的这个结论来源于她对四个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德、法)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政治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通过横向比较,常常能够让人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线索和问题,伯勒萨德的比较方法也不例外。
伯勒萨德发现,四个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程度甚为不同。英国和美国经历了撒切尔和里根的政治经济政策,国有经济的比例下降最大,国家监管和社会福利的撤退最为严重;相反,法国虽然在这些年经历了私营经济的大举扩张,社会福利却反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至于德国,除了减税之外,新自由主义居然在各个领域都遭到了挫败。
面对这些不同,很多人会解释说,英美有着深厚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传统,受到这种熏陶,在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快速拥抱追求自由市场,排除国家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奇怪。
但是,伯勒萨德提醒我们,如果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英国和美国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节制其实非常惊人。比如,英美都对企业经营征收了不菲的税额,七十年代时,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远比今天严格;在那时的英国,工会势力如日中天,以至于右倾的保守党都要把自己的政策往中左协调,英国发展出的“福利国家”更是成为了一套模范社会制度。而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却比英美要“右倾”得多,两国都更为追求工业化和复苏,并没有特别注意节制资本,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
于是,通过比较,伯勒萨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工会传统如此深厚的英国,会一下子就热烈地拥抱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为什么强调监管和征税的美国会通过里根的世纪大减税?而为什么政治经济上保守的德法反而较少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冲击呢?
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往往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归纳为四类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推动;三是以弗里德曼和朝圣山学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卖力推销;四是英美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独特文化。
伯勒萨德指出,这四种归因虽然有其道理,但若是任意采用,都有简单粗暴之嫌。在《自由市场的政治》这本书中,她提出,我们需要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机制的角度去理解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横行。尤为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不是一个由清晰明确一致的单一理论指导实践的产物。它恰恰是极其灵活,才能够符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条件,从而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的。
提到新自由主义的勃兴,大家自然不会忘记里根和撒切尔提出的大规模减税——这意味着政府从再分配领域逐渐退出,放弃主张监管市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然而伯勒萨德用数据告诉我们,尽管减税政策看起来轰轰烈烈,英美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实行之后的实际财政收入却并未有大规模的减少。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减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作者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在于税收的结构。不同种类的税收在不同国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不同,比如在美国和英国,个人所得税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收入来源,同时征收较多的还有个人投资税等税种。相比之下,两国对营业税这样的累退税的征收,就没有那么重要。
与之相反,伯勒萨德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税收结构中,占据大头的是累退税,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不少。她认为,正是这种区别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后果,甚至导致了英美新自由主义能够非常强烈地调动选举政治中的民意为其服务。
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结果,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是高度“可见”的。与此相比,营业税和其他累退税属于“不可见”的间接征税,政客们很难将之作为公共话题进行操控。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就算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提高营业税,看起来仍然是“减税”;反之,只要增加个税,就算大幅度减小营业税,也会被当做是政府贪得无厌的象征。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把这种手段玩到了极致。比如当后者面对减税带来的赤字压力时,就大幅度提高不可见的营业税税率,帮助政府既推行了承诺的“减税”,又不至于入不敷出。
伯勒萨德认为,在英美的政治传统中,个人所得税带有明显的“公平”属性,即通过累进税率征富济贫,属于一种“为了社会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而德法两国聚焦于战后的经济复苏发展,更加考虑“国家整体”的概念,从而个税没有带上斗争的烙印。
伯勒萨德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减税政策同时进入里根的政治议题的,还有恢复金本位制的倡议。相比减税,金本位制更容易在政治上推行。然而减税成为了里根的重大政绩,金本位制却没有恢复。伯勒萨德指出,这正说明了“可见度”对操弄政治经济话题的重要性。金本位制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难以调动民意进行拥护和支持。与此相比,税收问题只需要强调“大政府养懒汉”,并质疑政府再分配的效率,就能迅速调动中产阶级摇摆选民的支持。
于是,在税收问题上,作者看到,作为社会公平战场的英美个人所得税吸引了全部的政治目光,当中产阶级不满于国家的再分配时,中产阶级纳税人就变成了政府可以调用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减税为第一次动员,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很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都把矛头指向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然而在书中,伯勒萨德反对把问题归因为这群经济学家的“理论”。她指出,与其直接认为他们是幕后的推手,我们不如询问,他们是如何从大群经济学家中脱颖而出的?而他们的理论,真的被政府全盘接受照做了吗?
首先,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经济理论,并不是因为保守党的政客们真的相信他的鼓吹,而是因为,要抗衡工党,保守党需要一套不一样的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传统的解决方案是调整工资,可这就要面对强大的工会势力,事情会变得非常棘手。所以,看上去能够绕过工会的货币主义就博得了青睐。
伯勒萨德发现,尽管政府号称采用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但却和弗里德曼的主张南辕北辙。在后者的理论中,政府需要做的,是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抑制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政府赤字是很正常的,毋须刻意控制。而撒切尔政府更为关注的,却在于如何控制财政赤字。
结果,撒切尔政府之所以采取货币主义,根本不像后来所鼓吹的那样,是因为预先确定了长期计划,而是因为这套理论看起来符合保守党想要的紧缩经济政策。其结果是,货币政策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引入经济管理,而政府根本只想控制预算。与此同时的减税又增加了赤字,结果政府在明面上实行紧缩和减税,背地里却提高营业税并出售国有企业来弥补。伯勒萨德讽刺地说,这套“货币主义”一经施行,好像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没有什么区别。
相比被大肆吹捧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撒切尔真正的成功来源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然而作者指出,这两项政策一开始也没有被严肃考虑。撒切尔政府固然在第一任期就开启了保守党一直垂涎的私有化进程,但都是小心翼翼,不敢逾越,因为民意此时既不愿意进一步国有化,也不愿意退回私有化。至于廉租房出售,更是首相所反对的,因为她认为这会让廉租房的租户轻松买到房产,给他们带来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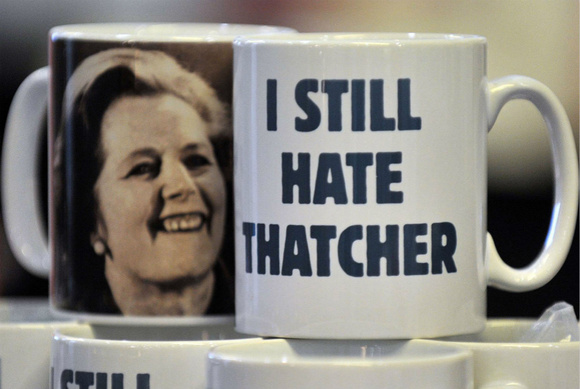
但是随着政府对弥补赤字的需要,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都变成了重头戏,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好处。伯勒萨德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帮助保守党完成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把工党的选民转化为保守党选民。福利国家中,大量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住在廉租房里,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撒切尔经济政策的推行,国有企业被折成股票出售,廉租房被卖给了租户。于是,一大批原先依赖国有体制的普通人,一下子变成了掌握公司股票和拥有房产的小中产。结果是,这些选民本来应该抵制的两项改革,反而成为了撒切尔最得意的政绩——当然,它们完全是“见步行步”的试探结果。
在考察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时,作者注意到,一些非常进步的社会运动,反而成为了右翼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这是新自由主义历史中极其吊诡的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的反监管运动和英国的工会政治。
在美国,里根的减税政策伴随着大规模的反监管。学者们往往认为反监管背后是大企业的推动。但是伯勒萨德发现,反监管的声音早在里根上任前就已经喊遍美国了。继而她发现,“反监管”这个含糊的口号,居然包含着从左翼群众运动到右翼大财团游说转变的奇怪过程。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消费者运动如火如荼。以“消费者权益之父”拉尔夫·纳德为首的人们认为,美国的很多联邦机构已经和商业巨头沆瀣一气,所以应该裁撤这些联邦机构,以斩断商业巨头的利益输送渠道,取而代之以消费者自己的的代表机构。
伯勒萨德发现,里根和其他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巧妙地运用了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势头。他们同样把“官商勾结”视为糟透的东西,但却以此佐证“大政府”的无用。接着,通过玩弄文字,里根们把“消费者”替换为“美国人”,这样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方的资本家,都变成了均质的美国人,既然政监管会导致勾结,就应该一口气为所有“美国人”松绑——结果,不仅是政府的监管机构被大量裁撤,连消费者们自己的代表机构也未能幸免。内德推行权益运动的时候,可没能想到里根会有这一出。
撒切尔政府和工会的斗争更是解释了左翼斗争如何“助长”了新自由主义。英国工会拥有强烈的斗争传统,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保守党政府去国有化的推行,工会逐渐被孤立起来,原先用以斗争的穷人/中产的区分,现在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陷阱。随着更多英国人成为有房有股的“中产”,保守党政府得到的民众支持也就愈发有力,工会斗争也就愈发陷入“中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而工会长期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被当做是阻碍经济发展,助推通货膨胀的罪过而遭到中产阶级的鄙视。等到撒切尔向工会开刀的时候,民意已经转向政府一边了。
有趣的是,相比英美,法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并不全来自左翼,因为两国的左翼力量不够强大。之所以德法的新自由主义推行不倡,反而是因为德国的执政的右翼基民盟没有强大的左翼对手,组织松散,自身包含了一些工会和基督教的力量,后两者反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而在法国,长期右翼执政使得民间没有对福利国家的敌视,故而政府推行私有化之余,国家福利没有任何削减,反而进一步加强。
在全书的结尾,伯勒萨德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开了一个玩笑:保守主义者们,包括哈耶克,常常提到“多数人的暴政”,以质疑民主政治的无用。作者却说,纵观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史,我们看到的是政客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把新自由主义变成多数人的心头好,以此压迫占少数的、底层的人群,这恐怕才是“多数人的暴政”吧。
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势头仍然强劲,而且仍然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保有巨大的力量。伯勒萨德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的批判,是一份有争议但令人清醒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现实背后复杂的运作。她使我们注意到,当我们把新自由主义说成是一系列政客和经济学家合谋的大规模计划,或是某一小撮统治阶级不可告人的计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采信了他们自己那一套洋洋得意的说辞。他们把自己标榜成了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英雄人物,把施行时跌跌撞撞见招拆招的经济政治政策美化为了提前准备好的坚定行动。这样一来,他们就抹去了对民意的调用,抹去了政策施行中的种种临时起意,抹去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以灵活的形态成为主流的复杂过程。而其中左翼行动造成的缝隙,多少让前者捡了便宜。
当我们反抗新自由主义时,也许应该稍加注意,在主流话语背后被遮蔽和隐藏的历史是什么,我们的反抗话语,会不会不知觉陷入唯心史观的圈套里?而从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教训——比如说,既然新自由主义能把握左翼运动留下的社会空隙,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又可否,或是如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tootopia),土逗公社是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受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