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梳理研究中国古代幽冥文化,历朝历代的鬼故事看了个遍,对鬼的认识相当深入,对人更是如此。

栾保群与“幽冥世界”的“缘分”很早便有了,他“自小喜欢听鬼故事,听了怕,怕了还要听”;看戏时,看奚啸伯的《九更天》,也吓得一夜没睡好觉,“一闭眼就是无头鬼来告状”。读初中一年级时,他无意间在一个很小的书店里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用商务旧纸型印的《搜神记》,另一本是吕叔湘的《笔记文选读》,“没料到,这两本小书对我的影响,一直贯穿了六十年” ,栾保群感慨说。
除了早年在乡下担任中学教师的几年,栾保群做了一辈子的出版社编辑的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看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开始留意与幽冥文化相关的材料,并将之摘录下来。抄书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中关于幽冥文化的论述外,最主要的是志怪笔记、唐人传奇里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包括一些学术笔记,诸如《日知录》、《陔馀丛考》中有关神鬼的文字。到2000年,他抄了各种有关材料已有一百多万字。
在正式“谈鬼”之前,栾保群曾以“冥府”为题,写过两篇关于“泰山治鬼”的论文,探讨“作为五岳之长的泰山为什么会成为冥府”。鉴于幽冥文化在学术界终究还是另类,“冥府”之题没有再继续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严晓星先生作伐,开始在《万象》杂志上写起了不那么学术的“鬼话”随笔,成就了“扪虱谈鬼录”这个专栏系列。栾保群研究“鬼话”,不是单单将故事列举出来博取猎奇目光,而是将各类“鬼话”以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法分析——他把“鬼”分为“水鬼”、“僵尸”、“骷髅”等等形状,不仅援引历朝历代的笔记小说,还详细比较了不同故事版本的流变,以此探讨出一个结论:“鬼话”无论如何变化,总是与人相关,从来就没有与人无关的鬼故事,而故事反映的也是人间万象;只是其中的荒诞稀奇,少人深究。
今年7月,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系列出版了第三本《鬼在江湖》,着眼于鬼故事里鬼魂的形体声貌和在人间现形的方式,而前两本《扪虱谈鬼录》(2010)和《说魂儿》(2011)的重点则在于对“鬼话”的分析。在新书出版之后,他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专访,研究鬼故事的人是怎么看待鬼故事的,让我们一探究竟。

界面文化:你怎么想到去写“扪虱谈鬼”系列的?
栾保群:写“扪虱谈鬼”系列可以说是很偶然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动起了整理幽冥文化的念头,我一直在出版社当编辑,没有别的研究任务,工作就是看书找资料,当时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读书消遣的时候,一发现写神、鬼和妖怪的,就收集下来。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做一些整理,但是到底做成什么样子没有具体目标。我想知道,比如“冥府“是怎样发展到晚近这种“地藏菩萨-十殿阎罗-城隍”系统的,因为明代以前的“冥府“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而明代以来的“冥府”也不完全由这个系统独占;自古以来,中国的“冥府”一直是多元化的——佛教的、道教的、民间的冥府同时存在,那么冥府的存在还有多少真实性呢?
其他的“幽冥文化”问题也是一样,都可以用历史的方法揭示出它们的真实成因。当然,这并没有搞科普的意思,只是想让读者了解“幽冥文化”的实质。至于文本的形式,当时只想做一个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那样的东西,但不知不觉就抄撮了百万多字左右的资料,抄的时候也就自然做了整理归类。
界面文化:在这上百万字的材料中,你都抄了什么书?
栾保群:抄的内容太多了,只要是发现了跟幽冥文化有关的——我怕以后模模糊糊不好记,或是不好找——就都抄下来,像是历史书、经书里对于鬼神之说的态度,还有学术笔记小说里对鬼神的探讨。但是这些论述基本大量重复,而最为儒者所认同的,也就是我在第二本《说魂儿》里提到的郑国子产的观点——“鬼魂存在有久有暂,但注定要消散的”。笔记小说里的材料主要是鬼的形态和生活,有与人的交流,恋爱、复仇,以及各种冥府的形态,还有轮回、转世之类的故事。
我对材料是比较敏感和熟悉的。我大学学中文,研究生在社科院念历史,我发现个别中文学者的论著是没有历史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甄别资料真假,对资料的年代和环境没有判断。对资料掌握不好,写出的东西自然是靠不住的,我看资料要先分析可靠性。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引用了内容庞杂的志怪笔记,在你看来,笔记体说鬼是否有一个发展的脉络,比如六朝志怪与明清笔记有没有不同?
栾保群:一方面的确有不同,比如唐人传奇情节诙诡奇艳,出人意表,后世作者很难做到,只有蒲松龄《聊斋》中的一些长篇对传奇体发扬光大了。另一方面,鬼故事千千万万,总是有着差不多的一些套路,比如从魏晋志怪到蒲松龄,说鬼总是善良的鬼多、有人性化的故事多、厉鬼少,还有一些“复仇”模式、“灵魂附体”模式,基本元素都是一样的,“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我其实有个想法,就是把中国鬼故事的类型归纳下来,分析从一个类型伸展出去的变化,比如《说魂儿》里提到的“有鬼一船”这样的类型(编者注:指的是一种灾难故事类型),有很多变体。由一个类型故事延伸出无数不同的变体,不论中国民间故事还是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都是如此,灰姑娘的故事在全世界也有不同变体。而我们从对某个基本类型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对人、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
界面文化:书中也有一些你自己耳闻的传说,比如“家里的簸箕能成精”这样有些可笑的故事,你对市井传说、民间习俗是不是很有兴趣?
栾保群:爱听,但我的记忆力很差,再加上手懒,听了也记不住。另外一个就是,人们说的所谓鬼故事,很多并不是有情节的故事,比如同事老张说他老姐中了撞科,被邻居的老王附了体,一张嘴就是男人的口音。再比如我同学说,看到胡同里有个东西穿着古代的衣服往这边走,一个劲儿地走,就是走不过来,这些孩子们看着都很吃惊。我听到的鬼故事大多如此,好像也没什么可记的价值,也都没有成型的故事。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书上见到的文人记载得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可能都有很大的加工成分。最早汉魏的鬼故事和人的故事完全没有区别,比如讲一个人在荒野中见到一个小屋子,出来个年轻女子招待他——人事和鬼事的区别就在于,他出来扭头一看,原来那不是一个屋子,是一个坟。
界面文化:这样说来,对中国古代“鬼话”的研究与世界民间故事的研究基本是一样的?
栾保群:鬼故事大多就是民间故事的一类。《牛郎织女》也是神怪故事,《白蛇传》是妖怪的故事,《李慧娘》完全就是鬼故事,中国民间“四大传说” (编者注:指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著名的《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基本都跟鬼有关,“梁祝”也是靠死后幽灵变蝴蝶的方式来让故事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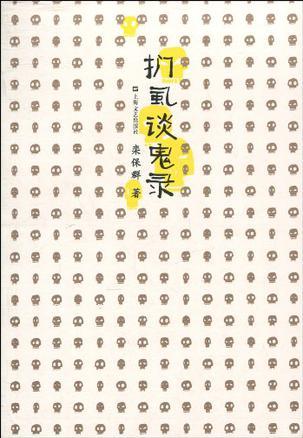
界面文化:这里说的“梁祝”故事靠化蝶才变得完满,是不是意味着“鬼故事”很多时候都成为了现实中无解问题的解决方案?
栾保群:文学本来就有对现实的缺陷加以弥补的作用,不仅鬼狐故事如此,那些才子佳人、出将入相的小说都有文人意淫的成分。只是因为鬼神故事更具浪漫色彩,所以想象力更能放开。像那些半夜来的狐狸精,难免与文人红袖添香的幻想有关系。还有女鬼看似很随便、很自然的一夜情,也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敢于写的,与现实中人性的束缚有关。蒲松龄在《鲁公女》中的那句“生有拘束,死无禁忌”,对鬼魂如此,对写鬼的文人是如此,对编鬼故事的非文人也是一样。那些浪漫的鬼故事最早都是民间创造的,魏晋时期的大量鬼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文人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而且人成了鬼,好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李慧娘,我觉得她在生前不大可能有那么强烈的反抗精神。那些艳鬼生前养在深闺,也很难做出出格越轨之事。但在死后,本来被束缚的人性解放出来了。把现实中实在达不到的用鬼故事来达到,结局比较完满一点,所以鬼故事里复仇主题也很常见。不能说完全是写鬼文人的想象作用,这些事情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只不过可能被礼教斥为道德败坏,甚至成为严打对象。《惊梦》中的杜丽娘还未成鬼,也在梦中发生了越轨之事。这就像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一些事,如果放到五十年前看的话,也许人们会以为是只有鬼故事中才会出现的。
界面文化:刚才你说到鬼故事是民间故事的一部分,但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志怪传奇都是文人创作,像是南宋《夷坚志》的作者洪迈官阶很高,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是一个失意文人。这是不是意味着,鬼故事跟真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栾保群:应该这么说,传奇这个类型多是文人创造的故事,还有很多是文人根据民间口耳相传记录下来的内容,就像洪迈自己是当官的,他的《夷坚志》里很多都是官场上的朋友跟他讲的故事,故事具体到某地某人,有名有姓,这也叫从民间传出来的——“民间”不单单指老百姓,也可能是官宦人家。故事会这么讲,某个官员家的下人老妈子说,官员家里闹鬼了;如果这家遭恨的话,就带点儿诅咒性质;如果这家不那么遭恨,故事就没那么恶毒。我们要知道,鬼故事都是人根据想象编出来的,你在官员家墙外面听见里面有怪声,就可以编出他家里出了什么怪事儿;鬼故事就像我们现在经历的很多谣言,都有着很大的加工成分。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鬼故事和谣言紧密相关,这二者有着怎样相似的加工过程和传播心态?
栾保群:二者是有关的。很多鬼故事里讲江湖术士怎么心狠手毒,把小孩子的鬼魂拘禁起来,役使小孩儿的鬼魂到处敲诈勒索,传得像真的一样,但是怎么可能呢?江湖术士没有这个本事,这个本事也许是他自己吹的,也许是外面他人加工的。为什么大家会相信?原因之一是,大众在添油加醋地传播鬼故事和谣言时好像可以得到一种快感,二来这也反映了人们在动荡时代的特殊心态。

界面文化:在这个系列第一本的书中,你回忆说原来有一段不让谈鬼的日子。
栾保群: “文革”之前不让谈鬼,“文革”期间自然更不允许了,但这些禁令对民众来说形同虚设。1968年之后我在农村教中学,老乡和学生给我讲了不少鬼故事,其中最多的就是当时某村发生的事,比如鬼魂附体、公社干部被巫婆戏弄,有名有姓。可以想像,这些鬼故事在民间是多么流行。但晚上谈鬼并不影响白天搞大批判,也不影响我在课堂上教学生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课本。批判是要批判的,但是老百姓无论如何都要找开心,因为老百姓他不明白啊、听不懂啊,后来就变成找开心了。
界面文化:跟禁忌的态度相比,有意思的是,你的“扪虱谈鬼”系列基本上是在系统性地、甚至是“科学性”地从各个视角,比如说鬼形、鬼影、脱壳、鬼哭等方面来说鬼谈魂,这是不是一种对谈鬼色变或避讳姿态的反拨?你是怎么想到这些角度的?
栾保群:我用随笔谈鬼之初,是没有什么系统的打算的。原来在《万象》上连载,是想到什么写什么,《万象》停刊之后,我也就不写了,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韩樱女士要凑到一起出版。第一本好像有些反响,我这才想起写第二本,这时也就只有沿着一条线索写下去——比如第二本主要是谈“魂儿”,第三本谈鬼的形体,也就想到鬼的模样、影相、声响、气味,想到的要比写出来的多,没写的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相关材料。
我整理资料时要归类,归类之后就好像有一个“系统”了。如果有人要系统地写关于鬼的专著,最好不要先搭起系统的架子,要做的就是搜集材料,由材料本身形成所谓“系统”。因为人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想象鬼,所有的鬼故事都是和人连在一起的,鬼的生活的内容,也就是人为鬼设计的生活形态,好似人世的翻版,其实却和人的生活内容并不完全契合,比如人间的朋党争斗、群体暴动、诸侯割据、政权更替,这些“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热闹事,在冥界是没有的,那里的政权真的是万世一系,枯燥无比。所以简单地说,鬼故事都是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编的,但不完全是把人的社会照搬到幽冥世界中。
界面文化:书中有很多有“奇趣“的故事,比如未死魂先泣(编者注:指人没死,魂就去坟前哭泣的故事)、鬼换个地方打工就无人认识。那么在你看来,这个人鬼混杂的江湖,是不是一个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逻辑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更具有调侃现实规则的趣味?
栾保群:让我写趣味性的东西,还真写不出来,我的书都是把很有趣味的题目变得很没趣味了。因为我没有发挥,都是尽量简略,取其一节,只举一点与我的题目相关的,比如我写“鬼衣”只举某个故事中鬼穿衣服的这一点,写“鬼吃饭”只举吃饭的一个片段。
我觉得鬼界的逻辑和人界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逻辑编造鬼故事,只不过是想把它荒诞化。正如超现实是以现实为参照物,荒诞也是以正常的现象为蓝本,也就是说,两头怪物不过是在原来的脑袋上加了一个而已。鬼的前知就和神仙的前知一样,人不是也有自称先知的么?所谓先知,就是让未发生的事提前出现在自己的知觉中,出现像电影《死神来了》那种场面,中外可能是思路一致的。人们编鬼故事时是不大考虑它的逻辑性的,但有些鬼故事一旦被认可,其中的荒诞逻辑也就被人们接受了。
界面文化:鲁迅和周作人很早就对“幽冥文化”有过研究,鲁迅写有《女吊》,周作人写过《谈鬼论》,多是从文化民俗的角度切入。就你了解,当代有没有类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或者讨论?
栾保群:现在没有。过去陈平原有一本书《神神鬼鬼》,把近代一些学者还有吴晗副市长这些人谈鬼的内容汇集到一起。但真正有见解的还是鲁迅和周作人,一个是对幽冥文化的艺术化,突出的是挖掘其人民性内涵,而最终表现的是人性;另一个则着眼于历史,着眼于幽冥文化的民俗学意义,而最终表现为无神论者的理性。周作人的贡献在于涉猎的广度和中外文献的比较上;而在将幽冥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研究及改造扭结起来这方面,鲁迅先生所做的贡献无人能及;从对复仇鬼魂的看法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二位的部分差异。他们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著,但在零星杂文中所阐述的见解,至今仍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学科上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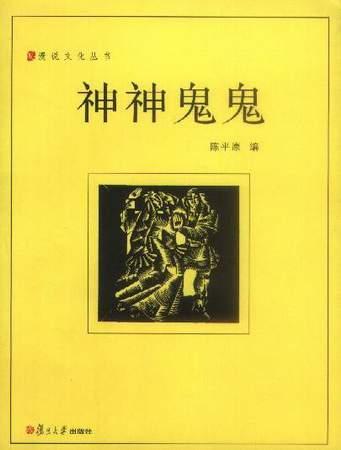
界面文化:日本怪谈很多都源于中国,比如《剪灯新话》,但是日本有人不断推陈出新地写怪谈,而且对当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栾保群:日本的妖怪有一些是从中国传入的,但比例并不大,我统计过,受中国影响的妖怪大约占百分之十稍多。中国的妖怪比日本要多得多,但我们没有“妖怪之学”,这是因为日本走进文明的时间比中国晚得多。中国思想界在春秋战国时就被史官文化占领,中国的神话都改造成了“历史”。民间很多妖怪都被淹没,只剩下个名目,究竟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比如《庄子》中说的“倍阿鲑蠪”、“泆阳”,“水有罔象,丘有峷”,还有汉代大傩中十二神驱赶的十几种鬼怪,很早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实际上,中国民间也一直在对自己的怪谈内容推陈出新,最典型的就是《白蛇传》。从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的蛇妖,到明末冯梦龙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经嘉庆年间《雷峰塔传奇》,至清末出现梦花馆主的《寓言讽世说部前后白蛇传》,再到现在的戏曲《白蛇传》,也在不断地人性化,让妖异故事更贴近老百姓的审美及价值观念。至于近年来改编的《青蛇》和《画皮》,走的好像是另外一条路子,同样是“推陈出新”,与我们的“白蛇精”、“水母娘娘”和日本新编的《牡丹灯记》却不一样。
界面文化:近年来中国流行的盗墓小说——比如《盗墓笔记》和《鬼吹灯》——里面也有很多情节直接源于笔记小说,受到了读者欢迎。你怎么看待广受青少年欢迎的“鬼话”作品?
栾保群:因为时间有限,我很少读长篇小说,对你说的这两部闻名已久,却没有时间看。可是一些新编的城市鬼故事我还是爱看的,一是故事短小,二是构思精巧。人和鬼发生错位,你变成我,我变成你,想象很丰富,对古人的鬼故事有很大突破。但对中国的幽冥文化来说,好像没提供什么新的可取的材料。书摊上有很多集成一大厚册来卖的,我也买过十几本,如果以后能把其中的好故事选一选,单独印出来的话也不错。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