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的探险历史把我们带回上世纪初的中亚腹地,这些故事,有助于我们今天去塑造古老丝路上的新可能。

田野考察中的斯文·赫定
“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先驱者们将很快起到他们的作用,陆地地图上的‘空白区’正逐渐减少,我们对海洋自然环境的了解年复一年正变得更加完善。十分清楚,过去的先驱者通过不畏惧危险和困难的工作方式,已被当代的探险家所效仿,他们详尽地查勘地表以及认识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并一如既往地去填补发现新的空白、去解决找到的新问题。虽然许多地区已作了详尽的勘探,仍然有一些区域是先驱者们未曾到达的地域,尤其是亚洲腹地,长期被人们遗漏,几乎难以进入的广袤戈壁沙漠以及西藏高原无边无际的荒野,在当今如同南北两极一样鲜为人知”。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
当今既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交流与互动的时代。千百年来,丝绸之路连接着东西方两端的古老文明,促成了彼此间的碰撞与交融,在人类文明史上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近代,随着殖民时代到来,传统的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一批批西方探险家,他们目的各异,有些还抱有不良企图,甚至造成了巨大破坏。但他们的探险活动也在客观上提供了关于这一区域的诸多知识,让后来者能够更全面、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这片广袤的亚洲腹地。在如今“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们回顾那些曾经活跃在亚洲腹地的探险家们,相信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过往的故事,并思考当下和未来,我们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的中国。
在中亚探险史上,有几位人物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丰碑,这不仅在于其传奇英雄般的探险经历,还在于其在学术层面所留下的丰厚遗产,使我们能够在听闻那些传奇故事之余,重新去翻看那些保存至今的文物与著作,继而回望与体会一个多世纪之前亚洲腹地的文化与生态,其中一位就是斯文·赫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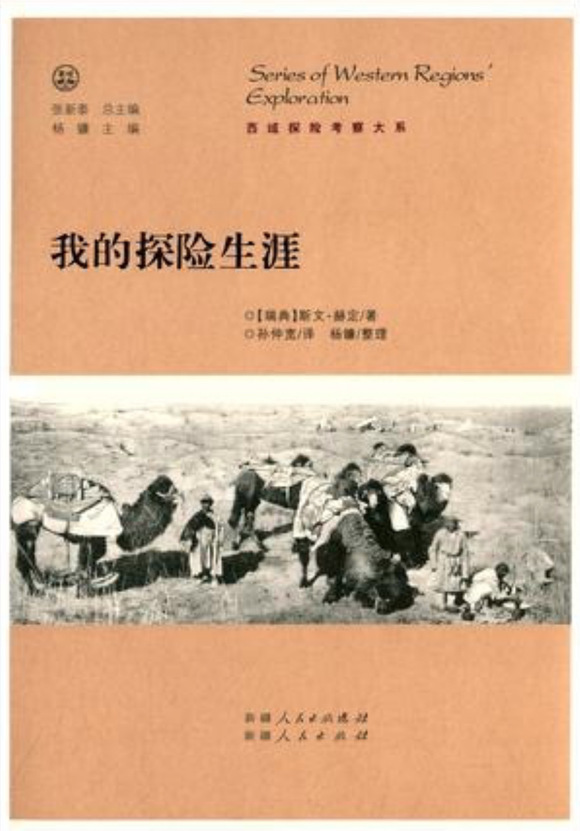
1880年,只有15岁的瑞典少年斯文·赫定在见证了瑞典探险家诺尔登斯基奥德(Nordenskjold)从北极探险凯旋的隆重场面之后,决心从事探险活动,并因此进入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学术世界。18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斯文·赫定得以游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从此,亚洲,尤其是中亚,开始召唤着年轻的斯文·赫定用他的一生去探寻、去发现。
当然,斯文·赫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游历者,他既是作家,也是地理学家,借由他的文字,公众得以了解这些艰险而又神奇的探险故事,学者得以窥见那些重现天日的历史遗存;经由他的地理学记述,我们得以在百年之后精确重复他的探险路线与地点,去追寻曾经的足迹。
斯文·赫定在五次漫长的中亚之旅中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仅仅只是传播沿途得到的新知识,而是在考察中亚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同时,将这片曾经一度被忘却的区域的古老文明,再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从此再也无法忘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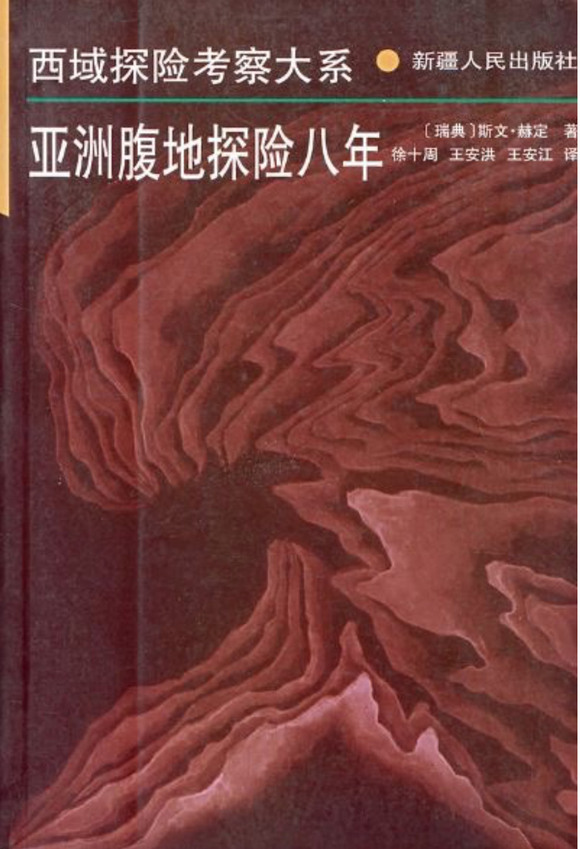
1893年,斯文·赫定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亚洲腹地考察之旅,他于当年10月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发,经俄国大铁路东行,曾经遥远的亚洲在他的眼前展开,他在《我的探险生涯》一书中写道:
“火车沿着库拉河蜿蜒前进,有时在河的北岸,有时又行驶到河的南岸。库拉河沿岸已有垦殖,清新鲜绿的河岸经常在远处闪烁着光辉。然而,除了这些开垦的田地外,其余可说是一片荒芜;大部分都是平坦的大草原,只见到照顾牲口的牧羊人踪迹,还有少数地方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朝北望去,整个高加索山恰似灯火通明的舞台景幕,深浅交织的蓝色调夹杂着峰峦积雪的白色线条,这就是亚洲啊!这片诱人的景致令我舍不得移开视线。在那一刻,我已经,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爱上这块一望无垠的荒原旷野,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被吸引到东方,而且越来越深入。”
这片中亚土地,从此成为斯文·赫定之后五十多年不断游走、探索与发现的地方。
与诸多在这时期探访中亚的旅行者不同,斯文·赫定并不以猎奇的角度看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组成的社会,而是以尊敬的态度,记述这种经由生活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地方性知识。而这种知识,曾经不止一次被用到他的考察之旅当中,让他脱离险境。
例如,他在《穿过亚洲》一书中记载到,在中亚,“柯尔克孜人(此处指中亚的吉尔吉斯人)表现出来的对方位的辨识力和视力,高度的敏锐和精确,被发挥到了极致。”在赫定这样的“异乡人”看来,旅行穿过之处“总感到地面没有任何改变……丝毫看不出有道路的迹象。”但“柯尔克孜人就可以找到他的路,甚至在夜晚,没有天体作为向导来帮助他时,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路。他认识每一种植物,每一块石头,他注意到草丛生长的地方稀少寻常,而且总是靠拢在一起,他观察到欧洲人没有仪器就不可能发现的地表的不规则性。他能辨别出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外乡人骑的马匹的颜色,他拥有世界上最坚忍的意志,他甚至能够看清那匹马的神韵。透过野草地望去,远处只呈现出一个小点正在前行或后退,他就能告诉你那是否是一辆马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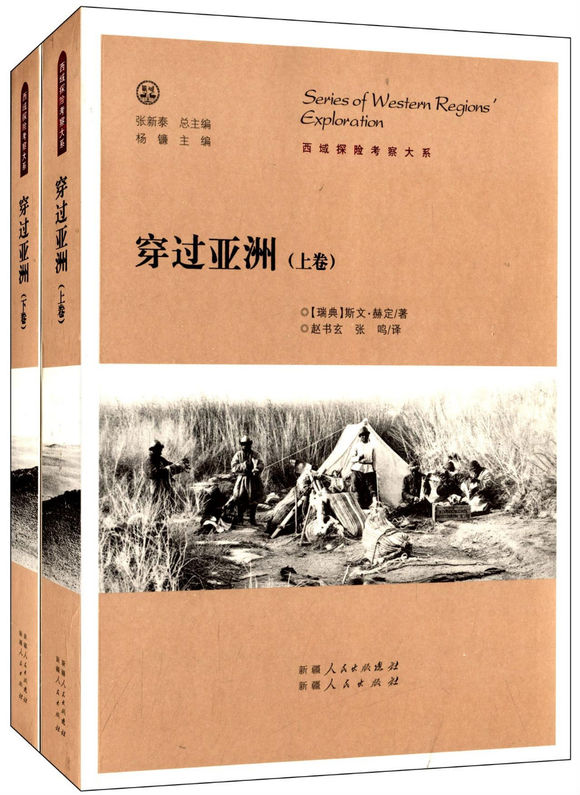
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包森(James Bosson)所指出的,作为最早关注中亚的欧洲学者之一,斯文·赫定与其后的研究者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考察与研究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在他之后的斯坦因、勒柯克、伯希和等人,所关注的全然是人文方面的内容;而他的俄国同行科兹洛夫的成就,则在自然科学中的地理学和动物考古学方面。正是因为兼顾了自然和人文,才使得斯文·赫定不仅为学术界所铭记,更为欧亚的广大公众所熟知,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探索发现之路上的“超级巨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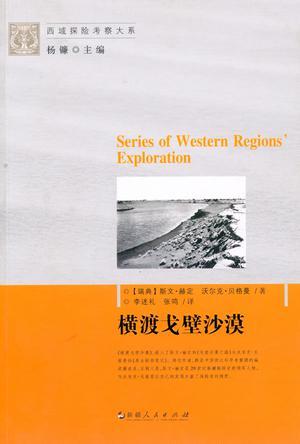
斯文·赫定的那个时代,也正是丝绸之路衰朽没落的时代。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考察回忆,向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一幅破败没落的场景:
“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
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他嘘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并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对于科学探索而言,和平总是可贵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文化和历史遗迹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斯文·赫定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贵的和平间隙,却无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回亚洲腹地,他年迈了,而与此同时,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决定性地变化了,但他还是期望:“当和平再一次降临时,我希望亚洲腹地的大门能再一次打开,持久的研究和考察工作可以继续。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会比以往更多地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飞机将会像汽车一样在各地的联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但是要想探知地球的秘密,要了解地球上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它上面繁衍的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需要再去探险。在没有人迹的地方,仍然需要那些古老的骆驼队历尽艰辛,穿越在荒漠之中”。
在漫长的一生中,斯文·赫定的足迹踏遍了亚洲内陆的每个角落。这些地方独一无二的地貌和生态特征,很多都经由他的记述和介绍被西方世界所知晓,并成为后来很多西方研究者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神奇与魅力所在。而如今,西方曾经对“神秘”东方的追寻,正在新的语境下,展现出东方向西方“回看”的另一种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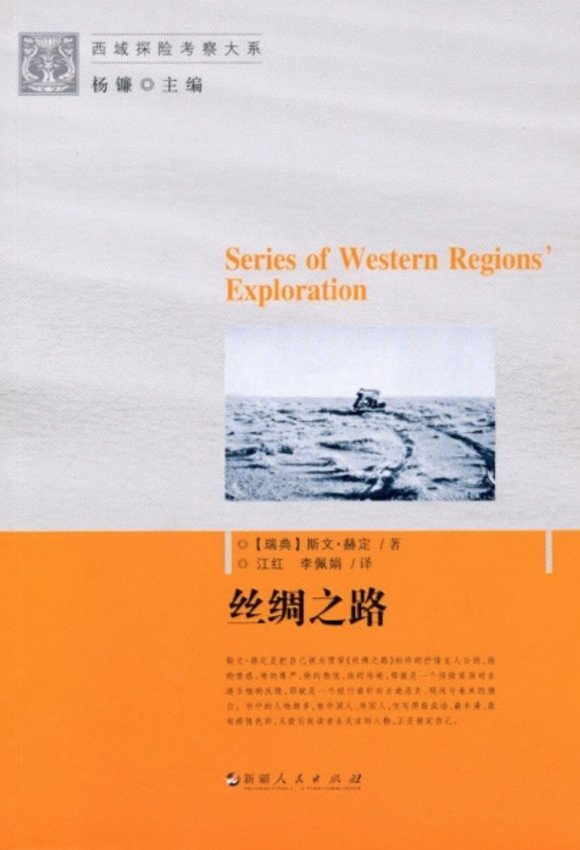
长期的田野生活,成就了斯文·赫定的探险和学术地位,更塑造了他对这一区域的敏锐判断力。丝绸之路的未来图景,虽然在他的时代里似乎看不到新的曙光,但斯文·赫定还是充满着信心,他不无预见地写道: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汽车旅行爱好者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穿过整个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经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到达汉堡、不来梅港、加莱或布伦……他以最近的路线穿越了整个旧世界的横断面,完成的是一次最有趣、最有教益的汽车旅行,也是这地球上最好不过的一次旅行。待到归来时,他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回忆:风景如画、人潮如涌的中国内地,戈壁滩边缘上的绿洲,敦煌和楼兰之间神秘的大漠,野骆驼那孤寂荒凉的故乡。他眼前会掠过那游移的湖泊和那刚在孔雀河古河岸上重新长出的植被带。他会目睹塔克拉玛干北缘上连绵的沙丘和天山脚下塔里木人的绿洲。亚洲腹地的夏日会烤得他发烫,沙暴那鬼哭狼嚎般的怪声和冬日暴风雪的呼啸尖叫声,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将连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忌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在如今这一新的时代,历史正塑造着这种可能性,斯文·赫定未曾亲身看到的,或许我们能够做到。
(作者简介:袁剑,青年学者,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等作品。)